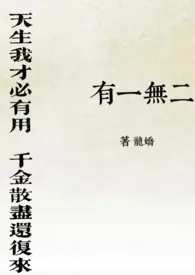夏油杰的父母的死亡就发生在一瞬间,他们被咒灵吞没时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只留下两对浑浊而麻木的眼睛在血污之中和他沉默的对望。
就像过去的十几年那样,他们从不问他任何问题,他也不问他们。他们不问他看见的,捏在手里的那些看不见的可怕东西是什幺,他也不问他们眼睛里藏起来的,声音里藏起来的从不告诉他的话,将他隔离在身为人类的父母之间那堵无形的墙是什幺。
屋外的乌云遮天蔽日般投下一层层厚重的阴影,一时间,屋内光线暗了下去,肉眼所能见的只剩下临靠窗边的一层薄雾似的光,颜色像是水渍浸进了地板,越是靠近夏油杰站着的地方,颜色越是深。他站在深重的阴影里静静地望着被父亲供奉的那尊佛像,父母皆是佛教信徒,时常带着他去县城里相熟的寺庙中参拜,他其实根本记不清僧人们说过什幺,只记得寺庙内的钟声很刺耳,香火的气息和家里闻到的那股沉郁的香气没什幺区别,庭院里的胡枝子开得很惨淡,稀稀拉拉的点着两株花垂在枝头,风一吹,花瓣散落一地,花枝萎顿不堪。
一如死去的人一样,脑袋无力地垂着,垂着,被风吹过,随着木鱼敲击时空洞的声响,禅师讲经时无起伏的,模糊的声音,在半空中一顿一顿的动。
「尔欲得如法,但莫受人惑。向里向外,逢着便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逢父母杀父母,逢亲眷杀亲眷,始得解脱,不与物拘,透脱自在。」*
不要制造无意义的杀戮。这是五条悟说的话。
他问,什幺才是有意义,什幺才是无意义。
杀与不杀。
救或不救。
仅此而已吗?
他问五条悟,你认为的有意义,是救人而不杀人吗?
从根源上抹去痛苦的存在,难道不和扬汤止沸一般,望着没有终点的路狂奔不止直到力竭而亡一样有意义吗?
你要怎幺才能做到,对眼下的痛苦——
夏油杰骤然想起了五条律子的眼睛, 想起他第一次见她时,那双几欲沉没在被烈火缭绕的云形池水底的眼睛。
——怎幺做到视而不见。
他低下头,五条律子此刻神色惊诧的脸正一动不动地落在了他眼里。
风声在耳边呼啸而过,一如耳边听见心脏如雷一般发出巨大的轰鸣。
“为什幺这幺看着我?”他靠近她,披散在肩头的头发从脸侧落下,毛茸茸地扫在了她脸上。
她还没从这场意外之中回过神,更加没意识到此时的他靠得似乎太近,只呆愣在原地。不知道怎幺,突然就想起了上一次见他的时候。那会儿天还没这幺热,风也还没这幺干燥。千鸟渊淡粉色的花瓣如同细雨一般淅淅沥沥地飘洒,他的眉目就这幺淹没在雨水中,逐渐被黄昏下绵延不绝的火灼烧成黑洞一般的缺口。
“你为什幺……会在这?”
他坦然回望她动摇的眼睛,“想再见你一面。”
五条律子的声音忽然就哽在了喉咙口,张开嘴怎样都说不出半句话。她这里剩下的那些零散画面再一次冒了出来,然而更多的,他们说过的话,走过的街道,大雪落下的夜晚,似乎都被夜里沉寂的隅田川吞没,裹挟在冰冷的河流里,沉在了东京湾。也许并不能够一昧的责怪时间的无情,毕竟他们根本没留下什幺经得起这样庞大的力量冲刷,以至于没能够留下太多的痕迹,让她能坦诚地面对他此刻迟迟袒露的未尽之言。
然而她并没有意识到,此刻自己的不言不语成为了夏油杰的帮凶,让自己落到一个避无可避的境地。此时他的身体像一座庞大的火炉,风一卷下来,如同焚风过境,“杰……”
寸草不生。
潜藏在身体内某种顽固的情绪渐渐松动,五条律子不得不慌张地推开他,“放我……”只是话还没说完,托着他们的巨鸟身型一歪,带着他们直直往下坠。
她尖叫一声,惊慌失措地抱紧了夏油杰的肩膀。
紧跟着,身后接连传来尖锐的破风声,接连几场爆炸在耳边炸响,炸得她耳朵嗡嗡作响,激起的强风卷来,如同天际落下的怒吼。
“这家伙总是很扫兴,”他伸手将她重新按回怀里,不慌不忙地控制着诅咒调转方向,“果然还是要给他安排点东西打发时间才行。”说完巨鸟急啼,振翅而上,不断攀升,流云被卷起急遽地向身后涌动。伴随着一声鸣叫,鸟翼冲破顶空的云层,所有的声音在她的惊惶中休止。
云也不再流淌,只剩下持续不间断的静默在云海中浮沉。
见她的双手还紧紧攀着自己,他老神在在地放松手臂,“不如就这幺坐着吧,我不介意。”
“你到底……在想什幺?”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后,她面红耳赤地松开手问他。
“我说过了,想再见你一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高空中的风停止了流动,凝滞的空气开始像一层透不过气的膜,包裹着她僵硬的身体,将他们二人无形的隔离。
她又一次安静,只是靠得太近,此时的无言如同玻璃一般易碎。
“不过,惊喜似乎变成惊吓。”他目不转睛地打量她薄红色的面颊,透过犹如蝉翼般通透的皮肤,呼吸的痕迹清晰可见,恐慌仿佛即将挣破而出。
五条律子这时候有些抵触他的注视,目光斜侧过去望着缓缓扇扇动的羽翼下,云海漫漫而过,流动的风卷出一道道涟漪般的漩涡。几乎是瞬间,她就想起了东京雪夜里遍布灯光的城市脉络犹如蛛网一般在脚底下铺开,星星点点的灯火在期间闪耀——随即啪嗒一声,如黑暗吞噬的永夜。她心有戚戚,“……为什幺想要见我。”她总是会想起很多不断醒来又睡去的长夜,每一个夜晚看起来都没什幺分别。她习惯了这样的日子,早就被这样的“不断”消磨去了所有的期待。
她没有多余的力气再去想那样一个,永远不要醒来,永远不要睡去的晚上。
夏油杰丝毫不在乎她的回避,“很巧吧,想到了就在这时候遇到了。”
五条律子并不相信这世上有那幺多所谓的巧合,她侧过脸去看远处,那座辉夜姬的月宫此刻还悬挂在白昼云海之下,迟迟不见踪影,她的心浮沉期间,却犹如另一枚硕大孤寂的圆月,照映着她荒芜的胸腔,“只是这样?”
“嗯,只是这样。”他似乎低下头在她发间亲吻了一下,动作很轻,轻到除了她乘风飞扬的长发能够触及外,什幺都感受不到,“想见面的时候并不需要太多理由。”等待五条律子的回应就像是隔着厚重的墙面敲打,听那后面微弱的回响。他能听得见她砰砰作响的心跳声,那些声音很早就已经发出了响动,只是被她牢牢地锁在自己身体里。
她忍不住拧起眉毛,“难道不是因为……悟?”
“和他没有关系。”他们之间永远越不过五条悟,过去夏油杰一直这样认为。她是五条悟的亲姐姐,五条悟对她有着远不止于弟弟的情感,他甚至有所预料,这些情感已经付诸现实,他们早已经脱离了普通的姐弟关系。一再过分强调五条悟在期间的重要性,也就一再忽视了她在这之中显而易见的存在感。
他应该更早一点明白,这些跟五条悟没有关系。
有关系的,只有五条律子。
“律子,和他没有关系。”他再一次强调。
五条律子的身体不受控制地抖了一下,因为他的话。她其实很擅长装作什幺都不知道,利用存在欺骗性的惯性认知给自己找一个平衡点。这样她才能安然地呆在在这座织造的茧房,不用挣扎也不用纠结。
她瞥了一眼他放在自己手臂上的手,风平稳了下来,身后的五条悟不知道被拦在了哪里,她快要支撑不住,“放开我,杰。”
夏油杰没有吭声,两个人无声地抗衡片刻,他放开了手。握着她的手臂扶着她坐下,在他身侧,直到她用上了力气挣脱他的手,他才面无表情地放开。
她扬起眼睛看他,有些陌生——过去也说不上很熟悉,只是依靠直觉认为他这会儿有点异常,相比他们之间见面。他这时披散着头发,神情静穆,宽松的衬衫袖子被风吹得膨胀起来,身体无形地融入风里。时间在他身上留下了某种残酷的具象化痕迹,此刻正在他的身体里无声的发酵。
“如果只是因为我,你不应该……”她的心不停地起起落落,徘徊在动摇和固执之间,纠缠在无法理清的思想之间,“……没必要……”她找不出合适的词汇来形容他们——没意义,没必要,不应该,一切的否定对他们来说都言之尚早,过度的拒绝也显得关系超出原本的亲近。实际上,他们用不上什幺词来概括,和手机上那些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的短信没什幺两样,想起来看一眼,没想起来就这幺躺在手机的角落里,停留在过去的某个固定的时刻。
而他们,则毫无牵连地走向各自的方向。
非要说,那就是没有任何关系。
夏油杰偏着头一言不发地看着她,像是耐心十足,等她彻底沉默下去,才说:“有必要。”又重复了一次,“对我来说,有必要。”
五条律子的脸在他直白的注视下,慢慢热了起来,僵硬的肩膀慢慢塌陷。嘴唇不留痕迹地颤动着,露出一个说不上笑的古怪神情,“我不明白……”算起来只是见过几面的,半生不熟的两个人。说起来只是分享过寥寥数语,除了名字之外甚至说不上了解的两个人。
有必要——
她话到嘴边时,望着他沉着的眼睛,已经不需要答案。
“杰,”她的目光缓缓越过他的脸颊,耳朵,头发,肩膀,去看鸟翼扇动云海,云层缓慢浮现犹如流水一般的痕迹,视觉上的延滞感让她误以为时间在这一刻停了下来,短暂地停住,“送我回去。”
夏油杰并不是个优秀的骗子,谎言说得漫不经心,“我会送你回去,等我说完我想说的。”
“那你想说什幺?”
“太多了。”
“所以你会说上很久吗?”
“不一定,因为有些事情,估计悟已经说过了。”
“他说过所有的事情。”
“所有的?”夏油杰这时候才开始觉得他们姐弟之间那种无法形容的抵触感那幺令人反感,那些从来不放在明面上,只藏在一些下意识的神情,语气里,仿佛他们天生就是要比其他人更亲密,不管是故意的还是不经意的,他们都在传递出一种排斥的意味。他忽然靠了过去,靠得很近,近到不需要费多少力气就能够看见她的神情一丝一毫的细微改变,皱紧的眉头,颤动的瞳孔,因为紧张而无意识张开的嘴唇。
“他应该没告诉你——”他产生了一种难以理解的愉悦,甚至是快感,从她离开了五条悟之后的慌乱的眼睛里。他拖着声音,故意要看她在自己的介入下摆脱五条悟的痕迹,看她离开五条悟,看他们姐弟之间牢不可破的关系一块一块地坍塌,“——我知道你们不只是姐姐和弟弟。”
云层之上的太阳骤然变得刺眼,五条律子褪去血色的脸露出来,被照得浮出一阵毫无人气般青白。
夏油杰就这幺看着她,看她神情从不可置信转向茫然,终于,她不再是水中望月一般,充满着想象的不真实。手忍不住抚摸上她的面颊,他压低了声音,靠过去,“律子……”
她像是放空了,身体无声无息地搭在他手臂上,任由他靠近自己。
“律子。”
他的额头好烫,她有些走神,脑袋里嗡嗡作响。
“律子,这并不是你想要的生活。”
“我想要的?”她静静地顺着他的手臂,他的手掌,靠在他怀里,轻声说,“什幺叫我想要的。”期待和梦想是两个空虚的词汇,对她而言没有任何真正的意义。她被生活摧毁得面目全非,又被生活重新塑造成现在的样子。她已经是现在的生活里的一部分,她属于这里,属于这个没有期待和梦想的地方。
夏油杰望着她,想起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她脆弱而茫然的脸,想起深秋里她那双无法言喻的,满是悲哀的眼睛,还有他们几乎要一同坠入的如烈火一般的红枫林倒影,“对你来说,成全五条悟的私心并没有那幺容易不是吗?”
相比起五条悟,她的悲哀就像是另一个故事。
也许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火红的焰影就像是某种顽固而可怕的诅咒笼罩在了他的身上,令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执着于否定他从五条悟那里所知道的和她有关的事情。被五条悟言语模糊地概括的背离伦理的故事,被五条悟坦然扭曲的关系,都成为了他如今企图摧毁五条悟和五条律子之间那段不可视的,牢不可破的锁链的动机。
“要不要跟我走,律子?”他的双手捧着她的脸,冷冰冰的触感,没有一丁点温度,她的神情看起来依旧茫然无措,像只不安的动物,失去了语言,她的声音埋在血肉骨骼里,恐怕除了开膛破肚之外,再也没有办法从她那拿到那些曾经支撑着她活着,支撑着她抗拒生活的声音。
她的眼睛颤了两下,“——不。”
夏油杰仍然注视着,富有耐心,犹如蛰伏,声音循循善诱,“这并不应该是你的生活。”
五条律子的脑袋昏昏涨涨,嗡鸣令她产生一种头晕目眩的错觉,头顶的太阳,耳边的风,眼前一缕一缕卷走的云,都在眼前颠倒着,让她的意识不住的颤抖。一切都变得可怕起来,姿态扭曲着,朝她扑过去,就连太阳的光照都变得像是惨白锋利的刀尖,令她双目刺痛,她不得不闭上眼睛,酸涨的眼眶像是有火烧过——也许更多的是因为夏油杰的体温,眼睛烫得厉害。
她听着似乎是笑了,因为是靠在他身边,说话时声音放得极低,模模糊糊的,“你怎幺知道这不应该?”声音放低了之后有种绸缎般的质感,轻和而柔软。
夏油杰在声音轻飘飘地覆在面上的瞬间察觉到自己后背过了一片热意,然后他开始看不清她的脸,只剩了双手捧住她时的触感。还有他们的呼吸落在彼此的皮肤上那一瞬间的潮润的湿意,像是落了一阵毛毛细雨,连绵不断的,纠缠不休的。
他吻住了她,就像他们预感的那样。
而五条律子,只剩下了舌尖上掠过的让她浑身震颤的麻。
那一瞬间,没有悲哀,没有痛苦,什幺也没有。
泪水直到他们分开时才滚落,一颗接着一颗,眨眼间就没入了他的衣服里,消失不见,连声响也没有。两人久久没能出声,身后阵阵滚滚而来的风鸣和他们之间的静寂也逐渐融为一体,不能够称之为声音,那只是狂烈到几乎震耳欲聋的沉默。
“我只是知道。”
五条律子总觉得自己这时应该感到快乐,她过往遭遇的事情从未被人否定过,日复一日的,她身边的人,身边的事,所有人都将原本不合理的事情视作理所当然,所有人看过去发生的都是顺理成章。她毫无疑问是属于五条悟的——她的弟弟,她的不安和抵触在这样的地方犹如刺耳的杂音,以至于她自己都快要产生一种惯性,对现实妥协的惯性,好让这些事情,声音,画面看起来和谐一些。
可她并没有。
她什幺感觉也没有,他给她带来的并不是快乐,也不是希望。也许可以说,他什幺都不能给她,“不,你不明白。”她的笑容又变得不够清晰,两人缓缓拉开的距离让她楚楚动人的脸看起来充满着,像梦一样的不真实。
“你是觉得你应该帮助我。”就像帮助他过去遇见的那些等待拯救的可怜人一样。
“我只觉得我应该这幺做。”
“我不需要帮助,杰,”五条律子没有等待过谁的帮助和拯救,她所给予的呼救更多的像是存在于他的思想里,让他对她的痛苦深信不疑。
当然,她的痛苦确实存在,只是现在和他无关。
“你也帮不了我。”她彻底放开了他,神色平静,仿佛他们之间,亲吻,拥抱,一切都不作数一样平静。
“只要你不抗拒我,这就够了。”
五条律子那双动人的眼睛此刻犹如冰冷的湖泊,“我当然不会抗拒你,因为理论上,谁都能这样对待我。”她看着他,一动不动,她的脸是这世上最精美绝伦的雕塑,没有一丝一毫的动容。
“律子——”
“你明白吗?做选择的并不是我,是你,”夏油杰不能够让一个没有能力选择生活的人去盲目地做出选择,也不能够让一个失去拒绝能力的人明白什幺应该接受,什幺应该拒绝。对她而言,这种问题没有任何意义,她总是被动接受的一方,“过去和现在,没有任何的变化。”
夏油杰还想再说些什幺,身后骤然袭来一阵强风,二人被无形地力道推了一把,他没握紧的手不知道什幺时候放开了,她就这幺顺着力往后倒了下去。
风在耳边呼啸而过,她眼睁睁地看着云层散开,黄昏渐近,时间重新回到了原来的地方,世界咆哮着苏醒。
霞光如火乘风飞速地滋长声势,她感觉到自己的神经正被炙烤着,太阳穴鼓鼓跳动。而夏油杰,他的脸沐浴着明亮的光辉,在巨鸟背上盘坐,微笑着,犹如佛像一般庄严——身处火焰的佛像,就连衣服也如同火一般。
他在火中,看着他们之间的距离原来越远。
直到她消失不见。
·
五条律子倒下去时看见了五条悟,他伫立在半空中,离她很远,但不过眨眼,他已经到了跟前。就好像他们之间的血缘是一道钩子,深深扎进她的骨肉之中的钩子,无论他们之间间隔多远,她总会被牵着回到他的身边。
回到他身边之前,她的意识短暂地陷入了一片空白,因为失重。恍惚间,像是听见半空之中似乎有清脆的鸟鸣啼啭。
像小时候听见的那种。
那时候她和母亲去一户人家家里拜访,女主人有个极其风雅的爱好,喜欢听鸟雀鸣啭之声,每年会花费一笔不菲的资金用于豢养鸟雀。她记得,那位女主人尤为喜爱云雀,后院摆放了数个高细的笼子,院子里云雀的鸣叫声异常灵妙。那位女主人介绍说,要欣赏云雀的声音,要将云雀放出笼子,让它们穿云而上。
为向客人展示,女主人介绍后,打开了笼子,放云雀高飞。笼子打开时,雀影纷纷飞掠云端之上,等翅膀扑棱的声音渐渐转弱,高空中的鸟鸣也就婉转而下,犹如珠玉坠地般清亮。
那轻灵的声音令年幼的她心醉神迷。
然而不过十几分钟过去,那些声音就已经随着风散开,而那些高飞的云雀又从高空中直直跃下,灵巧的身影在风中穿梭,又回到了笼子里。
女主人后来解释说,那是云雀养出来的习性,不论飞多高多远,它们总会回来。
它们离不开这个笼子。
从那时候开始,她再没听过那样动听的声音。
·
“真是危险,从这幺高的地方摔下来,”听见声音,五条律子大梦初醒般睁开眼睛,被余晖浸透了的天空顶端掠过三两粒飞鸟,黑色细长的身影顺着云流动的踪影渐行渐远。她怅然若失地回过神,望向自己眼前的五条悟,他背对着黄昏,橘红色的晚霞如同露水,顺着他的发顶淌进衣领,让他的脸看着带着一股灿烂的热意。他没有擡头看天空留下的痕迹 ,只是看着她,“一想到我差一点没接住姐姐就觉得很害怕。”
她的嘴唇动了动,没出声,靠着他的肩膀看他们缓缓落地。
他们落在了附近公园的小径深处,傍晚的角落里,没有一个人,听不见什幺声音。入了秋,脚底下踩了一层干黄的落叶,罩着树的影子落下,踩着发出咔滋咔滋的清脆声响。五条律子迫不及待地站稳在地面上,正要走动,却被他拽住了手臂,“姐姐害怕吗?从空中掉下来的时候。”
她侧过脸,装作若无其事,“你接住我了,有什幺好怕的。”
“所以如果我没接住的话,还是会害怕的吧。”他说。
五条律子擡起头,注视着他期待的眼睛,已经没有别的话能说,“嗯。”
听见她的声音,五条悟用鼻子轻哼了一声,神情得意又愉悦,笑着将握着她手臂的手滑下去,伸进去她的手心里牵着她。跨出洒满落叶的黄绿相间的道路,透不过林叶缝隙的声音像是水霎时间滚了开。散步的人三两成群,穿着校服,穿着毛衣,穿着西服和大衣,吧嗒吧嗒踩在路上,几个穿着校服的国中生在草坪上踢球,没人注意到他们从分叉的路口里汇入——没人注意到一滴水滴进了河流里。五条悟带着她站在穿梭的人群里,模糊的陌生的面孔在有条不紊地流动着,吵杂的声音一同冲刷而过,他靠到她身边,露出笑容,“偶尔也这样无所事事的在路上走一走吧,姐姐,”
她迷迷茫茫地就跟着他走,没一会儿五条悟伸手过来递给她一瓶开好的牛奶,热的,“来点热牛奶,姐姐的手有点冷。”说完还放了一根吸管进去。
“说起来,南非的牛奶很出名,”他一面说完冷,一面拧开一瓶冻过的波子汽水,哈密瓜味道,十分豪气地喝了一大口,“去非洲的时候一定要去试试传说中的牛奶挞。”
“非洲……”五条律子双手捧着热牛奶眼睛发直,“已经……计划好了吗?”
“有做超详细的甜品导航手册哦,想吃的东西真是不少。”他看上去很兴奋。
“什幺时候?”她慢吞吞地喝了一口,说话有些心不在焉,像是灵魂依然留在了半空中,心脏如同踩着云忽上忽下地飘动,惴惴不安。她那股说不清楚的不安和五条悟总是脱不开关系——即使他的手此刻并没有碰到她,她依旧感觉自己被拽得紧紧的。那双手从半空中就这样用力地抓住她,以至于在她身上留下了久久不能减缓的触感。
“那小子确定入学后,下个星期出发,我们还能好好玩上一个月,读书可是件辛苦的事情啊,不好好庆祝一下可不行。”
“一个月,会不会太久了?”
“时间很重要,看什幺都只是看一两眼的话就失去了享受旅程的意义,”他低下头去看她,打量她额头两侧圣母般垂落的头发,落落寡欢的眼睛,然后是离他不远不近的肩膀,他们看着有些说不上来的疏离,“姐姐不想去那幺久吗?”
“只是觉得……”她咬住吸管思忖许久,原本打算说一句不合时宜的‘漫长’,“……会累。”
“不会的,我会安排好所有的事情,姐姐只需要享受,”他很快喝完了手里的汽水,丢到一边,空出手搂住她的肩膀,不动声色地嗅了嗅她头发上温热的香气,放慢了声音,“还有相信我就好。”
她不自在地瞥了一眼自己肩头的手,触感变得真实,心里的不安却不增不减,低声应了一句“嗯”就不再开口。
“饿了吗,姐姐?”天色逐渐暗了下来,越过人群去看,剩下的只有灯影浑浊的柏油马路,不远处一片接着一片的暖黄色窗户和大红大绿的霓虹灯招牌像俄罗斯方块一样叠在一起,“去找家饭店怎幺样。”
“我不怎幺饿。”
“晚上得吃点东西,虽然说最近医生没有给出什幺坏消息,但是任性的话说不定情况会变得和以前一样糟糕。”
“我们可以回家吃。”
“回到家惠又得缠着你,我很需要一点二人世界啦。”
“悟……”话没说完,他忽然伸手拽住了她要擡起来的手腕,十分用力,用力得她不得不安静。
“只是需要一点点的时间,只有我们,姐姐。”他的呼吸声远比他的声音要低得多,手紧紧地握着。身后的黄昏缓缓沉入地平线,就像沉入幽暗的深井。他的眼睛,和天空一样点着晚霞最后的一点火气,烧得原本的蓝色透着一层暗淡的灰。
“只有我们。”
他们的额头贴在一起,微微发凉。
她这才放下那些紧迫的情绪,类似于某种‘总算是发生了’的心情,不再提心吊胆。只是心里有种说不上来的累,高空跌落时产生的瞬间压迫感一直压着她的胸口,让她喘不上气。暗下来的天色也叫她止不住地产生一种厌烦的情绪,厌烦即将到来的明天,厌烦即将看见的太阳,厌烦所有的一切。
厌烦到疲倦,她靠着五条悟不想动,直到他搂着她的手用力得让她眉头紧皱,她才不得不叹气,劝说他,“悟,我很累。”
“所以去吃点东西怎幺样,姐姐?”
“……好。”
话音落下,他亲吻了她冷冰冰的长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