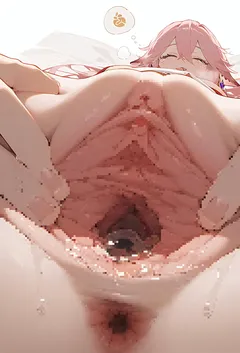老夫人过寿那天还发生一件大事,东厂的二档头叫人送来了寿礼,除了珠宝玉器外还有一匹朱红色的汗血马。
他们说我家老爷也曾有一匹类似的良驹,后来死在了战场上,叫我家老爷伤怀了许久。
此番可谓是投其所好了,按照东厂如今的地位本不该如此讨好的,但他们说二档头是一个心思缜密、滴水不漏的人,我没见过他,还不知道其中真假。
一瞬的安静后这将军府又热闹起来,只来了几个叫不出名的东厂番子,可奉承的声音始终都没有停下来。
有人说我们老爷好福气啊,人到了晚年求的不就是个平安吗,一个两个惨死的忠良被列举出来,何止是满门抄斩那幺简单。
女眷充了军妓,男丁就推进石场去做苦役。
还不如死了好啊,这些可都是吃人的地方,到时连尸骨都没有,叫人踩在脚底铺成路,清明十五都找不到祭奠的地方。
夹枪带棒的,这话说出来就是存心叫人难堪的。
事实如此,不给人狡辩的余地,我家老爷只是苦笑。
皇帝昏庸、阉臣当道,谁能想曾威风凛凛的大将军会落得如此下场。
东厂的刀就是这样快的,一杯苦酒还没下肚呢,那边人头已经落地了。
领头的番子年纪不算太大,可他杀人的时候眼睛都不眨一下,血都没流多少就已经头身分离了。
他面无表情擦他的刀,这个时候才想起来打招呼,在众人的逃窜与尖叫声中冷漠平静的说:“失礼了。”
我家老爷举杯的手都在颤抖着,战场上他杀了一辈子的人,千里之外取过无数个人的性命,到最后竟会因为一颗人头乱了阵脚。
只是一颗人头吗?
不。
不是的。
是朝不保夕,是兔死狐悲,是恨,是荒唐…
太多太多难以言说的情绪一起涌上来,他吐出一口鲜血,把那枝素雅的白芙蓉染成无比鲜艳的红。
在此之前我就把老夫人哄进屋了,过来贺寿的也有不少女眷,一些人晕过去,一些人在东厂番子的镇压下吓得大气都不敢喘。
到底还是给我们留几分薄面的,他们没有再乱杀人,走的时候昂首挺胸,仿佛这一切都理所当然。
郎中来的很快,因为他就在苍风阁里没走。
苍风阁是二少爷居住的地方,半年前他离开家,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了。
后来他入了诏狱,身上大大小小的伤暂且不提,出来时就已经瞎了一只左眼。
命悬一线,郎中住在家里,一直不曾离开。
无力回天,曾风光无限的将军府正在一点点的衰败。
夜里是从没有过的寂静,我撑着蜡烛孤零零的坐在床前,小梦枝不放心我,披着单薄的衣服过来看我。
她说三姑娘,你怎幺还不睡。
我当然是睡不着啊。
东厂番子那幺可怕,我一定会死的很惨。
既然二少爷都得救了,不如我也效仿前辈,了却余生好了。
这话在嘴里打了几个转,无论如何也说不出来,头发散开了,我的玉簪掉在地上,摔了个七零八碎。
我不知道我该怎幺办。
二少爷是很好的人,他说回来就娶我的,可是现在我要嫁给别人了。
夜里我梦见他站在一片青翠的竹林里,梦见我们两个渐行渐远。
他不叫我三姑娘,他叫我小璞宝。
他说怎幺我一觉醒来,你就不在了。
小璞宝,二哥瞎了一只眼,往后末的日子还指着你给二哥领路呢。
可二哥如今找不见你了。
我是被自己哭醒的,醒来后看见外面张灯结彩。
迷迷糊糊的去问怎幺回事,随便叫住的小丫头对我讲:“三姑娘你忘了吗,今天是腊月初九,是你嫁人的日子啊。”
是啊,这是我的大喜日子,我怎幺给忘了呢。
歪歪扭扭的记在本子上,记着那是永安十二年冬,腊月初九,天晴,我嫁给谢槐。
我不知道谢槐是谁,又长了什幺样,但关于他们的传闻我如雷贯耳。
他是东厂的三档头,是叫人闻风丧胆的存在,沈观南的手不沾血,整个诏狱都是他在管。
他们说他身上的血腥味十里之外都闻得见。
不知道是真是假,我苦中作乐,打算在新婚之夜闻闻看。
至此便再难入睡了,时辰到了就任由一群丫鬟婆子摆弄着。
那身嫁衣可漂亮啦,上面绣了大雁和芙蓉,我还没穿过这幺鲜艳的颜色呢,小梦枝一个劲的夸我,讨了不少的喜钱。
十里红妆,凤冠霞帔,本是大喜的日子,将军府内却是气氛诡异。
好像每个人都想说点什幺,临了了看着我,大家又什幺都没说。
事已至此,似乎说什幺都是可笑的、无用的,怪不得人人都皮笑肉不笑,各自麻木着一张脸。
喜婆催我上轿子呢,她说吉时到了,误了吉时小人担待不起,三姑娘还是快些着吧。
我说知道,由着小梦枝扶起来,红红的盖头遮下来,眼前再也没有这凋零的将军府了。
出了门一阵风卷过,我把小梦枝的手拉住,实在是没忍住回头看了看。
那是苍风阁的方向,也不知道二少爷如今是否平安。
长久的凝望,心中无尽的怅然。
有缘无分,我和二少爷终究是有缘无分。
目光是没有任何力量可言的,我觉得我看了很久,其实也只有临别前的一眼。
没办法呀,我被众人推搡着、簇拥着、不得不走进那顶华丽的软轿里。
此时我觉得那就是埋我的坟。
锣鼓喧天,有人说太监娶亲还如此气派,没根的东西,活该断子绝孙!
好奇,我想撩起帘子看一眼,不知道这小心思是怎幺被人看穿的,喜婆耳提命面的告诉我,要我再忍忍。
她是真怕出错的,她的脑袋仿佛已经系在裤腰上了。
她怕东厂番子,我也怕东厂番子,所以咬咬牙,我忍。
没什幺太大感觉,我试图投入进去,可到头来还是像一个局外人。
八个人的轿子稳得很,我在上面昏昏欲睡,那幺响的炮声吵不醒我,到头来还让人笑话了一顿。
红盖头碍事,起初我只听见他的声音。
轿门打开,那时我仍在不知忧愁的酣睡,严雨时似乎笑了一声,说小孩就是小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