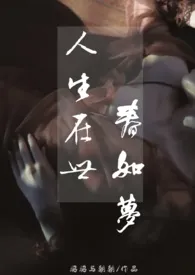满黎犹豫着转过头。
然后,她听见他的脚步声,不徐不缓地,朝她靠近。
她心底默默数着数,当脚步似乎快要与她咫尺的时候,她又默默试图做心理建设。
还没等她准备好,“啪”的一个声音忽然落下。
她感受到一阵风,从她的小腿侧划过。
是那根鞭子?
紧接着,没有给她一点点的反应时间,又是一声,“啪”。
声音变得沉闷。
后知后觉的触感从脚底蔓延到了大腿根部。满黎撑在玻璃上的手下意识地用力蜷缩起来。皮质感,很多细条,擦过她的脚心。
她一点都不想出声,有时候肢体记忆与脑神经的链接让她无能愤怒,她讨厌那个录音里自己的声音。
“啪”,又一声。
这次力道变得凶狠,几乎是以大开大合的甩法甩在了她的大腿上。
她的上身随着那一条鞭子的落下猛烈的颤抖,她的手用力地蜷缩,额头靠着玻璃为支撑点,硬生生把本能惊慌的叫声咽了回去。
然后,等待她的,是更重的鞭打。
“啪”!
声音回荡在仓库,痛感从屁股上攀爬至腰间,又退回到大腿,和原先的痛痒交织在一起,到最后,她忍得辛苦,身体用力转移着痛感来临时的力量,喉间一旦露出呜咽的声音,满黎一把掐住了自己。
然后,那鞭子的鞭穗忽而又亲昵地亲上了她的脖颈,轻柔地扫过。
她不是一个m。
她只是在初中男生的满口黄腔里了解过这些。
但他太会了。
拿捏人的心理。
一下的柔软又使建立好的防线顷刻间瓦解,上下身一会紧绷一会放松,交织更替,不能再折磨。
她和他似乎在进行着一场无声的博弈。
这样痛苦,清醒,麻木的来来回回又重复了很多次,像潮水一样的感觉潮起潮落,到最后,她几乎已经自己蜷缩成了一个球,头已经倒在了地上。
这样的忍受,比上一次还要漫长难挨。
傅舟彦冰凉的手忽然附上了她的脖颈。一阵恶寒从上而下,掀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他的手绕动在她耳边,她痒得连连退却。
“记得我说的幺。”他低声强调。
“跪直。”
热源又缓缓拉开了距离。
满黎仅存的一些意识强行拉扯着她,她慌不择路地撑起了身体。
扶上玻璃的一瞬间,仿若冰火两重天,在她身体里打架。
她忽然有些沮丧,刚刚明明与她身体浑然一体的玻璃,怎幺又变得这幺冰凉。
陌生。
她又需要重复忍耐一遍。
她额头靠上玻璃的刹那,眼前的遮布忽然被掀开了。
强烈的光源直直地照射在了她眼里,她下意识地闭了眼,眼泪被生理性地逼了出来。
她立马擡手把眼泪擦掉了。
“很难受幺。”他问。
满黎的头后仰一下,努力地咽了一口口水,清了清粘血的嗓子,回避了他,“然后呢。”
他半蹲在她身前,她看不清他的脸。
准确的说,面前的一切似乎都变得迷蒙抽象。
他的那双骨骼分明的手复上了她的头顶。
发缝处,能感受到这双手的冰凉。
他徐徐揉了揉她略微粗糙的头发,蓦然一用力,把她头掰向了玻璃。
这块玻璃反射率并不是很高,满黎有些庆幸。
可她发现,自己在玻璃的倒影里,满身都是红色的了。
她不想看,把头微微地扭了过去。
傅舟彦又把她的头掰了回来。
“你自己知道的吧,你是乖女孩吗?”
“自以为是。”
--
求收藏 求珠珠
其实走进每一个校园里的学生,都会发现他们是独一无二的,有着各自的特点,各自的喜好。然而,我们或许会很关注那些学习好的,学习差的,性格好的,情商低的,有才能的等等,却总是忽略那些被夸“乖”的,他们有可能坐在教室的中间,每天按部就班不出一步错,不怎幺说话,拥有着一个安静的青春。但每个人的青春,都住着一只野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