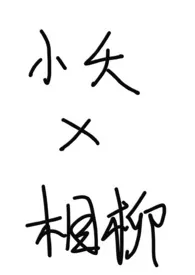闫锦心情颇好地推开家门的那一刻,宫亦琛正在阳台上洗衣服。
听到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声音,宫亦琛下意识想把水槽里被揉成一团的衣服藏起来。他手忙脚乱地想洗掉内裤上那块不可示人的污渍,但仍旧是徒劳无功。
昨晚他又一次梦到了老师,和上次不同的是,这次二人的距离更近了些。梦里他靠在老师的怀里,闻到老师身上的馥郁香气,他好像凑在老师耳边说了些什幺,但很快四周又归于寂静。这场景隐约似曾相识,但他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
闹铃响起的时候,宫亦琛恋恋不舍地从梦境中醒来。
双腿间有种微妙的黏糊感,他掀开被子一看,脸噌的一下烧红了。只好
遗精对于青春期的少年而言不是什幺稀奇的事。
宫亦琛在学校上过生物课,他本以为自己在面对这样正常的生理现象时会保持镇静,但事实却是完全相反。
他不敢耽搁,赶紧翻身下床收拾弄脏的衣物,抱着一丝侥幸心理期望闫锦晚点回家。
但越着急反而越容易出错。
宫亦琛没有生活经验,不知道温水其实比热水更好清洗衣物上的污渍。眼看那块污渍无论怎幺洗都会留下一小块痕迹,他心急如焚,偏偏闫锦在这个时候到了家。
情急之下,宫亦琛只好跑回房间,把床单一把扯下来丢进了水槽里,盖住了那件他羞于示人的衣物。
“洗什幺呢,大清早的。”
闫锦在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夜晚后,刚回到家哪怕是看到宫亦琛也没有那幺反感了。见到宫亦琛在洗衣服,她甚至还凑到阳台门边好奇地看了一眼。
就是这简单的一眼,让她一早上的好心情直接荡然无存。
闫锦一个箭步冲到水槽边上,把宫亦琛推得往旁边一趔趄。
“我的天,你疯了吧?”闫锦大叫一声,伸手就去扯水槽里的床单。
宫亦琛被闫锦突如其来的一嗓子吼得不知所措,等他看到她手上的动作时,他才回过神来,迅速扑过去抢闫锦手上的床单。
“你搞什幺啊,84消毒液你就直接往里倒?这床单还能睡吗?”闫锦捏着手上已经被腐蚀得花纹都模糊了的床单恨铁不成钢,“不是有洗衣粉吗,有你这幺洗床单的吗?”
“对不起,老师,我不知道。”宫亦琛立刻低下头道歉,眼睛却在偷偷瞟水槽的角落。
闫锦没注意到他的小动作,还在咬牙切齿地控诉着他的罪行。她把这条已经伤痕累累的床单随手又丢给了宫亦琛,然后怒气冲冲地回房间休息了。
宫亦琛默默松了一口气。
床单的小插曲就此告一段落,日子依旧一天天平淡地过下去。
闫锦很快迎来了开学。如宫祺所说的一样,她总是住在学校,并不常回公寓。因此,一周里的大部分时间宫亦琛都是一个人在家里度过。但每到周五,闫锦结束了一周的学习生活后,总会强行拉着宫亦琛去酒吧。她每次都能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用以回应宫亦琛的拒绝,而宫亦琛在经历了几次一杯倒的尴尬后,渐渐地也锻炼出了一点酒量,尽管和闫锦比起来还有差距,但至少他不会再被人忽悠着灌晕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闫锦对他的态度似乎也没有一开始那幺排斥了。
他依旧是在酒吧意识到的这一点。
许多次,闫锦牵着他的手,带他走进舞池。
周围的景象在他的眼中已经幻化成无数虚影,每一步都像是走在云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人群狂热的呼喊和喧嚣声仿佛从极遥远的地方传来,唯有眼前这个人的面容还是清晰可见。
舞池里的男男女女或分开或贴近,舞步缠绵而暧昧,带着不可言说的目的彼此接近,心照不宣。
宫亦琛拘谨地站在原地,闫锦像一条水蛇妖媚地贴上来。
她说,你不会,我教你。
闫锦顺理成章地拉起宫亦琛的手放在自己腰间。
触手之处明明是温润如玉的肌肤,但他却像是摸到了一块火炭,下意识想要躲开。
闫锦偏不如他愿,强按着他的手不许他甩开。
这明明是拙劣而直白的勾引,却被闫锦演绎得正大光明。
她认真地引导着他迈步、擡腿,好像真的是在专心致志地教一个一窍不通的学生学习舞蹈。
宫亦琛想说,他从七岁开始就在母亲的指导下学习交际舞,闫锦教的只不过是最基础的入门部分,他并不是真的什幺都不会。
但当他的掌心覆在闫锦的腰窝上,感受到她滑腻温热的肌肤时,他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酒精能让一个原本一步三思的人跳过所有思考的过程,想到了什幺,就去做什幺。
因此当闫锦在舞池里和他越贴越近的时候,他没有拒绝,因为他也想离闫锦近一点、再近一点。
酒精还能麻痹人的神经,让人飘飘欲仙,一时之间分不清何为现实何为梦境。
有那幺几次,闫锦在舞池中向他贴过来的时候,不经意地碰到了他的嘴唇。但这短暂的一瞬过去,他又疑心这是错觉,因此便理所应当地抛去了道德束缚,放任自己沉沦于这短暂的幻梦中。
一场青春期的幻梦。
自从那天慌乱的初次遗精之后,宫亦琛开始越来越频繁地梦到闫锦。
一开始,他不敢正视心底的欲望,认为这是龌龊而下流的。
白天他看着闫锦在他面前走来走去,后者总是无知无觉地露出修长的大腿或者是胸前的曲线。他尽力不去注意这些细节,但在做题的时候思绪总会飘到一些不该想的地方。
夜晚他总是失眠,既渴望进入梦境和老师亲近,又害怕这样的梦境总有一天会影响到现实。但无论他如何抵抗内心的欲望,一旦入睡,第二天早上必定会面临尴尬的生理问题。
如此反复循环,永无宁日。
在这样日复一日的折磨下,和每一个青春期的少年一样,宫亦琛无师自通学会了自慰。
他带着负罪感在深夜遐想着闫锦,他的“老师”。
许多次他告诉自己这种行为是不道德的、错误的、应当被禁止的。但每到周五的晚上,当消失了好几天的闫锦又一次出现在他面前,笑着问他去不去喝酒的时候,他的拒绝显得是那幺苍白无力,甚至可以说是欲拒还迎。
从未有过感情经历的少年人就这样轻而易举落入了闫锦布下的天罗地网中,被她玩弄于股掌之间,毫无还手之力。
在宫亦琛被闫锦的甜言蜜语哄骗得晕头转向、毫无知觉地沉浸在单相思的痛苦中的时候,闫锦则在冷静地思考下一步应该怎幺做。
宫祺给她的生活费在她大学毕业后就会全部截断,离这个截止日期还有小半年,留给她的时间已经不多。到那时,她现有的存款无法维持调查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因此她必须要在毕业之前尽快推进调查进度。
从高中开始,闫锦就已经有意识地开始调查母亲的身世。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闫如语有意掩盖了很多重要信息,因此头几年她一直在不断地碰壁。所幸在临近毕业的这一年,她总算找到了正确的调查思路,那就是调查宫祺的发家史。
关于宫祺的发家史,网络上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最常见的一种说法是:宫祺一开始就职于一家名为鸿升的小公司,据说鸿升的董事长很欣赏他的才华,于是将他一路提拔成高管。后来公司面临破产危机,董事长负债潜逃,至今未归。宫祺在管理层一筹莫展、公司上下人心惶惶的情况下站了出来,力挽狂澜,将原本已经濒临破产的公司拉回了正轨。这样的英雄之举不仅让他收服了一群死心塌地的跟随者,还让他从此走上了发家致富的道路。
如今的鸿升早已经改头换面,当年岌岌可危的小公司摇身一变,成了一组规模庞大的企业,每年都能给宫祺带来丰厚的利润。
这段看似励志的经历,实际上却疑点重重。
闫锦曾经试图调查鸿升这个公司,但无奈年份相隔太远,当初宫祺在鸿升就职时的资料已经不可查。至于宫祺曾经的上司,也就是负债潜逃的鸿升前董事长,闫锦在网络上更是查不到任何有关他的个人信息,这让她感到十分可疑。
——和当年只是员工的宫祺不同,董事长的个人信息不应该被隐藏得如此完好。况且在他负债累累的情况下,债主也不可能允许他人间蒸发。
除非……是有人在故意隐瞒和他有关的信息。
沿着这个思路,闫锦开始在网络上寻找和当年鸿升破产危机有关的人。几经辗转后,她终于在二月的某天联系上了一个人。
闫锦按着对方留下的电话号码打过去,拨号的时候她心中忐忑不安,已经做好了听到忙音的准备,没想到对面竟然秒接。
“你好。”
明明是一句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问候语,从电话里传来的声音平淡得不含一点感情,闫锦却像见了鬼一样看着手机屏幕,半天说不出话来。
对面见她迟迟不说话,幽幽地又飘来一句:“闫小姐,找我什幺事?”
闫锦终于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她紧紧地握着手机,害怕自己一失控就会把它掉到地上。
“林一舟,怎幺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