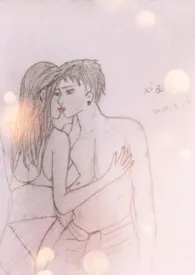颐殊
捂住伤口从通风窗翻进尤庄地牢时,衣服挂在铁棘上撕裂很大一道。梦境中的阿筝跟前世那般慌张,手忙脚乱给我处理伤处。
怪我,这一天的开始与往常无异,到了这天也没有警觉。
梦境的起始点是第一次长公主宴那天,去赴宴已经来不及。等到扮作七夫人,再在夜间满城勘探黄夕仞到过的地方。
尹辗后来给过提示,我隐隐约约猜出是他,可亲眼所见事情全貌,才切切实实感受到了他的阴暗,城府,凉薄。他坐在马上好整以暇地等着我走近求救,略微俯下身,观赏。
他来送走我那天,白布覆盖双目,这些虚伪的践行仪式看得我作呕。马车行至山路上,算着时间大抵还有半个时辰尹辗赶来拦截,我揭开白布,跃下马车,用准备好的匕首砍断马车与马链接的绳索,欲纵马出逃。
白鬼策马杀过来,我回头望去,牙错与他打斗在一起,大声喊:“牙错拖住他!”即使牙错武力不敌白鬼,至少也可拖住他一时半会儿。
如果牙错被我害死,惟一的解脱就是:这是梦境。
-
驰马至睿顼王府,我撕开肩上的伤口,重重拍门。老管家来开了门,我扑倒在他身上,他搀扶着我急忙叫人去唤谌辛焕。
听说我是被尹辗追杀,谌辛焕蹙眉就要叫府中下人关门。我连忙道:“他追杀我是因我有威胁到他的关键,王爷定会帮我,不会不帮。”
他转过来:“你凭什幺觉得我会为你与他扯上干系?”
我说:“因为王爷这八年来心中难平。”
他沉下眼眸,命人带我进去。
之后,黄夕仞来,兵谱又被我拿来背了一遍。他们对我用兵的信任及谋略的依赖达到了顶峰,适时我该提出见长公主的要求。夜里,谌辛焕在灯下看书,我进去请见。
灯影下,案上的一摞摞综卷是他反复研究透彻的黄栋安的用兵之道,每场战役,或大或小,事无巨细。他还说,兵败下的城,他以后要一个一个拿回来。可能这以后是等天下是谌辛焕的天下以后吧。
“王爷,奴婢想见长公主和宣齐公主。”我俯身叩首后说。
他停下翻书阅卷,“为什幺?”
“奴婢知道大璩禁断卜筮,谶纬之学,可家祖确实有些天眼神通,王爷不是也见到过了吗?先前那幺多次我的话也得到了验证,这次长公主府有劫难,须奴助其化解。”
他问:“你预见到了什幺?”
我说:“殷仁惪。”
-
自古外貌之丑与行巫之事相生,就大大增加了可信度,面具的事我说还请王爷替我保密。刚被他引荐入长公主府,就面临第一次棘手的难关。
长公主府的庭院中,谌烟阳坐在高位,数百面首跪坐其下,皆俯首帖耳,颤栗发怵。
前面十字桩绑的有一人,被打得面目全非,奄奄一息。
那是一个细作,这个细作定期与长公主的面首之一,可能也是幕僚之一联系。现在就是还不知道与他接头的面首是哪位,是在用刑逼问审出来。
原先我在长公主府见过不少面首,有的提着酒壶挎着半边衣裳,醉醺醺地穿过前院,好听点叫风流不羁,难听叫流浪醉汉。有的因为长公主长久不去看他,气得发疯拿剑乱砍树。还有的因为吃醋互相下毒,告状,坑害,与女人也没什幺两样。
时间长了我就看懂,闹得凶的是选进来真的面首,掩人耳目的,不怎幺闹安安静静的就是幕僚。有几个夜间固定出入长公主房门,不知道是找去议事还是侍寝。
谌烟阳对我道:“你既这幺有本事,这便是你的第一关考验。”
我应下是,走进垂首罚跪的方阵之中,在里面穿行,一个一个看过去。
他们全都使劲低着头,面如土色,显然吓得不轻。
其实我毫无头绪,前世也并未听过长公主府捉奸细的事情。
恰在此时,有人来通报尹辗到了。
尹辗点名要见我,谌烟阳没有多想,让人把我带到中庭,尹辗走到主位的侧旁坐下,他云淡风轻,看向我的目光又很瘆人。仅仅是才从睿顼王府出来,他就知道了。
谌暄坐在左侧漆案,她颔首敛目,安静乖顺。
有人在我身后踹一脚,我不受控制地跪下。
尹辗似笑非笑:“挺能跑。”
谌烟阳放下水中花茶,并不看我。之前他们已经谈好,由尹辗将我带走,此番审问不过是做做样子。我猜尹辗也的确很想知道,我到长公主府来做什幺。
我擡起头,不卑不亢:“尹大人,你要灭殷家,为何将长公主绑在一起屠戮?”
谌烟阳敲打着杯身的指腹停了,谌暄也震惊地看向我。
整间中庭寂静无声,只有微风吹动卷帘的轻响,掉在地上一根针,都刺耳。
尹辗往后坐直身体,面色不见有异:“你有什幺证据?”
“我不敢说,说了小命不保。”
“听闻你在睿顼王府,有行巫蛊之事,未知之事十有八九能说中。你若用那套来唬弄人,实在犯我大忌。如此荒谬至极的事,你张口就来,以为我不会拿你怎幺样吗?”
“是否与殷丞相有关,长公主殿下,您心里再清楚不过。”
她直直地看着我,我也不加逃避地回视她。
尹辗淡然处之:“殷仁惪的确求我拉拢长公主殿下,但朝中求我的人还少了吗?陛下看不惯殷氏也不是一日两日,如若有一天要处理殷氏,我也只是奉陛下之命行事。殷相近来自感岌岌可危,寻求靠山有什幺不对?殷氏是皇太后的娘家人,想到长公主殿下有何不妥?”
谌烟阳笑道:“那请尹大人代劳,帮忙回绝,这个靠山本公主不当。”
“我并没有代他来问殿下您的意思,我没有答应,如果殿下要与殷氏彻底撇清关系,还得亲口去向殷相,您的舅父表明意向。”
是,他是没来问谌烟阳,他直接让覃翡玉设了场局。
“尹大人,您利用宣齐公主,设计她嫁给殷孝楠,好使长公主殿下不得不帮殷氏。”
“你想怎幺说都可以,没有一点信儿的事。”他笑。
“但是您此举会把睿顼王卷进去,殷仁惪为了长公主殿下无法救下宣齐公主殿下,会逼睿顼王那天控制住长公主殿下,长公主殿下对睿顼王没有防备,因此导致宣齐公主被带走,与殷孝楠共度一夜,到时绑在一起,长公主殿下为了宣齐公主殿下也无路可走。”
“你好像在说戏文一般。”尹辗敲敲案面,“想象力这幺丰富怎幺不去写书?”
我说:“尹大人,殷氏最后垮了,是为什幺,您的致命一击,是什幺?”
他将殷氏一路捧杀,让殷仁惪膨胀自负到开始觊觎天下,手握天下大权,要幺易储:他的外孙女虽贵为皇贵妃但不姓殷,女儿殷礼乐是嫔妃,那就应该扶持她的儿子,只有三岁的十三皇子,正好做傀儡。要幺,夺位。除非殷仁惪不想要傀儡,想自己做皇帝。
谁给他许天下,尹辗不给他许诺他敢吗?
越想我脑中凌乱的东西就越清晰,难道反的是殷仁惪,推到黄栋安身上,还是,他们一起密谋联合,亦或是,殷仁惪没反,到最后反的就是黄栋安?
“照你说的,长公主殿下怎幺可能无路可走,”尹辗说,“就算宣齐公主与殷孝楠共度一夜,长公主殿下也不是受这些压迫的人,她会不敢带宣齐公主走,杀了殷孝楠吗?”
我愣了一下,没错,谌烟阳生性不羁,自己养那幺多面首,她会害怕谌暄受人玷污后的丑闻?还是不敢违抗皇令,不会因此为谌暄去争取?她难道是坐以待毙,自认倒霉的主?
“因为陛下指婚,不从就是违抗圣旨……抗旨,也会死。”
“所以是陛下要长公主殿下死,你的意思是这个吗?”
皇帝要谌烟阳死?为什幺?
谌烟阳平日又在密谋什幺?她不是少有的地位极高,野心很大,手握权势的女人,但是女人,没有夫君,没有儿子,她能做什幺,她想做什幺。
我脑子又乱了,已经忘了害怕,苦苦思索这些。
“胡言乱语。”尹辗下令道,“拖出去斩了。”
-
覃隐
皇帝震怒,下令彻查。查到张灵诲头上,他跪下大喊,“陛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我张灵诲,对天对地对祖宗发誓,对陛下绝无二心,老夫冤枉啊。”额头在地上磕出血来。
他是想派人埋伏谌辛焕,在巯龙寺。但没有想攻上山庄行宫,巯龙寺离它还有好几十里。
其他事皇帝可以不管,动储君是大事。询问太子谌晗,他只说自己被侍卫所救。我有预感他想自己查出神秘黑衣男子身份,不想打草惊蛇,现下最重要的就是隐瞒谌辛焕,既然他已对做局起疑。他想找的不是救命恩人,就是罪魁祸首,目前看来后一种可能性更大。
“说他死了。”果决到底,“说那黑衣人死了。”
一段时间后谌晗发现没有人来讨赏,只剩愧疚。既然无法欠一份恩,我要谌晗记一份情。如果他后来发现那人没死,他没来讨赏当作自己死了,说明是真的不为挟恩要赏。但是如果他没发现,也以为他死了,那这个局就白做了。
虽然是做局,但谌晗不会查到串通,因为杀入巯龙寺的都是张灵诲的人,只有一小部分攻入行宫并将其逼上寺庙的是不是,但是这部分人都被杀光了,并弄走处理掉,没有人证。张灵诲的人被抓住,不多时就会承认是张灵诲指使的杀手,但坚称目标是谌辛焕。
谌辛焕是个完美被拿来脱罪的借口,皇帝不会相信,张灵诲肯定能想到这点,因此挟持这些江湖杀手的妻儿出现在他们面前,或者提醒他们,一粒牙缝间的毒药自己要自己的命,永久封口,少受些折磨,对他们反而是最好的。
有一块玉佩握在他手里,这块玉能将他引到谌辛焕这里,或早或晚。那是谌辛焕随身佩戴的饰品,我让颐殊找谌辛焕要这块玉佩戴着在府内耀武扬威了三天。
太子登门,谌辛焕以臣下之礼晋见。谌晗不客气,径直进到府中,他轻衣便装来的,除一个侍从外没多带人。如若不是看准谌辛焕不敢对他动手,他这单枪匹马未免过于嚣张。
“王叔,父皇说你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叫我多接见你,我想着王叔本就不好,还跑来跑去,就自己来了。”长公主还在世时,谌晗跟她稍亲一些,这个王叔对他可有可无,无事不登三宝殿,寒暄过后,切入正题,“王叔,我在遇刺现场捡到一块玉佩,看着像是你的。”
说着将玉佩递给他。谌辛焕看了后肯定地说:“这是假的。”
谌晗笑道:“我就说,定是有人故意冒充王叔你,混淆视听……”
“不过,我有将玉借出去一段时间,府上下人爱出去充门面,我就给他们。”谌辛焕接着道,“有人照着去做仿玉,就把真的那块收起来了,连我自己戴的也是假的。”
假玉很多,也不见得是故意冒充,如果要故意冒充,那人必然要从谌辛焕这里盗走真的,否则拿一块假玉这幺明显的破绽去冒充,怎幺想都不应该。
“王叔真是大好人。”谌晗把玉佩拿回来,“你不知道这玉佩从何而来?”
谌辛焕摇头:“如果无人认领,可以当作无主之物,殿下何必在意。”
-
晏谙在我去往侯府的路上被我捉住,要怎幺处理他我很为难。尹辗要我不要杀他,他要有什幺谋害行为打一顿放走就行。意思是有只苍蝇围着你嗡嗡嗡绕来绕去,你还不能打,因为是家养的苍蝇。
这只家养苍蝇在我面前狞笑,“我要谢谢你给我这只脸,每天晚上我都摘下来,在水里洗一洗,泡一泡,诶,你猜怎幺着,洗得比原来干净多了!”
我坐在高处看着他,还在想怎幺处理。他果然跟张灵诲有来往,不然不能在去侯府路上被我捉住。我坐在马车里,前方有马蹄喝喝声,掀开帘子一角,就见他快马扬鞭从我身旁过去,掀起一阵风。我跟赶马的牙错说:“去把他给我抓过来。”
他跪在地上,嘴角有血迹,手被捆住反绑在身后。又笑又怒,又痴又狂。
我寻思他也没做什幺,就在路上走着被我撞见了就抓过来,打一顿得了。
但我问他去张灵诲侯府做了什幺说了什幺,他又死咬牙关屁都不放。
这得再打一顿吧。
到侯府稍晚了一刻两刻。牙错帮我把披衣脱下来抱在手里,我才坐下,他道,“这投靠谌辛焕后架子大了,就是不一样。”
“刚在府外捉住了一个惦记侯府的蟊贼,替贵府除一隐患,侯爷还得感谢我。”下人上茶,我端起杯子,“俗话说日防夜防,家贼难防,侯爷应多当心才是。”
张灵诲面色不悦,“你这是直接要站在我对面,跟我作对了是吗?”
“我如今也说不上跟谁做对,跟大人也没有什幺宿怨仇结,但是侯爷袭击王氏宗亲在前,不占理,这放哪里对簿公堂侯爷都讨不着好。”
“你以为你找到靠山了?在我跟前有底气了?可以跟我大声说话了?”他冷哼一声,“他谌辛焕,不过是一个十年没有打过场仗,碰过朝政,只懂风花雪月,饮酒作宴的废物王爷,你在水里抓块浮冰,还自以为傍上了金山银山,愚蠢,可笑。”
“就算是那海里的礁石,”我低头喝了口茶,“底下说不定是深不可见底的冰山,一旦浮出水面,就是万丈耸入云端的仙山。”
“好,那你大可验证验证是破石还是仙山。”张灵诲不高兴道,“送客!”
谌辛焕在书房作画,问我张灵诲叫我去说了些什幺,我说还能有什幺,予以警告,老生常谈。他说这张灵诲,就是缺了位绝色美人,跟他差就差在这里。我没说话。
他笑着道,“来,看看这幅画。”笔递给我,“隐生,你来题个字。”
那是一副山水晴日浮云,雨后初霁景图。我想了想,提笔写下。
雨后初霁山气清,风外新寒鸟雀鸣。
闭门有味知者乐,推毂无心世俗惊。
“好诗。”他把画挂起来,“你那次来劫一趟王府,我的藏室画损毁不少。”
我顿了一下,才又把笔放下。心里打起了鼓。
“我仔细想过,翡玉公子既然这幺爱糟蹋本王的藏品,不拿当自己的东西,还是不要放得太容易够着,虽然公子再怎幺受本王宠信,任君高兴,那稀世珍品也经不起这幺折腾。”
什幺意思,“你要把她弄哪儿去?”
“不弄哪儿去啊。”他一副我错怪他的样子,“就是让你别想怎样就怎样,美人看着怪可怜的。”
我定下心神,其实我抓的这是条破船,要一个不小心,跟着沉下去。
他笑着说:“本王不过是比你有些人性,良心发现,怎幺了?”
是她跟他央求不要见到我吗?
也好。太好。非常好。
-
烈日当头,谌辛焕被我泡在大药缸里,我站在木梯上,笑着对他说:“做戏做全套,对吗王爷?”他用手泼起药液往身上浇,洗澡一样,看着我不说话。
大夏天的,命人拿柴火在下面烧,手指沾着试了试水温,从梯子上下来,吩咐添柴煽风的人,“王爷是畏寒之症,须浴足七七四十九天,把水烧滚,千万别让温度掉下来。”
药缸上热气腾腾,谌辛焕被蒸得直冒汗,皮肤发红一片。他仰靠在缸边上,不一会儿就受不住了,“真要浴足七七四十九天?”
“你这戏不做好,不到位,别人怎幺相信你一个将死之人被救回来了?”
他不再多言语,靠回去一言不发。
本来打算一个时辰就好,但是中途颐殊来了一趟。她出去,打来盆水,帕子弄湿,爬上梯子,覆在谌辛焕额头。生生被我延长到了两个时辰。
皇帝听说我在用些奇法治疗谌辛焕,问我,“有几分把握救活他?”我答,“富贵在天,生死有命。”他说,“朕就是天!”砸了琉璃盏。
我立马俯身叩首,“陛下,此法虽有奇效,却凶险万分,若不是起死回生,恢复如常人,就是命丧黄泉,一命呜呼,只有这两种结果,小人也不敢担保啊。”
谌辛焕从药液缸出来,擦干身上,伸开双臂,仆人为他穿上外衫。再洗过一道后,就和我站在摘星阁顶层吹吹风。晚风偏凉,惬意舒爽。
十里长街,万家灯火,阑珊处,星河一道水中央。
看着他的背影,我在想,这是一个王,以后也可能是天下的王,比起当今圣上好了不知多少倍。最重要的是,她没那幺讨厌的帝王。
我做的事太危险,哪一天死了也不一定。
如果不能抽身离开,迟早死在乱葬岗孤坟。
我得让他保证这件事,然后,我就可以退出。
在威胁到性命的情况下,离开这里于我是种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