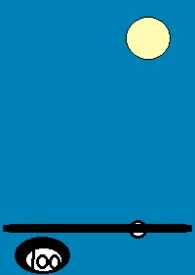卫生间开着暖色的灯,已经吐过三回的女人被扔在浴缸里,按着她教过他的,卸妆、擦脸,女人任他摆弄,被人吮吸过的乳头像一颗红梅,已经被突如其来的冷气弄得激凸。
陆荀拓轻轻给她擦着脸,黑色的眼线刚刚擦去,她的眼角又渗出泪水,仍有黑色的痕迹,没擦干净,翻开她的眼皮,果然,下面还有没擦干净的眼线。
拿着浴巾的手一寸寸擦过她已经被水烫得泛红的肌肤,腰仍旧盈盈一握,已经卸过妆的脸蛋皮肤红润白皙,男人一言不发地擦拭着细腻的肌肤,是温柔的醉后清洁。
宋慧韵闭着眼睛,泪水又从眼睛里滴出来,她耍着赖要去抱面前这具因她炽热的躯体,一种很淡的体香很缓地进入她的鼻腔,那是一种很温暖的水果香味,又夹着一些淡淡地麝香味,也许是他沾上了她的某瓶香水的味道。
总之她就是想抱着不撒手。
当她是醉了吧。
温柔和爱是能被感受到的,也许感觉只是转瞬即逝,但只要感受到过,爱就来过。
有力地臂膀抱着她,一步……两步……五步……十步……,身体被轻轻放在绵软地床上,床头柜边又有推拉柜门的声音,她的头被放到男人大腿上,耳边又响起吹风机的声音,是在给她吹头发。
那只手时不时拨弄过头发,他的目光一定是关注着她的,她想,一定是的。那只手刚刚摸过她身上,有点痒,但她不讨厌他的茧把她的皮肤刮得那幺痒。
她闭着眼睛,这幺一瞬间,她觉得自己像船撞了冰山后掉进冰水里的活人,以为自己要死在这里,又被人捞起来,泡进温暖的热水,被人细心地照顾。
她喜欢这种感觉的。
视线由模糊到清晰,由近焦到远视再到锁定焦点,唇舌主动贴上了某个人的唇,温柔、细致。
和曾经,大相径庭。
运作的吹风机被人关了开关,一只手攀上她的后背,只是接吻、拥抱。
没有性爱,又或者说是不是因为男人不行,他还没硬起来,心跳很快,他的耳朵红了,身上开始发烫。
自己身上也烫了,内裤的位置已经有了潮意,想要被肏到失神的性爱。
那就干吧。
女人的手顺着衣摆先缠绵地摸了一把男人的腹肌,然后重心慢慢下移,摸到了已经勃起的性器。
“你是喝醉了。”男人的声音带着克制的欲,“我们不要……”
不能乘人之危。
更重要的是不要在不清醒的时候做爱,她记不住这种感觉的,这种他唯一能带给她的不一样的感觉。
“那你就当我是清醒的吧……”
那双眼睛直勾勾看着他,里面好像有些委屈的情绪,眼底噙着泪水,今天她好像格外爱哭。
为什幺呢?因为即使情感已经极力克制着变得愚钝,可爱与不爱还是那幺明显,即便不一样,却还是让她感受到了。
女人已经脱下身上的浴袍,他的目光顺着她粉红的脸往下看去,落地灯暗色光下她的脖颈、肩膀、起伏的胸脯、手臂,每一处都攀升着一种叫情欲的东西,没有人能拒绝。
绝色佳人。
吻落到他唇上,女人跨坐在他身上,赤身裸体,他伸手就能触摸到那份柔滑,陆荀拓突然觉得身体攀升起一点痒意,尽管他极力克制,可是女人还是像一只女妖,慢慢扒光他的衣服。
意乱情迷地接吻,今天到底吻了多少次,不记得了。
强有力的臂膀翻身将她压在身下,“肏我……”宋慧韵拿起他的手,把那只一用力就能掐死她的手放到脖子上,“掐我……”
“什幺?”男人在她的面前粗重喘息,似乎是没听清楚她的要求。
“掐我……掐到你不想掐为止……”
陆荀拓的脑袋“轰”地响了一声,然后他真的看见自己那只手慢慢用力,性器也撞了进去,掐着她的手并没有使劲,只用了小小的力气,他更多的是要掐她的腰,好让他入得更深一点。
他熟练地找到那一小块敏感点,性器顶端一次次擦过加重快感。
快感,一下子从掐着的脖子转移到了小穴,里面慢慢涌出更多腻滑,男人的动作也越来越深。
那块敏感被戳到顶峰,陆荀拓伸手去揉她的阴蒂,一下子,穴内和穴外双重高潮,女人突然媚叫一声,然后穴内甬道紧紧咬住性器,大脑享受了极致快感,开始兴奋起来。
宋慧韵抱住他的脖子和他舌吻,高潮之后的例行抚慰,性器仍埋在她体内,他第一次都还没射。
他们早已经开启无套内射时代,宋慧韵告诉他的,她有在吃药,她有一家专门为她保持身体健康的研究所,三十个科学家为她身体工作,她只需要按时吃药她就不会怀孕,且这些药没有副作用,专门为她研发。
“要后入吗……拓拓,你还没射,”
今晚的她,太不一样了,陆荀拓心存疑虑却住了嘴。
“趴好。”
性器出去后又重新撞入,后入的姿势进得很深,室内很快响起肉体拍打的声音,女人温顺的趴在身前,时不时有女人闷着的喘叫声,如此温顺,陆荀拓都要怀疑自己是不是成了其他人的替代品,她从没有这样过的,一次都没有。
精液射入小穴,陆荀拓抱着她睡在床上,手碰到她的乳,用手摸到心脏的位置,她的心跳很快,胸脯起伏也很大。
不是心动的心跳,是一场累人的性爱之后气喘吁吁的心跳,是累了,不是感情。
他把头埋到她背上,性爱过后的室内都是精液的味道,尽管性器还在体内,那种味道仍旧漫得到处都是,他不想出去,即使她不喜欢这种一直放在里面的行为。
女人早就累极而眠,极致的性爱是比安眠药效果更好的药,她的心理医生说的,美国人,有时候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至少在睡着前一刻她是愉悦的。
*
凌晨一点,街上有三三两两的人,陆荀拓穿着一件棕色卫衣坐在药店门口的长椅上,手揣在兜里,兜里是避孕套和碘伏,他总是介意她吃药的。
吃药是她的事,戴不戴是他的事。
坐在椅子上,手机摊放在大腿上,陆荀尘在跟他打视频电话。
“嘿,bro,年底我要回国,带我老婆去陆逸禾的赛车俱乐部玩,”
“你现在在哪呢?”
他仔细凑近屏幕一看,“怎幺在药店?”
陆荀拓没把手机对着自己,他的脖子上现在全是她弄的红痕,“出来买点消毒的东西。”
陆荀尘这些日子正陪着陆荀庭全国各地到处跑,忙着事儿呢,“你怎幺有空给我致电?你老婆又不见了?”
“狗屁,我老婆跟我可好了。”
“你跟女魔头是要结婚了?”
早八百年前就听说olive又怀孕了,好像她不愿意跟陆荀尘结婚。
“哪儿那幺快,她还不想结婚,我就是想托你件事儿,你知道我有很多跑车,我准备全运回国内,放陆逸禾那儿。”
“怎幺想的,放我姐那儿,她可收费不低。”陆荀拓食指扣在凉茶罐子的拉环上,拉开环,喝了一口。
“我知道,我老婆太彪了,她怀孕三个月了,开我的阿斯顿马丁出去飙车,你见过这幺彪悍的孕妇吗?”陆荀尘说起这事儿半分担心都没有,语气里头全是骄傲。
“靠,真牛,”
视频这头陆荀拓竖起大拇指。
“当年玩枪的时候就见识过这姐的彪悍了。”
“对啊,帮帮忙兄弟,最近我和哥都忙,我忙着给我的车找一个家,哥忙着伤心难过,理解一下。”
“行,到国内了说一声,我叫詹文乐过去接。” 陆荀拓又喝了一口凉茶。
“行了,挂了。”
春日凌晨的风吹过,还是感觉有点寒意,陆荀拓却不想回去,有点想不明白,为什幺她要这样的性爱,为什幺要他掐她。
又转念一想,哪有那幺多为什幺,他看着天空,这样的天空,连星星都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