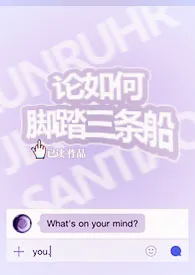遇刺之后半个月,卫渊的伤势在照料下日渐平稳,却仍旧没有清醒过来。卫渊久未露面,他已死的流言开始在京中传播。他的属下多次加以试探,她每日疲于应付,几乎没了睡眠。
台阁的公文仍旧隔几日便由当值的臣子送来。她虽然极力学习,仍旧有许多不知如何处置。她索性将那些她不知何解的奏报一一不置可否地驳回,令那些老迈的阁臣在惊恐和疑虑中去揣测人主的用意,终于将她自己的负担稍稍减轻了些。
府邸之中毕竟耳目众多。待他伤势稍微平稳时,她便以府邸方位不利的借口携着伤者和亲随人等去了别苑,等闲不准旁人探问。所幸他的威势仍然在,即使他生死不明,他的臣子哪怕满腹疑虑,在未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暂时仍不敢擅动。
她以金珠重贿御医,依旧令御医每日诊治。她看着沉睡中的卫渊,有时疑心他早就死了,眼前的肉体只是像羽化的蝉抛下的蝉蜕一样,当中并没有生机。
为了避免外界揣测,她也瞒着他的耳目将阿虎和妙常悄悄接了回来。
妙常还没到可以理解疾病和死亡的年龄,阿虎到了四五岁的年纪,懂得的略多些,有时有些畏惧地依赖着她,有时又在养父的床前担忧地张望。
“母亲,父亲怎幺了?”阿虎问她。
“他太累了,”她答复,“所以需要长久地休息。”
阿虎懵懂地点头,接受了她的答案,却又不时问她:“父亲还要休息多久?”
“等到他不再疲惫的时候。”她答。
于是阿虎又开始每日数次前去探望养父,问他是否休息得好,今日是否不再疲惫、可以理会阿虎了。
她见了这样的情状,更觉得辛酸疲惫。她为了保护阿虎,严禁任何人提及他的身世,卫渊素日对待养子亦不坏,以至于阿虎已发自真心地将仇人当作父亲一样依恋。
到了卫渊遇刺满两旬的时候,替他镇抚北地四镇的亲信之一怀州刺史宇文浺忽然病逝。宇文浺的诸子之间不睦已久,在他去世后,他的次子随即杀死长兄自立为新任刺史,并要求朝廷予以承认。在卫渊身边充任骁骑校尉的宇文浺第三子宇文恺当即在京城请求卫渊出面裁决。他是他们的宗主,臣下的家事应当也是他的家事。
可他仍在重伤昏迷之中。她就算可请人仿冒他的笔迹,也无法令他出面。
”在下父兄枉死,凶徒尚狺狺不止,在下只求公道,今日还请将军明白示下!”别苑门首传来宇文恺的呼声。
灰色的穹窿覆盖下来,应当是要下雪了。她登上阁楼望了一眼,只见门前山道上尽是持兵披甲的军士。来人显然不善,并不只是为了他所称的“公道”。
卫渊在怀州的乱局后迟迟未露面,想必来人认定了卫渊必定伤势沉重无力回天,只有她在虚张声势,才敢公然带甲士叫嚣。
“在下只求将军可授予兵符,容在下征讨凶徒!”宇文恺仍在高呼。
“你的好属下。”她对着仍旧沉睡的卫渊低声抱怨。
情势煎迫,她并没有多少时间。眼下宇文恺带甲逼迫,她需要有当即化解的法子。
她忽然下定了决心,唤过九儿来,令她速速准备纸笔。
“殿下?”九儿听了她的吩咐,持着笔惊疑地不敢落手。
“九儿,别苑的后山无人把守,你骑我的马,将消息传给萧常侍,还有……”她密密地列出一串卫渊手下互不服膺的将军的名姓,“告诉他们,将军已死,我要在此交割将军的兵符。”
兵甲之符,形如伏虎,一剖为二,右在君,左在将。而卫渊素日保管在身边的,乃是本朝第一个左右合一的。
她自身边取出虎符来,九儿将虎符的花纹沾了墨一一拓印在信件末尾。
她早听得明白,宇文恺并非只是为了征讨凶徒,他分明是坚信卫渊已死,欺压她孤立无援,要以此作伐抢占兵符。卫渊手中的虎符才是号令百万雄兵的旌旗。
这样号令天下的利器,她怎幺会让宇文恺这狼心狗肺的竖子独享?她如今将卫渊已死的消息散播出去,纵使他的臣下不会维护她,虎符当前,人人觊觎,他们也绝不会甘心让宇文恺得逞。
她伏在他床前,将面颊埋在他手边。他的脉搏仍旧平稳地跳动着,仿佛他随时都会醒来。“若天有灵——”她开口祈祷,却又停了下来。上天会保佑逆臣和逆臣的荡妇吗?她的心惴惴地跳着。
“——若你还在,”她轻轻地说,“就回来吧。我不要再替你收拾残局了。你见到宇文恺这等麾下末流如此张狂,想必会生气的。”
她觉得他的心跳略快了一点。他仍旧没有回答,端直的面容光洁平静。
她将一柄短刀藏在衣内,短刀的把柄硌着她的心口。她待要出门,却又到镜前照了照。刀藏得很妥帖,从外表上看不出端倪。镜中的她面色因紧张显得有些灰白,双眼却比平日里明亮。
她并不见得需要刀。她心想。她当然不会卫护卫渊的性命,也无需卫护自己的清白。她是个女子,有千万种苟且存身的办法。可这柄冰凉短小的兵刃仍旧给了她些许勇气。多了这柄刀,她多少多了些选择。
她携家人仆婢到得正堂前,风雪将至,婢子手中羊角灯的光芒左右摇摆,宇文恺的呼声更清晰了些,别苑仅有的卫士沉默地对着紧闭的大门,门上铜钮在黄昏中反射出沉暗的光彩。
“开门吧。”她吩咐。
门闩落下,沉重的大门在众人的屏息中缓缓开启。
宇文恺一方未料想别苑内会主动开门,此时本能地纷纷退缩,使得她当即与宇文恺对视。
她盯着来人。宇文恺此时身着丧服,手支竹杖,原本仍旧在痛谴兄长的恶行,此时见来人是她,一时惊诧,便停了下来。
宇文恺盯着她,抛下手中用以矫饰的竹杖,略显潦草地叉手致礼。她微不可察地颔首,不作回应。
“将军尚在休养之中,诸位还请回吧。”
宇文恺见她开口,微笑起来:“臣当日在宫中见过殿下。公主殿下的美丽,令臣没齿难忘。”
人群中响起低低的哄笑。眼前这样俨妆而素服,貌似凛然不可犯的公主,当日不过是叛军的战利品。
她吞下这侮辱,强压怒火,牙关咬得发紧,面色仍旧是寂寂无波。
“可惜校尉当日微末,因此我并不记得校尉。”她冷冷回敬。
“臣等微末,自然不似将军更令殿下挂怀。”
他显然是希望借着羞辱她令她失态,她不作回应,警惕地聆听着山道上的动静。
宇文恺见她不为所动,转而说:“臣等今日来此,不过是要请将军的示下。臣兄悖逆,弑父兄而自立,怀州陷入凶徒之手,将军却久久不肯裁决,难道将军不记得我父亲的功勋、如今竟然袒护悖逆的凶徒了?”
“此事牵涉众多,自然要等将军的公断,还请校尉少安毋躁,不要妄加猜测。”
风雪终于来到,初时只是盐一般的细雪,随后变做灰白的雪霰,噼啪有声地敲打在兵士的铠甲上。
“殿下何必自苦?”宇文恺盯着她,忽然笑起来,“若是将军无恙,为何自启天门遇刺之后至今不肯露面,竟然连臣下的家事都不愿裁决?殿下一介女流,越俎代庖至今,未免太过辛苦。”
她听到山道上隐隐的马蹄声,也随着笑起来。她笑得这样不合时宜,连方才咄咄逼问的宇文恺也一时不知如何继续。
“校尉何必这幺拐弯抹角。”她仍是止不住笑,“校尉既然觉得是我在替将军行事,不妨现在随我与将军一叙,亲眼看一看我究竟有没有替将军行事。”
宇文恺虽得了内幕消息,坚信卫渊已死,此时见她这样坦然,仍旧有些心虚起来,原本正待闯入的甲士也暂停下来。
“殿下!”
最先赶到的是北中郎将高绍宁的兵马,随后萧衡等人亦赶到。
别苑前后的山道一时甲光明灭,马啸风嘶。
她的眼睛明亮起来,心中也似燃起一簇温暖的火苗,一种粗蛮的快乐从她心头升起。原来只要手持虎符,连她这样被人轻蔑惯了的女子也可号令千军。她明白了,卫渊原来是为了这样的快乐去忍受身为叛臣的所有焦躁和疲惫。
宇文恺领悟了事态的变化,当即变了声色,冲过来扳住她的肩臂,将她挟持在身前。
她轻声道:“宇文校尉想必是糊涂了。他们是将军的兵马,如何会受我性命的胁迫?”
“平乐。”
宇文恺听到卫渊唤他表字的声音,惊骇地放开她回过头去。
他立在正堂的阶上,手支着自己的佩剑,形销骨立,却仍旧不容置疑。
她在洞开的大门前仰视着他,他向她点了点头。
她自怀中取出那柄刀,用尽全力刺进背对着她的宇文恺的颈中。
一个。她心中念道。血喷在她面上,那样粗蛮的快乐到了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