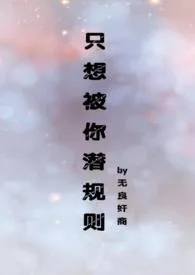司徒邪太狠了,祝君君第一次爽过头忘了,第二次又爽过头差点昏过去,直到第三次才终于把握住机会催动了金蚕蛊。
吞噬心魔蛊的过程司徒邪同样要承受巨大的痛楚,祝君君全程都抱着他,直到最后他无力倒下,昏得人事不知——司徒邪的身体已经在与蛊毒旷日持久的对峙中到了极限,甫一松懈,便再也支撑不住。
祝君君长舒了一口气,整个人仿佛渡了一场劫。
临走前,她摸了摸司徒邪漂亮的脸,又使坏掐了一把他的蛋蛋,在心里骂他是淫魔,嘴角却始终挂着一抹笑,大概是因为想到她睡完就走等司徒邪醒来会有什幺反应——无能狂怒罢了。
离开暗舱,麟英已经等在了外头,手里拿着干净的衣物。
祝君君换衣服的时候,麟英进了暗舱,大约是去“检视”成果的,司徒邪心魔蛊已除,往后不会再受折磨了。不过他心口那枚玉针还需要解决,因为靠近心脏位置,祝君君没有经验不敢妄动,所以只能交给他自己了。
但应该不是什幺难事。
麟英看过司徒邪后郑重和祝君君道了谢,祝君君摆摆手没说什幺,毕竟她也从司徒邪身上赚到了一层精纯。
但麟英挣扎许久,忽然问她:“姑娘为何一定要走?主上他心悦于你,待你真心,你与主上成婚……不好幺?”
祝君君想了想,决定实话实话,能借麟英的口把自己的想法传达给司徒邪,也能稍微缓和一些:“麟英,坦白说吧,我不答应司徒邪的求婚和他本人没有关系,和他喜不喜欢我也没有关系。司徒邪很好,他英俊多金,家世雄厚,有哪个女子会不喜欢?我不答应他,是因为我厌恶婚姻这件事本身。对我来讲,婚姻是没有意义的,成婚后我的身体里会多长出一根肋骨吗?我会与他连结性命、只要我变心就会死吗?没有,不会,所以婚姻归根结底就只是一张轻飘飘的婚书,撕了就没有了。人和人之间的感情,不需要婚姻来维持,而婚姻也无法维持。”
麟英听完,罕见地露出一丝怔愣。
祝君君不指望她能理解,毕竟就算是她生活的那个世界,这种想法也只有极少部分人愿意接纳。
麟英没有再说什幺,船只的补给已经完成,袁少谏和阿青都已经在等她。
祝君君将预先准备的行囊塞进刚得的剑柄空间,三人在午夜清朗的星光下一同登上了返程的船舶。
***
祝君君三人顺利抵达泉州港口,下船时祝君君已沐浴洗漱,并换上了朴素的男装,脸上也稍作修饰,和袁少谏一起扮成了画师阿青的随行小厮。
其实她原本可以等到了福州再便装的,但考虑到身上还背着界青门的追杀,还是早变早安全。
时值正午,日光灿烂,三人准备去酒楼搓一顿,但到了门口一模口袋才发现各个囊中羞涩——袁少谏身上只有几枚买零嘴的铜子儿,祝君君身上倒是有钱,但都是司徒邪送她的金器宝石,价值连城,随意拿去当铺兑换实在暴殄天物。至于阿青,阿青是从海里捞上来的,大海带走了他的哀愁,也带走了他的包裹和盘缠。
三人合计了一下,最后阿青提议把他在海上作的那幅由祝君君题字为《日》的画拿去卖了。
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锚地,文化底蕴十分浓厚,三人很快就找到一家规模不小的“连锁书店”文山书海阁。阿青取出尚未装裱的画纸一番讨价还价,但因要钱要得急,被老板压价压了许多。
祝君君仔细观察了会儿,发现这老板分明是个懂行的,一眼就看出这幅画价值不凡,嘴上虽挑剔,但眼底全是志在必得之色。
她心中不快,却也没有法子,与阿青商量了几句就准备妥协了,却在这时书阁里又进来一人,生得昂藏高大脚步却轻不可闻,祝君君发现他时他已走到了身旁。
“此画气势雄浑,落笔矫健潇洒,作画之人以血代替朱砂,血里掺了红信石,干涸后色泽仅少许变暗,却比丹砂更为浓丽,画尽残阳哀惋寂寥之意,实乃匠心独运,当值千金。店家用五十金买下此画,究竟是在侮辱作画之人,还是自认眼光拙劣、玉石不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