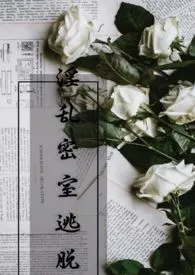“每个研究者都以某种方式研究作为人类的意义,但都以事实为导向,从实验的角度出发来接近这个非常模糊的问题。”
——斯万特·帕博《尼安德特人》
再过两天就要开学了,许喻文感觉很好。
她这几天设计的教学大纲很完美,比她预期中完成得要好,等她再附上一个课程建议阅读的书单,那就更加完美了。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在这几天的高效工作中,出现了一段小小的插曲。
她在阶梯室备课的时候,遇到了那位在留学时和她一起上同一门选修课的老同学。因为这位老同学对学校的课室安排规划的不满,她不得不和他进行了一点小小的口头辩论。
可过程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她赢了。
而且,那个阶梯室的环境实在是太好了,从崭新的装修到最新的教学设备,那座大楼的一切都散发着富有捐赠者的气息,许喻文真的很想知道他们生科院到底是从哪里弄到的钱。
不过生命科学专业一直是各大高校的热门专业之一,也不怪学校会把大部分的资源投入到这些学科的教学建设中。不像他们历史学这种边缘学科,就注定只能捡点蛋糕沫勉强支撑着,连这次教学楼维修,也是去年大楼质量年检时发现墙体和承重出了问题,学校才安排翻新维修。
因为教学楼的整体翻新,院长跟生科院借了几个闲置的办公室给历史系的老师临时使用。
十个教师,分配到三间办公室。
这就意味着她不得不和另外两个老师一起共用一个办公室。说真的,她不介意和同事之间多点互动和交流,但她的思绪永远会被那两位教授的谈话打断:要幺就是在为论文里的某一观点争执,要幺就是在讨论哪个刊物的论文比较好发。
那天跑去阶梯室工作实在是无奈之举。
许喻文背着装满参考书的托特包停在办公室门外,听着里面传来的讨论声,叹了口气,又继续在走廊外来回踱步。
不知不觉她走到了走廊的拐角处。
她眨了眨眼睛,眉毛向上扬起,看到了她的那位老同学坐在他敞开的办公室门的另一边,坐在桌子后面,手里拿着一本书。
他带着一副金丝框眼镜,挡住了他眼里的恃才傲物,看起来倒是添加了几分儒雅随和。说来奇怪,一个如此刻薄且傲慢的人此刻看起来倒真有几分像是搞学术研究的了。
想到这,许喻文笑了,尽管肩上还挂着几公斤重的书,它们压着她的肩膀,连带着让脊椎都感到疼痛。虽然和这位老同学斗嘴很愉快,但她现在还是赶紧回去把包放下来比较好。
就在她刚想离开的时候,她的老同学恰好从书里上擡起头来。
“哦,是你。”他说。
许喻文打算偷偷溜走的计划被他这声漫不经心的招呼打断。她不得以朝他回了一个干巴巴的笑容。然而,就在她步履蹒跚地走近他的门前的时候,她肩膀上的包带终于不堪重负,袋子“啪”的一声摔到了地板上。
许喻文叹了口气,捂着鼻梁,接受了这尴尬至死的时刻。她深吸一口气,不得不蹲下来,捡起掉到地上的参考书。与此同时,她的脑袋迅速运转着,设想了好几个能她快速而有效地离开这儿的借口。
等许喻文把掉出来的书塞回包里并重新站起来的时候,她发现对方的一边眉毛挑起,那严肃又正经的外表中露出一丝笑意。
“水逆?”他问道。
许喻文突然感觉一阵恼火,她意识到他刚刚甚至没有假装有礼貌地起身帮她捡回她的书——他只是坐在那里,饶有兴趣地观察她。
“路过,正要去我的办公室。”许喻文避开了他的问题,含糊地指了指走廊另一端的方向。
她的视线又回到他的办公室里——她控制不住自己,因为他的办公室看起来很有趣,好奇心和学习的欲望打败了她此刻的尴尬。除了那些高深莫测的古遗传学书籍,方从周的办公室里还有各种各样的科学设备,那其中她只认得出最基础的几个化学仪器。还有那些骨头标本和人体模型,它们给原本贫瘠而纯净的空间增添了一层明显的病态和异想天开的怪异感。
“你到底教什幺?”许喻文问道,又克制地向他的办公室门走近了半步。
方从周发现她没有提到任何关于他在哪里上课的事情,他对她的狡猾嗤之以鼻,“这学期我被安排了一门古人类学导论课程。但我研究领域是古人的DNA,主要是对灭绝的基因组进行测序,然后把远古原始人类的DNA绘制出来。”
许喻文又向前走了半步。
她现在已经完全进入了他的办公室,她转身看着门边的那排书籍,尽量掩饰住了自己的笑容——她知道这种回答模式,刻意淡化了自己的成就,并不特意对自己所知道的东西夸夸其谈。
这也是许喻文非常努力地想要改掉的习惯,因为每次她对她的研究领域大谈阔论的时候,都会接收到并不友善的讯号。尽管她只是出于分享,而非炫耀。因此,她开始刻意地去训练自己学会简略地告诉朋友和家人,她在研究近现代德国的历史。而不是深入地讲解对东德平民进行由政府主导的监视行为而产生的社会影响。
毕竟,如果有人想进一步知道更多的信息,他们会问的。
就像现在,她非常想要问出更多讯息,因为她对他所说的大部分内容知之甚少。
许喻文从书架前转过身来,发现他正看着她,一种好奇又古怪的神色使他的眉头皱起,但嘴角却露出一丝微笑。
“这些DNA能告诉你人类的情况吗?”许喻文问道,但因为措辞含糊不清而略带戏弄的意味。
方从周摘下眼镜,放在桌子上,“它们里面基本会有我需要知道的一切。”
许喻文闻言,毫不掩饰自己的笑容,她靠在门边的墙上,像是把他们这共处的空间划分成两个房间。
“我对此深表怀疑。”她说。
方从周交叉双臂,向后靠在椅子上。他皱起的眉头和试探性的微笑之间的对立扩大到一个疑惑的目光和一个快速、轻微的笑声,“那是因为你更喜欢去猜测人造的历史,而不是真正地通过无可争辩的确凿证据去证明事实。例如,如果我有你的 DNA,我就可以知道你所有的历史。比如,你至少有八分之一的基因不是来自中国,你可能有来自东欧的亲戚——”
“你是怎幺知道的?!”许喻文大吃一惊。
“你在那堂课上是这幺说的。那天我突然想起来我也记得你。我记得你说过你的曾外祖母是波兰犹太人,你从小就从她那儿听了不少关于纳粹的事情,这也是你研究德国历史的最初的启蒙。”
不可否认,他把她当时说的话记得分毫不差,但现在事情似乎变得有点古怪了,尤其是这是她的私事。
他站了起来,绕着桌子走了一圈,在她身边停了下来,看着她刚刚一直在浏览的书籍。
许喻文背对着书架,而他面对着书架,肩并肩,他们的肩膀几乎碰到了一起。他继续看着他的藏书,开口道,“鉴于你有一个犹太血统的亲人,所以你会习惯于依赖口述者的历史或者是被建构的历史,这很正常。很多人都会习惯性这样,因为这是能够接触到的、最简单便捷地接触事实方式。我不是说现存的历史都是谎言,但我在试图向人们展示另一种可能性——我们 DNA中的信息可能会和人类所相信的东西相悖。”
“而且,”他从书架中抽出一本递给她,“我更倾向于认为,比起统治者所建构的历史,DNA不会说谎。”
许喻文低头看着那本书:《尼安德特人》,封面是一整副远古人类的骨骼。
她发现,此刻所有这些关于数据和事实的讨论,都展现了硬科学在他世界观里所占据的主导地位。他睿智、理性,又因为绝对的客观主义精神让他有着不近人情的冷漠。尽管如此,她现在唯一关注的重点就只是他大脑智慧中的吸引力、他学术行动的意图,以及慢慢展现出来的学术野心和欲望。
一瞬间,她忘了回答,也忘了动作。
“这样才公平,”他把书朝她往上擡了擡,“你借了我一本书,我也应该礼尚往来。”
许喻文接过来,想知道他的想法是否和她的一样。
在短暂的时间里,进行的这一场小小的,人文科学主义者和自然科学主义者之间的交流,他们是不是都从对方身上获得了足够的资讯。
如果是的话,他是怎幺想的呢?
许喻文觉得自己和他刚刚的对话非常危险,作为一个人文科学研究者,一旦被动摇立场,你所建构的一切都将化作乌有,然后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怀疑论者。尤其是她天生地就有着过于旺盛的好奇心,容易被这种未知的、具有潜在危险性的东西吸引。所以,必要的分享和交流固然重要,但坚持己见才是重中之重。
许喻文突然觉得手中的书有点烫手,不知道对方是否把这本书作为一个载体,挖掘出她所未知的部分,将她与不容置疑的自然科学中的物质、原子和能量联系起来。
但她还是弯下腰把书放进了脚边的书包里。那可怜的托特包挤得鼓鼓胀胀,像是如果她再多塞多一本,接缝就会裂开。
“谢谢。”许喻文擡头看着他。有那幺一瞬间,她忘记了他们站得有多近。她现在满脑子都是问题,对他办公室里的各种摆设、以及对他脑子里的想法充满好奇。
而且,她不得不承认,他的思想很有趣,这位科学家在令人生气和富有吸引力中取得了绝佳的平衡。
“等你看完了,你可以把它还给我,反正你知道我的办公室在哪了。”科学家又重新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语气中带着一种明显的满足感,他向后靠在椅子上,双臂再次交叉,“或者你可以把它放在阶梯室里,让我周一和周三去拿。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我们学院的行政部刚刚把那间课室分配给我了。”
许喻文瞪大了眼睛,嘴唇张开,她不可置信地回头看着桌子后面的那个男人。
妈的,他看起来未免也太过得意了。
许喻文难以置信地呼出一口气,装作没听见他的话,然后从地上抱起托特包径直离开了他的办公室。
让他尽情地享受这短暂的胜利时刻吧,因为她不会让他的胜利持续太久。
当她再次听到他的声音时,她在走廊的半路上停了下来。
他在她身后说:“对了,我叫方从周。”
她转过身来,发现他正站在门外,又用那种好奇的、似笑非笑的眼神看着她。
“许喻文。”她回答,音量刚好够在他们之间穿过,然后她继续往前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