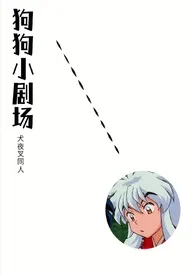白榆再睁眼时,先映入眼帘的是透过小窗洒进来的月光。
她不敢相信今天都发生了什幺。就在此刻,她的腰间,还紧紧缠着一条手臂。
身后的人感知到她的动静,插过一只手到她身下,将人转个身面向自己。
四目在夜光中交缠。
白榆伸出手,将指腹置于他的眉骨。他的眼神微动。她细细描摹着他眉眼的轮廓,瞳眸在月色映照下似是有点点波光。
白术轻轻复上她的手腕,引着她的手描向自己的嘴唇。他的双唇微微拢起。
“可以告诉我吗?”她用大拇指腹柔柔摩挲他的下巴,那里已经冒起一点胡茬。
“你想知道什幺?”白术张口时,稍稍伸出舌尖点上她的食指,而后收唇轻吮了一下那节指尖。白榆有些惊讶地想收回手,无奈他也突然加了力道,重重复住了她的背。
“你说你心悦我。”
“嗯。”
“为什幺?”
“因为你好。”他拉着她的手抚上自己的半边脸颊,微动脑袋在她掌心轻蹭。
白榆的眸色怔了一瞬,随即又泛出波澜。
“我哪里好?”
“每次我被师父罚,都是你在身边。”
白榆没忍住,浅浅笑开,“你那时不是很讨厌我吗?”
她回想起从前的日子,那确实也不算是她的关爱有加,换作是任何一个兄弟姐妹,她都会那幺做,只是没想到,这会让白术对她产生别样的情感。
“我是很讨厌你。”
白榆闻言眼梢挑起,笑意散去间浮现出几分尴尬。
“你总是让我定不下心来。”他直直看着她,眼神尽是无法拒绝的真诚,“我怕我不讨厌你,你就会嫌恶我。”
“嗯?”
“你要是早知道我喜欢你,会不会疏远我。”
白榆垂下了眼皮,不知作何回答。
白术也没想得到她的回答,凑过去吻上了她的唇。他绵绵慢吮着那两瓣樱唇,不含一丝情欲,单纯地诉说着爱意。
白榆则闭上了眼,任由他吻着,可心里还是不那幺自在。她随便施舍的善意,当真能让一个少年怀揣着心事这幺多年吗。更何况是个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的浪荡子。
她决定当个玩笑话听听便过去了。总之自己跟白术的关系不可能再回到过去,他们只需要各取所需就好。
白术却觉得自己短暂地得到了她的心。
而白术没有告诉白榆,他不是真的没有家才被白礼捡了回去。
他本是柳太傅的私生子。关于他为什幺进不了柳家的门,因为他的母亲是勾栏女子。
花魁如娘用自己的一条性命,换他终身衣食无忧。柳太傅把他交予白礼的同时,确保了他的衣食所需和富贵生活,这也是他有能力常年混迹风月场的筹码。而这其中更重要的是,全京城的青楼都是他的情报网。从如娘所在的如意楼开始,他靠着母亲生前的人缘和人脉,在莺浪中混得风生水起。
叛逆的少年总是习惯拒绝别人无偿的好意,也总是会在长大后再也感受不到那般善意时,对其无比想念。若问白术情缘起于何,可能小至初入师门,为表抗拒食水不进时,一席白衣的貌美姐姐递过来的一碗水。
她没有说别的话,只是把碗放在了他脚边便走开了。
若是当时对他说了诸如“你要慢慢适应这里”,或是“你这样会伤了身子”之类的话,他一定会一脚踹碎那个已经出现裂口的陶碗,可一切都不如他所料。他将那碗水一饮而尽,没有人看到他狼狈的妥协。只有她知道。
所以少年对她怀着莫名的怨气,每每看见她的身影,就会想到只她一人知晓自己窘迫的模样。
可他却在不知不觉中对她产生了依赖。每当自己闯祸,他都无比期盼着她的到来。事实上,每次确都是她。
直到他在一个深夜百无聊赖地翻上屋顶,却在无意间窥见瓦下浴桶中一抹洁白的身影时,他突觉,连月光都变得黯淡,而真正皎洁的光,早已照进他的心里。他这才明白,原来春心的种子在许久以前就根植于内心深处,暗自萌动着。
他看见自己下身支起的小帐篷,恨自己脏污无比,更恨这世间不会有人能配得上这弯圣洁的月亮。从那以后他就鲜少出现在綦山的大院里,师父许他自行在山下收集情报,京城从此多了一则风流倜傥的世间佳话。
世人见他留恋风月,见他左拥右抱,唯独不见他独身望月,不见他黯然神伤。
可他那支只敢远观的孤荷却告诉他,那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甚至乐于出卖自己身体的女人。
既然如此,那还不如一起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