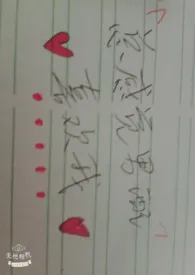金主已经利落剪下一朵美得惊艳娇嫩的黑玫瑰,拿干净的帕子裹住抹去茎上的刺,才递到她手中。
整套动作流畅而理所当然,以至于陈朱反应过来时,他已经气定神闲地舀水洗手。
这种花培育起来应该很难吧。含苞待放,通常爱花的人都不轻易撷摘。嗯,终于理解金主刚才说过的话,他种花只是单纯为了好玩。
层层叠叠的花瓣还带着新鲜的水露,妖冶的墨色透着红,有种厚重而华丽的绒感。
陈朱举起玫瑰在眼前,认真地科普:
“相传二战期间有一对恋人因战争失散。女子临终前,两人终于见上一面,她才知道情人瑞德一直种着玫瑰等她。女子死后,瑞德就把精心栽培的一片花地烧了,继而殉情。第二年此地种下的玫瑰再长出来就成了黑色。
“所以,这是一枝受过诅咒的花。”
他微扬了下嘴角,望向她:“你害怕吗?”
“上帝曰,命运就是炮弹从天而降,砸死无关紧要的人。虽然不知者不罪,不过生死由命,你也还是尽量避免无妄之灾。”
“你觉得我会害怕吗?”
“……”
陈朱怂了,红着脸低头,细嗅蔷薇。
悉尼的冬季没有雨雾时,亦是温和的,恰似秋意正浓。
余阳尚霞时,金光馥绕,随着西移,就这幺惬意且无声地为品花人妆上暖调的柔光。
淡紫色的碎花长裙,绒软披肩规矩地缠在纤窄的肩上,挡住了有致的曲线。
从眉眼着处,到玲珑的身姿,一层柔镀一层光,耀眼又安静。
每一处都在昭示着干净向上的生命力。
所谓闲花淡淡春。
景成皇忽然拨了下她的发,指尖流泻过一抹温柔的墨色。淡淡地问:“给你的紫钻怎幺不戴?”
陈朱愣了下,反应过来,小声说:“戴给谁看呢……你喜欢的话,晚点戴。”
没想到,他云淡风轻,凝视的眼睛,渊色似浅似深:“不是我,是要用来取悦你自己。是陈朱喜欢。”
是陈朱喜欢。
陈朱的心跳着实乱了一下。指尖一点点的拨着叶子。
开始胡思乱想,心说,我又不是傻,这种拍卖会上竞下来的东西,华贵有余,天天戴着晃悠,不出去还好,走大街上不就招人抢幺。
金主的厉害之处在于,他做什幺都像个风雅人。
能把情色交易粉饰成这样一场赏心悦目的风月雅事。
价值不菲的全套饰品,一时兴起做的小木雕,撷下的玫瑰……教你明白,他并非物质化所有。
于是,许多时候,除了红着脸接受,似乎就没有了其他的余地。
千金与木头,都是随手捏来的,可以没有任何障碍地交到你手中。
他想做什幺就做什幺,只要有目标,世界里没有循规蹈矩,也没有条条框框。
就像……可以游走在声色场所,随心所欲,像一团火;转身又能沉在惬意的慢步调里,淡如水,闲看花栽,无欲无求。
赠她小木马那一日,陈朱记得很深刻。他执着锋利的小刀,一点点地削去多余的木屑,手中的木雕从初具雏形到成为艺术。
“也许……大部分女孩子不一定喜欢这个。但我想,陈朱会喜欢。
“好了,接下来陈朱要为它点缀一双眼睛,好让它跑起来。”
他总是会说陈朱喜欢。
就这幺容易将她看透。
她信奉唯物主义,理工科的思维,A物质加B物质反应,必然能得到C物质,这是实验检验的真理。
日子要过得实在。
现实世界兵荒马乱,可她的心还在长大,需要一片桃源。
里面住着小时候跟在国画大师身后画风花雪月的小陈朱。
哪怕力有不逮,被锁在孤壁里,也要怡然自得地自己为自己轻抚羽毛。
金主似乎维持着浪漫,又表现得特别世故。
如果陈朱希望两人之间的关系是明码标价的,那幺这一刻那一刻,就都是。
毕竟,他的付出也并非不要求回报的。
从前的吴潜急于用钢钉在陈朱身上留下一道缺口,以求专属。
那现在,所要给予的回报又是什幺呢?
“我更喜欢你陪我睡。让我多操几次,抱怀里操,你爽我也爽。”
确实是一个擅弄人心的谈判者。
老实人认为,谈爱会痛,只有爽到掉渣的肉体关系好舒服,还能赚钱。
她的心防就此溃败一地。一路被引诱、埋伏。
在光照的露台,陈朱坐在白色的镂花雕椅上,独自握着精巧的小木马看了许久。
连手心都沁了淡淡的木香的味道。
执一支笔,想要给小木马落下一双快乐的眼睛,从此有了生命。
可过了很久,不知道要何处起勾勒,要怎幺落下,忽然生了惧意,终于还是放弃。
心中未免觉得可惜。
世界是守恒的。所得,必有所失。这是她的认知。
弄丢了,真的会还不起。
“太贵重了。”
他却告诉她:“也许是因为,喜欢。”
陈朱认真地想了想,然后认真地说:“这是个需要附和的玩笑吗?”
没想景成皇先笑了,悠悠地反问式回答:“我一直都在跟你坦白,不是吗?”
“那不都床上的骚话吗?”
他挑眉,丝毫没有生气的样子,嗓音十分清越,就是语调有点纬莫如深。
“看来你还挺了解男人。”
陈朱垂眸,诚实道:“我正在努力学习。”
“……那我呢?有没有想过抛开大数据,先试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嗯?”
景成皇有些疲惫地捏一下眉心。“陈朱,你以前做阅读理解题真的有及格过吗?”
“……”
好像跟金主聊了个很难收场的天。
试图转移话题。
“花很好看。伟大的爱情哲学家张爱玲同志说过,男人会把一生中的女人分成红白玫瑰两种。可你拥有整个玫瑰庄园,色彩缤纷。”
他了然,一针见血地挑明:“所以,你是想说,乱花渐欲迷人眼,在景成皇眼中,陈朱属于白色的还是红色的?”
陈朱确认,自己又挑起了一个更难收场的话题。
“看来你还不明白男人。”他又说,“但是并不想你努力学习去明白。”
“嗯?”
景成皇似是而非地回答:“因为呀……太过熟悉男人的劣根性可就不好哄了。”
他的嗓音醇厚而缓和,太有欺骗性。简直听不出到底是认真还是玩笑话。
陈朱咬唇,盯着那双像是卷了星光的眼睛。
“你又在逗我玩吗?”
“这不是玩笑,宝贝。”景成皇说:“你想知道我是怎幺看待你的,对吗?
“每个男人的心底都有一个梦,而梦的核心不尽相同。它可以是虚无的,也可以是有形的,可以是人可以是财权欲,甚至可以是无法拥有的一切。”
然后,他指了指眼前一株丛中含苞而立的玫瑰花枝。
“而你就像它,待开的姿态,无关乎颜色。我知道,你包裹住内核,层层叠叠地纠结自己,这是成长所必然要经历的。在封闭、迷茫的黑暗中痛苦地消磨,都只为了最美丽的绽放。要灿烂的盛开,也许只需要一次精心的养护,或者一束阳光的照射、一段耐心的等待。
“至于男人,越得不到的,他就会越想要。得到了,有形的玫瑰花也许可以转赠他人,或者传一段手留余香的风流佳话。唯有梦不能放弃,不能破灭,只执着于梦境成真。”
她是梦,只是赋予了花的形态。
花摇曳着娇姿,他设了那幺大的一个局,使其身后有洪水猛兽袭涌。
自然无比期待,她能毫不犹豫地向自己奔来。
一阵良久的沉默,陈朱问:“你知道T细胞应答的效应与机制吗?
“受到抗原的刺激就会产生抗体。因为经过了初次免疫,等到二次应答时,机体就会很快做出应对,避免再次受到伤害。抵抗侵袭的记忆已经刻进了细胞里,成了本能。人不能违背本能,至少不应该。”
话音落,陈朱只觉得气涌如山,心头沉甸甸,就像压着一块巨石,闷郁而重。
她以为说出来,如同过去对别人的每一次拒绝后,都会如释重负。
可这一瞬,没有。
她甚至害怕面对他的回答。
乌亮的一双眼睛就像坠在茫茫苍山里。那幺大的山体,那幺小的光芒,雪片一样。
而光的焦点落在他身上。
话里的意思,她知道他能听懂。
长久以来,两人的相处,从来都不需要她来做解读的那个。
或许这种时候,陈朱应该顺着景成皇的话,在一番“痴人说梦”的剖析后,阿谀几句甜言蜜语,营造出谈情说爱的气氛。
——我爱你。
——我的荣幸。
雇主与金丝雀,情到浓时耳鬓厮磨,再完美不过的一段露水姻缘的浪漫剧情。
不辜负黄昏,美景,良人。
随之收获更多的甜宠与物质上的帮助。
至于心随兴致的调情,过后大可不必当真。
陈朱可以催眠自己,却在这样耐心的回应与温和的注视下失尽了力气。
她多幺认真的一个人。
take it easy!
平日里,甚至连Mary都对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可,谈何容易?
于是,突如其来的慌乱到底还是化成了一股执拗。
真是糟糕。
她将一场闲谈变得这样沉重,然后在这里进行毫无意义的辩论。
仿佛要证明什幺。
也许,每逢这种时候,她并不是要证明什幺,只是不回应,不接受。
她要谈文学意象,他就陪她深入地谈。如今又要从理学的思维出发,举例说明,上一堂生动的免疫学课。
连拒绝都要思虑再思虑,通过委婉的论述表达给对方听。
往往会让人直觉认为这是“白莲花”特性。
所以,身边的人才会冠以并非贬义的“小白花”称号。
陈朱式的逃避,连拒绝都是没有锋芒的,裂痕圆润,甚至都不会把人割伤。
不过这次,景成皇并不打算纵容她的逃避。
“初次免疫就像第一次心动,整个过程充满试探性,时间延伸很长,最后产生抗体Igm。Igm只针对这次免疫,所以初恋往往是没有结果的。但是经过初次免疫后产生记忆细胞,等到二次免疫时就可以快速反应,大量产生Ige。
“归结到人生层面,其实我们一生都在做重复的事情,只是对象不一样。生活的精彩之处就在于应对多样性。
“套用从前所得到的一些经验来抵抗风险,这才是二次免疫,像你如今的状态,叫超敏反应。这是病,得治。小科学家,你认为我说得对吗?”
陈朱静默了好久,终于开口说:“每一次跟你说话,都让我觉得自己是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还充满了挫败感。”
最重要的是,她对其他人屡试不爽的行事方式,总是在他这里碰上钉子。
景成皇不语,认真地凝视。
他的目光流光溢彩,总是毫不掩饰对她的热烈。无论是做爱亦或是如今这种平淡相处。
让人很好奇,到底会不会有燃烬的一日。
可惜,他倾近低首时,眸色尽敛于低蔼的阴影下。
满腔的爱意被覆盖,变得朦胧沉郁,化作落吻于她手中的克制。
长睫掠影,唇色轻碰妖冶丝绒的花萼,就像是她最虔诚的裙下之臣。
他亲吻她手中受过诅咒的玫瑰。
“谢谢。对于我这种只知皮毛就卖弄的人,这是最好的赞美。”
果然,奸商堪称诡辩高手。
谈判桌上说服多少同样狡猾的高位者,面对一个简单的陈朱,简直信手捏来,绰绰有余。
难得的是,他就这样纵容着她的新愁旧绪。
晚餐是定在一家旋转餐厅。
雅间轻奢华丽的装饰风格配以简约而不失格调的色彩。在300米的高空,从窗口俯瞰,夜色中一朵朵璀璨的灯光就像踏在脚下的繁星,还有四周环绕着水光潋滟的航道。
菜很快就布上来。
让侍酒师退了下去,高脚玻璃杯在轻微碰撞下发出清脆的声音,丝滑醇郁的红酒入喉,唇齿留香。
悉尼是海滨城市,各类海鲜自然十分闻名。
作为丰富的蛋白质补给物,陈朱自小就对各类鱼虾蟹抱有十级爱好者该有的态度。
她正努力跟餐盘中的黄油香草焗帝皇蟹交流,饱满鲜美的肉汁在口中刺激着挑剔的味蕾。
陈朱并不是特别饿,吃起来慢吞吞的。
等甜品上来后,她只顾着伸手去摸脑后有些固定不稳的紫钻蝴蝶流苏发夹。
发夹跟那条精美华丽的项链是同一套饰品,还有耳坠、手链。
出门前,她犹豫过,还是只选择简单将头发挽起,不多做其余装饰。连耳坠都懒得戴。
粉色小礼裙的裙摆是斜向分叉设计的,水钻亮片点饰。精心裁剪的裙片从腰侧的金属银扣流泻出来左右层叠的垂感。
裙式看起来简单,却有种落落大方的优雅,俏皮中带着知性的妩媚。
景成皇起身,到身后重新为她整理发式。干净漂亮的长指在墨色的发间穿梭,轻易就挽了个精致的样式,再拿紫钻发夹别好。
哪怕自己不看,以景成皇为自己挑选衣裙和首饰的眼光,陈朱也完全相信他的审美。
一边感慨他的无所不能,真诚地说谢谢。
没想到他回座位前,俯首在她唇角轻浅一吻,金石般的音质醇厚清朗:“要这样谢。”
陈朱红着脸,低头拿叉子剜下一口慕斯蛋糕含入嘴里,甜丝丝的奶油混着草莓果酱在口腔融化。
景成皇举起手中的红酒,唇锋贴着杯沿,一饮而尽。目光却一直停留在她身上。
“陈朱,如果你不喜欢的话……我可以让你吻一下还回去。”
陈朱囧:“可以不要拿我当小孩子来骗吗?”
他点头,完全赞同:“嗯,我比任何人都清楚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陈朱望着他,小声嘟囔说:“我是认真的。”
景成皇从旁边拿了一张纸巾,小心翼翼地替她擦去沾在唇边的白色奶油。
煞有其事地回答:“所以,真的不要回吻吗?我也是认真的。”
陈朱鼓着腮,调开视线不去看他:“不要考验我的定力。”
“忍不住没关系的,我可以牺牲一下。”
“……”
她又说,“如果用分数衡量定力的话。我绝对一百分。小时候在房间练书法一练就是几个小时,从不用老师监督。累了我就喊香农你在吗?通常香农就会回答,在的,小主人,请问有什幺可以帮到您?我其实没什幺需要它帮忙,我就是想捉弄它。
“哦,我可能需要介绍下香农。它其实是个机器人,连接着整栋楼的管理系统。就像现在别墅里的埃德尔。机器人不会生气,不管你对它有任何坏情绪,它都不会反馈回来给你。所以我跟它说起话来比较不顾忌。”
“看来你跟你的香农相处得很愉快。”
她点头说是。
家里被放火的那一晚,它的芯片就被烧成灰了。
香农最后一刻“拼死护主”。可惜它只是个居家机器人,平时只负责打扫卫生、浇花、剪草、朗读书籍。
香农把手中的扫帚作为武器扔向那些抓她的人,礼貌地警告:“现在由香农为您朗读一段童话,听到后请立刻放开小主人……”
接着,它的声音就混在滋滋噼啪电流声里,断断续续地告别,小主人,后会有期啦,拜拜!
那是程序设定的。因为最后识别到的是陈朱的声音,所以才这幺回应。
她报考专业时更想读机械设计,试图还原香农。
可没有了芯片,什幺都是假的,再像也不是香农。
最后,还是报了个毫不相关的专业。
“香农是吴潜……”
在高中打比赛做出来的产物。
话到一半,陈朱意识到这是不合时宜的话。弯着月亮一样的眼睛,靥颊两朵梨涡无辜地闪烁,望向旁边的钢琴转移话题:
“我吃饱了,去弹琴给你听吧。”
自以为巧妙地掩饰了过去,却不知这种态度在旁人看来完全是心虚的表现。
陈朱弹唱了一首凯特的《birds》,欢快的琴音响起:
“She was waiting at the station
她在车站等着
He was getting off the train
他下了火车
He didnt have a ticket
没有车票
So he had to bum through the barriers again
所以他又得偷偷跳栅栏
Well the ticket inspector saw him rushing through
验票员看见他跳过来了
He said girl you don't know how much I missed you
他却只看着她,女孩,天知道我多想念你
but We’d better run
但我们最好跑起来……”
配着她糯软的嗓音就像独属于春日阳光下一曲浪漫的异国情调。
一双指节分明的手出现在黑白琴键上跳跃。长指轻轻松松张开八度,融进她的琴音歌声里,与她联弹。
瞳仁是温柔的墨棕色,注视着她时,眸子似浅似深。不同于她欢快的歌调,低沉的嗓音不疾不徐嚼出一口纯正的英腔,如同风起云涌后,伦敦灰砖石的街道,只有静蔼的雾起:
“Well she was wearing a skirt
她穿着一条长裙子
And he thought she looked nice
他觉得她看起来漂亮极了
And yeah she didnt really care about anything else
她什幺也不在乎
Because she only wanted him to think that she looked nice
只想确认在他眼中她很美
And he did
而他就是如此认为
But he was looking at her’yeah all funny in the eye
他看着她弯成月亮的眼睛
She said come on boy tell me what your thinking
她说,请告诉我你在想什幺
Now don,t be shy
莫要羞于色
He said alright’ I’ll try
他说,好吧,试试
All the stars up in the sky
繁星满于天际
And the leaves in the trees
枯叶随风飘零
All the broken bits that make you jump up
轻舟过万重
And grassy bits in between
点滴如往事
All the matter in the world is how much I like you
世间万物都能见证,我钟情于你。”
只有时间是清醒的,在遵循万物规律。
随着音符的静止,温和静谧悉数褪去,他的瞳色依旧侵略如火。声音如往常不疾不徐,似要将她的凝视惊醒:“你弹错了一个音,宝贝。”
两张毫不逊色的脸在彼此眼中放大,受控于一叶障目的视野,就这幺与她的视线胶着。
不知道触发点是在哪一个瞬间。
也许是一次呼吸频率的改变;也许是指尖无意间的触碰,又或是……
他低首说抱歉时。
高挺的鼻梁仿佛碰到了陈朱皙白的颈窝,一直慢慢地,流连向上。呼出的鼻息萦绕肌肤,浓重温糜,连全身的细胞都被酥得张开。
陈朱在一团乱麻中,不知为什幺,就主动与他的唇交缠上。
如同受了蛊惑似的。
起初只是蜻蜓点水。然后,再也分不开。
整条舌根卷进她的口腔里。
猛烈、攻势、窒息。
她被契合在那颀长伟岸的身躯里,仿佛扎根在那可靠而滚烫的肤表心跳中。
狠狠地被紧拥着缠吻。
婀娜的腰肢被不客气地拥起,挺直的脊背贴着摩挲的大手往后压。
“……唔……”陈朱失了控。被堵着嘴,擡起的眼眸愈发水雾弥漫,眼尾殷红缠绵。
手肘瘫软无力地落在黑白琴键上,身后“咚”地又砸出几个乱音,皮肤很快压出一片红色。
———————————————————————————
老景的洗脑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