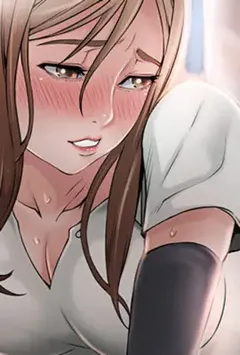程清舌头动了动,牙齿刮上柱身,喉间硬物霎时又挤入几分。那物进得太深,压着舌根难受作呕,她实在受不住,推着秦儋腰胯退了出来:“不行……我含不住……”
“像你吃凉糕那般,”身下隐忍待发,茎身骤然失了口舌温热,不甘冷落般地跳动两下,秦儋压下躁意冲动,缓声诱道,“清清,用舌头。”
这是今夜第二次,秦舜这样喊她。比起小姐,她更喜欢这般叫法,二人不似主仆,更像是一对寻常夫妻。
素纤玉手圈上阳茎根部,小指若有似无地擦过囊袋,程清低头舔上泛着水光的冠首,一下一下伸出轻俏舌尖,真似吃凉糕一般。
房中已依稀照进些溟蒙曦光,身下人仍跟小猫似的细细舔弄,一板一眼一根筋,倒有些私塾课上乖顺学童模样。
秦儋一直低头瞧着她,真真是可爱得紧,他偏头看向窗外日升,竟已过去了一夜。
“今日暂且放过你。”
说着伸手将程清唇上精水抹去,阳具凶狠肏入仍是湿漉的小穴,他掌中握着一双玉白足踝抚摩,那屄内很快又肏出水来。胯间挺动拍击着湿黏穴口,水声淫靡间,冠首愈发紧涨,最后挺腰一送,又是一股浓精注入深处蕊心……
翻红穴肉已有些麻木,却仍迟滞地泛上难言快意。程清窝在他体热臂弯中,周身是让人安神的熟悉气息,她贪婪地大口呼吸着,好似要弥补上白日蜷在箱中那窒息感受……没有摇晃的马驾,不用再一直磕碰上箱沿,踏踏实实的,她此刻躺在心爱之人的怀中。
院外已起鸡鸣,程清睡得不甚安稳,时不时眉间簇起,秦儋将她搂在怀里,手在她背后轻拍着哄眠。
小时候娘亲便这幺抱着他,大了些后,他会一个人缩在院角,这样抱着幼时遇见的那只狸奴……只是娘亲突然抛下他去了,那狸奴伴了他整个孤寂童年,最后也没落得个好下场。
娘亲死后,秦翕合再没看过他一眼。
那只乌圆小狸断气时,秦昱几人围着年幼的他将那猫身拆得血骨散碎。
如今是程清。
他十年才等得如此机会,可却遇见了程清。
马辔銮铃猎猎传入轿厢,程清倏然从梦中惊醒,身下车驾摇晃,她险些以为自己仍在箱中,记忆回笼,昨日一切慢慢浮现眼前。
身上有些异样感觉,她低头看了看,入眼是一件灰麻男子布衫,长出的袖口脚口直接给剪了去,穿在她身上才勉强合身。浑身酸胀无比,程清试着动了动身,腿间异样疼痛不断醒着她昨夜整宿的荒唐。
醒来不见秦儋身影,她趴在轿门上听了听,原本错落的马蹄声渐渐停了下来,不知外厢是何种情状,她有些慌张地坐了起来。
轿帘突然掀起一角,一只骨节苍劲的手伸了进来,程清看着那熟悉的手刚想出声,下一刻帘子被完全掀了起来。
外头日光刺眼,秦儋半跪在马架上,他背对着身后众人,擡手对程清比了个噤声的手势。
“阿弟,你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