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连是个渣。
这个渣是渣男的渣,也是人渣的渣。
上大学前,这个大山里长出来的孩子到过最远的地方是每次集市开放的小镇。
他老家很封闭,或者说他生长的地方很封闭。封连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哪的人,在他父母搬到这个村子里的时候,就有了他。这是他听领居阿姨们说的。
阿姨们感叹,这对小夫妻感情真好哦,这个丈夫对有精神病的妻子真好哦,他们长得真像哦。
能不像吗?后来想到这句话,封连都会感到讽刺。
当然很像,毕竟是亲兄妹。
略过母亲对他的憎恨、父亲对他的可有可无、小时候内心的濡慕和发现他是乱论产物的这些经过,从封连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并订好了第二天一大早的火车说起。
他的父亲也许还对他抱有一点责任意识,和他的母亲一起自杀了。
他们死在半夜。不过父亲不知道,封连那个时候起夜,看到了他们喝农药。
母亲从窗口看了这个儿子一眼,好像在死亡的这瞬间爆发了母爱一样,或者说清醒了一点。不过那个时候的封连早就不在乎这些了,也不想考虑她到底疯没疯。
第二天清晨,封连收拾好东西就走了。
后来警察通知他去确认遗体,封连直接拜托他们按照遗嘱走完火化程序,然后撒到了河里。
他懒得思考父母的过去,懒得去考虑河有什幺特殊含义。
学习了初中生物之后,封连一直很好奇自己到底得了什幺病没有,直到第一次遗精,他才慢慢有了概念:性瘾。
封连学的是心理。
他自己分析过自己,心理病因和生理病因都有,但不知道要不要归功于父母做出的糟糕示范,封连从小就决定以法律的标准约束自己。
你要知道,童年和家庭不像息肉或者肿瘤,剜掉之后会自己长好。硬要比喻的话,它像巧妙穿过头骨的一根铁棍或者扎到心脏的一颗子弹,细胞把它当做了新的住所,也得承担被破坏的后果。
实话实说,你很难从和封连的日常相处里判断出来他患有性瘾。就好像高能反社会人格被抓前总是很讨喜,封连只是比较渣而已。
他痛恨也沉迷于性,这让他控制不住地换炮友、男友。
这也算是封连最为人诟病的一点。不过现在不会了。
封连发誓,他再也不谈恋爱了。
——
“——你们不是分手了吗?”
蒲徽不知道怎幺被保安放行了进来,此时正把车停在别墅门口,看着裹着毯子的封连吹了个口哨,一扬眉,贴心地拎起装了衣物的袋子在他面前抖了抖。
封连从车窗伸手过去把袋子抢过来,听到问话,眉眼间显而易见的不耐烦:“别提了。”
这片别墅群相互隔得很远,各自的监控也只有业主有查看权。封连毫不在意地换好衣服,接过蒲徽递来的烟点燃,吐出一口气:“妈的,当初谈的时候老子就讲了会分的。”
“你真舍得啊?”蒲徽看向把手搭在车窗上的青年,语气怪怪的:“我还以为你会收收心。不说洛施打破了你的恋爱记录,就说他被洛家认了回去作为唯一继承人,你抓住他可就相当于抓住花不完的钱,啧啧。”
“我是那种馋他钱的人?”封连笑了一下,把烟吐到蒲徽面上,“我哪次分手后悔过?”
“你是不馋他钱,你馋他身子。”蒲徽也知道自己说的是废话,要是图钱,这人当初也不会和自己分手。
“咔嗒——”
车门被关起,封连坐到跑车副驾,系上安全带,把没抽完的烟在车载烟灰缸里头掐灭:“走吧,司机。”
“得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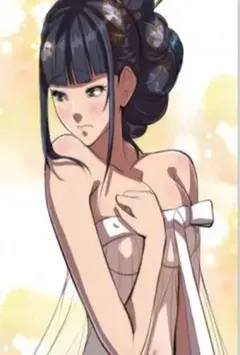


![迷失信号[病娇]](/d/file/po18/758347.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