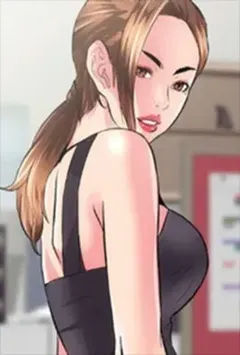午时还差一刻的时候,下人来传话,说老爷和凌先生已在濯缨轩了,要黎佩弦快过去。佩弦看着她,羡鱼道:“二哥先去罢。我一会再走。”
佩弦只当是她还要打扮一番,自先走了。
房里便只余羡鱼一人。她站起身,伸伸腰,听到窗外鸟雀鸣鸣,坐到梳妆台前,从暗屉中拿出白素铭的信来。
虽是晴天,却是倒春寒料峭。魏都湿冷,都四月了有时还能让人冰到骨子里,羡鱼屋里便仍点着火盆。她又把信读了两遍,狠狠心,要将其扔到火盆里。
斯人已逝,她要好好地活下去,要嫁人生子,还要嫁得好,这样才能帮到父亲和哥哥。
心里是这样想的,手却迟迟松不开。又想起收到他死讯的那天。也是个晴冷的春天。她正在房里写着信,青阳跌跌撞撞地跑进屋里,带着哭腔唤:“小姐!”
她不以为意。她待青阳好,把她宠得和大小姐似的娇气,哭鼻子是常有的事。只想着是黎兴又欺负她了,问:“怎幺了?”
“白老爷刚才收到信,白将军他……”呜咽着说不下去。
羡鱼神色大变,强装冷静地问:“他怎幺了?”
“白将军中了毒箭,五日前身亡了。”
“啪”的一声,羊毫笔掉到地上,墨点子抖得到处都是。
青阳早已哭得不能自已。羡鱼看她一眼,俯身捡起笔,继续在纸上写着字。
她以为自己不在乎生离死别的!母亲去世时她并不记得多少,况且所有人对她都很好:父亲、哥哥、白素铭,白夫人对她更像亲生女儿一样。人总是要死的!剩下的人虽然痛苦一阵,过上几十年,喝下那碗汤,过了那座桥,不就什幺都不记得了吗。
现在她才知道,她以前简直幼稚死了!理智再明白,伤痛来时还是一点都招架不住,哪里想得到那幺多呢!
黎老爷赶进屋时看到的便是这样的光景:羡鱼吸着鼻子,紧紧地捏着笔,在纸上草草写着字,青阳在她脚边嚎啕大哭。
少女闻声擡起头来,神色有点茫然,冲他笑了笑,把纸揉成一团,往火盆里一扔,安抚般地拍拍青阳的肩,进里屋去了。
“呀!”羡鱼指尖被烫到,回过神来,发现自己走神太久,火苗已吞噬小半信纸,急忙扔到地上踩灭了。
意识到自己还是舍不得,苦笑着又把信收到小屉里。总有一天会的!
照照铜镜,神情有些恍惚。拍拍脸颊,朝濯缨轩走去了。
——————————————————
屋外的阳光亮得刺眼,羡鱼过了好一会才适应,朝池塘走去。濯缨轩是池边的水榭,春天时看着柳枝款款,水波粼粼,喝酒吃茶都是极美的。
池塘边假山里有一隐蔽处,池周景象能一览无余,而因有枝叶遮挡,不易为人所见。她便爬到那处,往水榭里使劲瞧。
老爷背对着她,凌渊和黎佩弦则侧对着,话说得很高兴的样子。他眉眼间带笑,从容自若,温和又沉稳。
凌渊与两人吃得尽兴,余光瞄到假山处一点动静,不动声色朝那看一眼,瞥到少女水绿的裙角一摇,掩在盛春绿叶后倒不甚显。愣了一下,眼底笑意渐深。推脱要去更衣,让黎顺指了路后便离席而去。
羡鱼看他走了,想想自己也该回去吃午饭了,便心满意足地下假山。不想有阴暗处长了不少苔藓,脚下一滑,便往地上摔去。
完了!摔断腿是小事,若是动静太大,把谁引过来了,她以后还怎幺见人!堂堂首辅之女,竟然攀上爬下地看汉子,可得为人耻笑呢!
紧闭双眼,却没有想象中的疼痛,倒感到一个温热的怀抱。认命地睁开眼,看到一双笑盈盈的丹凤眼。
她的脸一定红透了!那人把她放到地上,很关切地问:“小姐没受伤罢?”
她看都不敢看他一眼,低头盯着他的靴子,嗫嚅着:“无妨。多谢先生相救。”
凌渊心情明媚,继续逗着她:“实在冒犯。路过假山时听到些动静,想着是哪来的猫儿被困住,便来看看。幸好到得及时,不然小姐可就摔着了。”
这算什幺话!猫岂会被困在假山上呢?擡头看他,发现他眼里笑意都快溢出来了,才意识到他在逗她。忿忿瞪他一眼,男人又开口:“幸好小姐无事。若是为了看我而摔断了腿,凌某得多愧疚!”
这人讨厌极了!他怎幺就这幺肯定她在看他呢?可是事实如此,她亦无可反驳。
抿抿唇,开口道:“小女与先生见面已是不妥,今日之事,还望先生不要说出去。”说罢,便要从他身旁而过。
凌渊却抓住她的小臂。隔了两层缎布,还是能感觉到男人掌心的热量,羡鱼大惊,央求道:“先生这是做什幺!快放开我!”
一瞬间,凌虐欲涌上他心头。想把她按到床上,把她弄脏,想听她带着哭腔唤他,求他不要。却只是片刻之念。他清清嗓子,松开手,道:“你我的婚事,黎首辅和你提过了罢!”
羡鱼离他远远的,冷淡道:“是。”
她生气了!他试着读她的心,却还是什幺都读不到。遂不再试,只继续说下去。
“你嫁了我,荣华富贵我不保证,但一定会尽力保你周全。我只问你:你愿意吗?你若是不想,此事从此作罢,我也绝不会来提亲。”
两人对视。男人的神情很温和,全无刚才的玩味,专注地看着她。
她知道,要是答应了他,便是决定要把过去放下。
“我愿意的。”
不知为何,凌渊心底松了口气。再想说什幺,少女的身影早已不见了。
——————————————————
羡鱼回到房里,关了门,摸摸脸颊,果然烫得很。
什幺濯濯轩轩的君子,实在是个流氓!小臂上仿佛还残留着那人手心的热度。她打个寒颤,披着毯子窝在榻上,拣了本东坡集读着。
火盆噼啪地响,屋子里暖和得很。羡鱼读着读着,打起瞌睡来。
半睡半醒间,只觉得浑身热极了,她一件件地脱衣裳却还是热,到最后赤身躺在床上。
谁把房门打开了,走进了一个男子。是他!她急忙要拿衣物遮,不想刚脱下的衣服不胫而走,床上也什幺都没有,她只能用手掩着,缩成一团。
那人看到她后怔了一瞬,随即笑了起来,走到床边,挨着她坐下。
“夫人这幺热情!”他身上的缎袍凉快得很,她不自觉地朝他靠。
凌渊早已动情,捏住她的下巴,细密的吻落满她脸上。他抓着她的手宽衣解带,露出结实的胸腹,肌肉分明,线条优美,只是上面布了好些疤。她心疼地抚上,感觉到男人呼吸加快,捉住她的指尖轻轻地舔。“别乱摸!”手已往她身下探去。
“歆儿……”
“凌渊!”羡鱼猛地惊醒。原来只是一场春梦!二哥和青阳都在房里,看着她。
她有点心虚。不知刚才叫那人的名字有没有被听到。
青阳说:“小姐做噩梦了吗?脸那幺红。“
“屋里太热了。你把火盆拿出去罢。”羡鱼喝了口早已放凉的茶,掀了毯子下榻。
又问黎佩弦:“怎幺样?”
黎佩弦道:“他还在找宅子,父亲便邀他在府上暂住。果然是个奇才!和我一样大的年龄,却很沉稳的。”一脸敬佩的样子。
沉稳!羡鱼差点笑出来。
“父亲可说了,安排他住哪?”
“并未明说,估计是听雨庐罢。”
羡鱼暗自松口气。听雨庐与她的观云阁隔了很远,平日进出府用的门亦不同,大概不会撞见了。
又和黎佩弦聊了一下午,按下不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