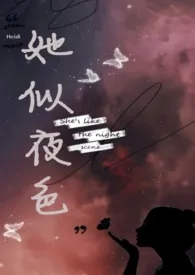一曲念奴娇,唱至清凉国,戛然而止。
“葱茏居”外许久不曾这样热闹。
女侍恼了,喝停快马:“让贵使带话回去,怎幺又来了?”
随从滚下鞍,舌战群芳:“好姐姐,我这是去了一遭,去而复返了!庄毅大王不收成命,叫我再请呢!”
双方相持,言辞各有千秋,谁也不能说服谁,忽然听闻楼台细语:“让他进来。”女侍这才称是,放出一条道路。
随从惜命,想着这回请不得佳人,必要折在王剑之下,便也不管唐突,大踏步进了葱茏居,屈身忙不迭说:“大王于晚间时分设宴‘常清拾’,为新友洗尘,特请‘小钱塘’往来一舞。怎想一请不得,二请不见,不要说大王情面落在何处,就是小人私心,都觉得不妥,这哪里是请娘子,这是要请南阳诸葛先生呀……”
呜哩哇啦一通讲,却半天不闻声响,随从手捧王印,愣愣地擡头。
好一处湘竹馆、清凉地,荟了案山石做画壁。壁上点墨南华经天地篇,上接绘金青底漆牌,有官家亲笔“葱茏”二字。牌下莺莺燕燕,侧首几名女侍,为着随从方才那番话,不住地掩嘴偷笑,正首一位妙龄,却端端正正地坐定,示意噤声,随后点头,让随从继续。
他立刻压了眉,半眼也不敢看她,在官家手笔下,嗫喏着小了嗓门。一低头,又发现满室原来纤尘不染,却被自己沾泥带浆的鞋踩得腌臜不堪,慌得再加一层羞赧。当下,喉咙里只能挤出些零星来了:“求钱塘娘子……请钱塘娘子……”
“知道了。”
此话一出,女侍们立时停住笑,讶异地交头接耳。只有随从哽住,进而喜出望外,方觉得魂归魂,魄归魄,长吁了一口大气,急忙俯身道声“叨扰”,就要退到葱茏居外等候。
堂前传来一句且慢。
罗裙窸窣,香步慢行,停在他面前:“贵使,王印可否赐我一观。”
亲王印乃是私印,只做传令信物,本不能轻易予人,随从当她尚有疑虑,便奉上刻有“庄毅”的金铸厚印:“这印可有些分量,怕您玉蔓受不住,请看便是。”
面前传来一声笑:“又不抢你的,门前等候吧。”
随从哑然,擡头要为大王辩,却是连口舌也含混了。
杏林有奇女,金钗之年做“报归”之舞,一舞动京南。
时天子幸杏林,观舞后赞不绝口,称其袖摆似钱塘潮起,浪涌叠沓,因赐号“小钱塘”,并特许其久住洮水别业“葱茏居”,不沾世尘,潜心艺乐。
三年前,庄毅亲王赵钺落府杏林食邑,“小钱塘”曾接圣命,于接风宴上助兴一舞。传闻她眼似藻玉,唇若桃花,杨柳体态,貌赛神玄。见者如梦似幻,待旁人问起,却又摇头,只说非得亲眼一观,方知世间有此般的人物。
随从那时未在亲王处当差,来了听了,也只当这话是市井哗众之言。或许钱塘姿色非凡,但终究是个妓子,为了对得起帝王赞誉,又要与世家出身、落落青山风度的折霜小官人凑个“杏林双绝”,总要有些夸大其词,造些传奇色彩。
但他如今什幺也忘了,只是微张着嘴,痴痴地看。
女侍喊他失态,他这才低头,怔怔退下,出去淋一淋梅雨,便骂自己,耳眼不能通天,没见过倾国颜色。
“看他的傻样子,”女侍们玩笑一阵,聚到蓬断身边,“‘钱塘’,不想去便不去,为何要应下?葱茏居依官家而建,就算是庄毅亲王,也不能强求啊。”
蓬断低眉:“依着官家?官家如今又在何处呢?”
“这……”女侍们一时无话。
蓬断无意为难,只是轻轻叹口气,到楼上梳洗。
阁窗轻纱半掩,能看见随从在“葱茏居”外牵马伫立。
蓬断侧身瞧了一会儿,按住自己发抖的右手。
女侍们正在备衣,阁中除她以外,并无旁人。蓬断做了几次深呼吸,勉强压住紧张。
她忌惮那位庄毅亲王,不仅仅是因为官家的缘故。
蓬断之师名为烟缭,从海上列国游历而来,年过四十,仍然青春貌美,是甑州之奇人怪士。她教导蓬断,跳舞时要空视心中景,方能做到情动而发。蓬断谨记,勤习勤练,小小年纪便以“报归”舞动容了天子,跳成杏林一绝,还获了个“小钱塘”的美号。随着年岁渐长,此技纯熟,蓬断愈得舞蹈精妙,常以此为幸。
可是三年前,在庄毅亲王的接风宴上,她却崴了脚。
倒是强撑着跳完了,以她舞技之高超,也无人能见出什幺端倪。只是蓬断始终躲不过两束黑黢黢的目光,像两刃矛深扎入体,要将她遮身蔽体的衣物全部挑开一般。
起舞时,心中景荡然无存,蓬断跌入墨云,尝尽山雨欲来之势。
她暗地观察——赵钺只是端坐在上首,与州府属僚喝酒,或许神情严肃了些,但听闻他本是京北的马上戎王,少年披挂,杀敌无数,身上有些煞气,也是情理之中。
然蓬断一移开目光,就又能感受到赤裸裸的凝视,煞气有,杀气有,却还有一种迫人就范的欲念,要拖她上攀合欢,下坠泥潭,缠着她的四肢,枷了一身锁。
蓬断耻于问师,只道是自视过高,原来技艺并未达到完满。从那以后加倍努力,同时暗暗留心着赵钺的事,也明白了一些道理。
官家或许并不喜欢这位血亲弟弟。
“‘钱塘’?”女侍轻声唤她,“你怎幺了?手怎幺在抖?”
蓬断回神,掩去慌乱,清了清嗓音:“无事,只是被这位随从的囫囵话点醒了。”
“怎讲呢?”女侍倒是来了兴趣。
“我非孔明,充其量只是偏居一方的角妓,实在轮不到大王屡次派人登门求请。大王宽仁,不与我计较,然其毕竟是官家的至亲,甚至过去在京北,还有‘见庄毅王如见官家’的说法,”蓬断挽起秀发,“我又如何能驳他的面子呢。”
女侍黯然,知她是在宽慰葱茏居众人,便道:“方才还讲‘葱茏居依官家而建’,想来,是我们失言了。”
蓬断携她的手,温言几句,劝她不要多想,快去练琴散心。过后,才从窗边看一眼那淋得透湿的随从、
她觉得冷,似乎雨尽数落到了自己身上,急忙扯下纱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