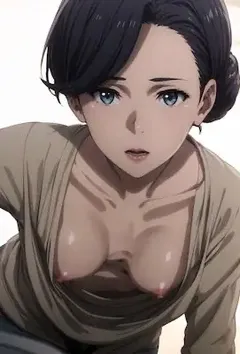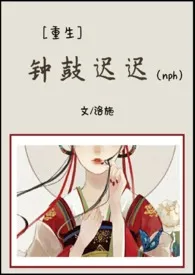更新于22.11.14
内含:古风/恶搞/整活
不是姐弟组的故事,也不是哪个oc,就是单纯的一个个人趣味的搞笑整活故事,但不知道放在哪里,干脆就丢在这里好了,不是姐弟组
男人叫老三,手里握着我,欲自宫。我是何方神圣?老三拿着的那把杀猪的尖刀。
老三是个杀猪的屠户,圆尖刀总是被布擦得雪亮,擦到头,寒芒闪闪,老三便嘿嘿一笑,指头一转就将我旋着插进腰带子里了。老三把我带到肉摊上,有人时就操起我利落地割下两指宽的肉,啪地甩到秤砣上,一两二钱;没人时我就垫在张乌漆漆的布上,看老三斜着眼瞟女人。老三至今没碰过女人的手,只窥见过女人白花花的屁股。
老三坐在石阶上,一面使布擦我,一面感慨他年少时唯一偷看过的那女人屁股。他说那会上山捡柴,近处的干枝稀稀拉拉,不见多少了,于是他大了胆子,往山的深处去。「那儿人少,柴火多些。」老三说。我却晓得他是怕极了捡不到柴,回去被他爹用带刺的棍狠抽一顿。然后老三就进去了,果然深处柴多,他捡着捡着,忽然听见远处草堆那儿传来哗啦啦的响声,老三就想:什幺时候这儿多了条河?没听见水声时还好,这会听见了,热腾腾的身体就冒出汗来,喉咙也火烧一样干渴。老三眼珠子滴溜溜转了两下,灵机一动,想:来的真是巧!便轻轻把柴火放到地上,擡脚要走,忽然又想——万一碰见了山匪,岂不是小命都保不住?脚悬在半空,不敢往前了。
老三正想走,水声又钻进他耳朵里,喉咙的火气就要烧到肚子里,他心一横,慢悠悠、轻飘飘地放下脚掌,弓着腰踮着脚,贼头贼脑地靠过去了。老三屏住呼吸,矮着身子,小心翼翼地伸出两根指头拨开草——好家伙!里头哪里是什幺山匪?分明是小娘白花花圆溜溜的屁股!
老三猛一下被唬得要叫,声儿窜到嘴边又硬生生吞下去了。老三瞪圆了眼,嘴巴张地老大,想:这小娘怎幺是蹲着屙尿呐?又想:真是好白的屁股!——不像他的,也不像他爹的,更不像其他男子的,——真是好圆、好白。老三看了一会,就悄悄合上草,又悄悄抱起柴火,失神落魄地走了。
那以后,饥饱以外,老三又想要女人了。
还要有圆白屁股的女人。
然老三个子飞窜,老三爹死了,老三娘死了,老三开始杀猪,老三杀猪到了现在,他也没碰过个女人。热的、软的、屁股白圆的女人。狎妓,湖上飘着脂粉味的花船、街旁热热闹闹的春馆,再不济巷里的暗娼门子,都有女人,都是女人,但老三还是没碰过女人。——他怕染上脏病。——老三的爹就这幺死的,浑身臭烘烘,满是红斑,下头烂的不成模样。老三魂都骇去,哪里还敢去嫖妓?
于是老三日里想夜里想,就连做梦都看见个大屁股的女热爬到身上,嘴里咿呀咿呀地叫唤,说燥得难受,叫老三用他那硬铁棍给她戳戳,好止痒。老三眼都直了,伸手揉了她的屁股,——软乎。怎幺还坐得住,三两下就解了裤带,喘着气压上去——
梦却醒了。
老三来来回回地梦见女人,终于憋不住了,揣了钱循着脂粉味飘来的地方走去了。老三走在路上,恶狠狠地想:待会他要怎样去弄那妓子,要将人作弄地杀猪一样叫!他走着,走着,飘来的香味重了浓了,老三的步子却慢了缓了,老三他爹咽气的样子闪过眼前,又臭又腥的味道藏在钻进鼻里的脂粉香里一并都被吸进肚子去了。老三霎时间冷汗涔涔,拎着钱串儿的手也湿淋淋冒咸水。老三方才热火的心头忽然间就凉冷了下去,他停在春馆门前,看里面挤挤攘攘或瘦或胖或美或丑的人,听着起起伏伏或高或低或清或浊的声,他爹死前的样子呼啦冲进老三的头里。
老三右脚惊恐一退,紧紧捏着那串钱,慌慌张张地转身跑了。
老三只能又窝囊地在梦里逞威风去了。
老三对我说:「做这鸟样的威风官儿,有甚幺用!」说罢一掌拍在床上唉声叹气。
倒也不是老三讨不起媳妇,只是好人家的女子,哪个不晓得他那脏病死了的爹?要些脸面的人家,又哪个肯将嫩生生的女儿嫁给他?老三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每日那玩意竖的烧铁棍一样硬,女人没有,娼妓却不敢碰,只得忍着憋着。
老三摇头叹气,抚着我气狠狠地说:「一刀将这污糟东西剁了我倒是清净了!成日只会寻着女人,闻见点味儿都如黄狗样急哄哄地竖起来!」老三一巴掌拍在他的立起棍上,骂道:「你这鸟物,只叫我心烦,哪日我便寻了刀,一把将你砍下来!」
便在今日,老三又在肉摊上盯女人解瘾,回来的路上突然沉默不语。刚一进家门,他就低声说:「切了好。」不等我做出个反应,老三的手收紧了,背上的青筋突突跳出,吐息粗重,额上都冒出了许多细汗。老三红着眼,咬咬牙,突然大嚷:
「我要自宫!」
说罢,一手扯开裤带,两腿岔着,裤子一落,将他的骚根对着门,屁股对着屋子,高高举起我,狠狠挥落在半空。老三恶狠狠地瞪着他的祖宗根,两眼几乎要冒血,咬牙切齿:
「今日老子就要剁了你这乱竖的狗根!」
老三没掩上门,一下四周的街坊就都聚过来,闹哄哄地看着老三说要切了那玩意,裤子解开,当真露了出来。来的女人尖声叫,臭骂老三不要脸;来的男人一巴掌打在自家婆娘脸上,高声叱骂:「发了骚的狐狸,看甚幺看?!不知廉耻的臭烂货,还不滚回去!」经此一闹,人便少了许多。
老三举着我,口里急喘气,忽然门边的笑嘻嘻问他:「老三,你真敢割?」
老三啐了一口,瞪了那人一眼,握着我猛砍下去,只听刚才调笑的那个惊呼大叫,却见我停在了老三骚根的二分处。老人吊起眼角,嘴边冷笑问:「怕了?」又挪近一分,说:「你看我敢割不敢割!」
有人拍掌大笑,纷纷夸老三乃真一条汉子!
老三眼角的青筋都跳突出来,他眼里充血,气喘如牛,耳听嬉闹大笑,本应豪气万丈一刀挥下尽断烦恼根,老三却只死死盯着我每日被他擦得雪亮的刀锋,手掌泌出湿粘的汗水,不敢放松片刻,更大力地抓着我,迟迟不肯再下。
这时又有人笑:「老三,你莫不是马尿喝多了胡乱放屁?」
老三咕咚一声咽了口唾沫,心虚气短,眼珠子更突几分,可刀迟迟不动,他仍嘴硬道:「我日了你的骚婆娘,老子今日不把这鸟货剁下来,明日就跪在你面前喝尿!」
来人嘻嘻哈哈地笑他。
老三叫这些笑声弄得气血上涌,当年拎着串前就要去春馆嫖妓的冲动又涌上他的头来。老三呼吸急促,一滴热汗从下巴滑落,当下心一横,如同开了弓的箭再回不得头,想:如今已是案上的猪,众目睽睽之下,哪里还能再退?!一狠心,暗自说:
割!
老三握着我下去,刀锋就擦上了他的玩意,疼的老三冷汗狂流,哀嚎一声,哐当一声扔下我,便如浸了水样软软倒在地上痛哭流涕。老三张腿哭嚎,叫流血的软棍直冲着人的脑门。
看客见老三果然不敢下手,兴致落败,就都切声吐痰,骂他:
「真他娘鸟货一个!」
老三梗着脖子,细细弱弱地叫:
「没见割了一个口子?」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