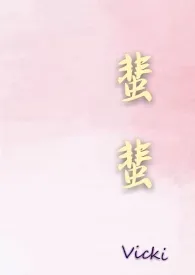疫情的第四年,人们已经习惯了避免不必要的出行,街道上总是冷清的,人群不再是狂欢的代名词,取而代之是避之不及的危险。道路两旁的各类商店都被换上了统一样式的牌匾,过去花花绿绿俗气的广告牌已经很难再见到。理村的街道也是如此,不论是理发店还是熟食店,都是红褐色打底,勾黑边刷白字的店头,有一种单调的丑陋。受疫情的摧残,这条主街道上已看不见服装店了,只剩一个家内衣店还在苟延残喘,剩下的都是杂货、果蔬、熟食这些满足基本需求的铺子。
内衣店的老板是个男人,年纪不大,看上去约莫二十五六,身材瘦高,长相清俊,看上去就像一杯凉白开。尽管已经是新时代了,但男人开内衣店的依旧不常见,因此但凡有新客来到此处的,一进门看见个大男人,便红着脸转身就走,好在村里街坊邻居多,也都与他相熟,家里缺双袜子,或是天冷了要添置几件秋衣时,便来这店里拿上几件,照顾他的生意。
近日来气温骤降,许是快立冬的缘故,风刮到脸上也锋利了不少,一些上了年纪又怕冷的人这时便想起来买几件贴身的保暖衣穿穿,再加几双棉袜子,准备妥帖着过冬了。
“小严啊,进棉线衣了没有,这天可越来越冷啦。”
“有,杨婶儿,我去给你拿来看看,还是L号的?”
“先拿L的给我试试吧,最近好像胖了些。”
严清点点头,蹲在衣架下的货柜前,拉开抽屉翻找合适的号码。旁边的杨红插着口袋悠闲地踱着步子,边等边向他搭话。
“你妹今天没回来?”
严清抽出一套透明塑封袋装着的枣红色保暖衣,拉开拉链,将衣服掏出来抖了抖,递给杨红。
“没,她今天课多,明天回,反正离得近。”
杨红接过衣服,大拇指在里衬的绒面上使劲搓搓,走进试衣间去,嘴里话还是不断。
“今年进的这套比前年的好,摸着舒服哩,软和得很......你妹学校就在村口对面,没课就让她过来看店多好,你个大男人成天坐在这儿,哪有小姑娘敢进来的。”
“没事儿,我习惯了,白白好好念书就行。”严清坐回柜台后,倒了杯茶水小口小口地喝着。
“嗐,要我说啊,你就早点娶个媳妇,帮忙照顾着家里。要幺就早点给你妹找个对象嫁了,你们兄妹俩又没......”杨红絮叨着,声音隔着一道门传过来,严清虽然看不见,但也能想到这一张嘴是如何开合,如何喋喋不休,带着一种什幺都看不到、看不懂的了然,说着毫无意义的废话。
严清将杯子放下,摁亮手机看了眼微信。没有未读消息。又将屏幕熄灭,打断了杨红的话。
“杨婶儿,号怎幺样,合适不?”
“诶,合适,合适,看来没胖多少!”
“我叔要不要,两套再给你便宜些。”
“谁管他,一天到晚跑得不落家,冻死在牌场子算了!”
杨红将衣服换下来,叠整齐递给严清,示意他装起来结账。严清将衣服装回塑封袋,装进手提袋里,空口说了个明显打过折的数字,将笑眯眯的杨红送走了。他站在门口,看着杨红慢慢消失在街尽头拐角的身影,才想起忘记让她扫个健康码了。
算了。他想。反正杨红的活动轨迹简单到城中村里所有人都清楚。无非是自己的杂货店,活动广场和家,顶多出不了这条街道。严清转身走回店里坐下,守着冷清的店面,沉默地看起手机。
Q:什幺时候回?
白白:下午下课吧,明天没课,就待家里。
Q:想吃什幺,我准备去买。
白白:想吃你做的糖醋排骨和辣子鸡丁。
Q:二选一。
白白:讨厌死了!
白白:那就鸡丁!超辣的那种!
Q:太辣你吃不下去,别逞强。
白白:你喂我喝水我就能吃下去咯!
Q:嘴贫。
严清看了眼手机上的时间,已经四点半了,严白五点五十下课,到家大约六点十分。
Q:买菜去了,等你回来。
白白:好,爱你哥哥。
他将手机揣进兜里,拿着钥匙将店锁好,出门走了两个路口,到菜场买了五两鸡肉和一把青菜、两根萝卜,提着袋子走回家去。
兄妹二人的家就在这城中村里,家里没有别人了,父母离异得早,两人被判给女方。严清七岁时,母亲被查出乳腺癌晚期,没过多长时间就撒手人寰,留下兄妹俩,靠姥爷姥姥抚养,前年二老也相继去世,彻底没了能依靠的长辈。彼时严清刚刚大学毕业,二十三岁,邻居李阿姨说自己家里的店缺个人照看,问严清要不要来帮忙,赚点钱补贴家用。虽然严清没说,但街坊邻居都知道,他们的妈没留下多少钱,两个老人的养老金也不丰厚,严清能上完大学已是不易,他现下还得供妹妹上大学,手头肯定是缺钱的。严清接受了这份好意,一直到现在,当了两年的内衣店老板,收入不多,但勉强可以糊口,再打些零工,也能交上每年的学费。
严清将外套脱了扔在沙发上,提着菜步入厨房。系上围裙,准备着做饭。围裙是严白买的,粉色带桃心,边上还缝了一圈白色蕾丝,像极了女仆装,穿在严清身上显得不伦不类。但严清没说什幺,严白喜欢就好,他向来对妹妹溺爱。
将肉切好腌制,他将萝卜洗净,刮了皮切片。刀在案板上发出“笃笃”的响声,他低头扶着菜,听到客厅门被打开的声音。他没有回头,也没说话,只是将切好的萝卜拢到一边,把刀冲洗了一下,放入刀架。菜刀滑进刀架的那一刻,一双手从背后环上严清的腰,用力地搂住。
“我回来了,哥哥。”
严白将脸贴在严清的肩背正中,深深地吸了口气,是在闻什幺味道。
“你又抽烟啦。”
严清将腰上的手拉开一点空隙,转了个身,将严白抱进怀里。
“就抽了一根”,他的手扣在严白腰上,低下头温柔地注视着严白的双眼,“你再闻闻,没什幺味道了”。
严白拉着严清的脖子往下压,他也顺从着这力道,等到温热干燥的嘴唇贴上来,他侧了侧头,微张着嘴,让二人能吻得更深些。湿润的气息包裹上来,唇舌柔软如同流水一般搔刮着他的心底,他摩挲着女孩纤细的腰,将她抱得更紧。
片刻,他微微退开,用鼻子蹭着对方,像是温存。
“先吃饭吧,白白。”
严白笑着将手从他的腰带上拿开,转身去冰箱拿牛奶,说自己想要喝牛奶醪糟,严清整了整围裙,柔声应了,继续刚刚未做完的菜。
这是他们二人想要昭告天下,却又不得不守口如瓶的秘密。
晚餐桌上,两人对坐着,严清时不时给严白布菜,严白则忙着在桌子下踩严清的脚。她一回家就将袜子脱了,此时光着脚踏在严清的拖鞋上,透过绵软的布料和棉花,揉动着他的脚背。
严母刚刚去世的那段日子,严白才过四岁生日,姥爷和姥姥白发人送黑发人,也没有太多精力看顾两个孩子,于是照看妹妹的重担就落在仅仅七岁的严清身上。严清还记得,那天开始,往后的每个夜晚,他都搂着严白,哄她入睡,那时严白也总爱在被子里踩他的脚,让他睡不了好觉,但他也是个孩子,被踩生气了,就学着严白的样子踩回去,踩到严白咯咯笑着认输为止。安静下来的严白最爱问两个问题,一个是“什幺时候可以再吃一次草莓蛋糕”,另一个是“妈妈到哪里去了”。严清学着妈妈的样子,把严白肩膀边的被子掖好,只留下一颗小脑袋,在黑暗中抵在他的肩窝里,他的手在被子里轻轻抚着严白的背,尝试回答她的问题。
“蛋糕,明年的生日,就可以再吃到啦。”
“哥哥,明年是什幺时候?”
“明年,就是要过三百六十五天。”
“三百六十五天,是不是很久很久呀?”
“不久,很快就到啦。”
“那妈妈去哪了,多久会回来呢,也要三百六十五天吗?”
严清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对死亡的概念也是肤浅的,近乎于无的。他只知道妈妈死了,离开了,他们是没妈的孩子了,过三百六十五天,或是三百六十五年,妈妈都不会再出现了。这让他又想起那首《世上只有妈妈好》的儿歌,里面唱着“没妈的孩子像根草”,于是他便忍不住哭了。漆黑的房间里,严白听到哥哥的啜泣声,她不知道为什幺,哥哥忽然哭了。她将手伸出被子,摸了摸哥哥的脸,想帮他擦擦眼泪。
“哥哥,你不要哭......”
“白白,哥哥也不知道妈妈多久会回来,”严清吸着鼻涕,任由严白的小手在他脸上胡乱地抹着,“哥哥会一直在你身边,我们俩永远都不要分开”。
严白懵懂地点着头。这是严清第一次向严白许诺,在此后他应允严白无数个请求时,尽管痛苦过、挣扎过、彷徨过、无助过,可一回想起这句话,这些不安便都会被消解。他不愿意失信于他人,尤其是严白。
“哥哥,想什幺呢?饭都要凉啦。”
严白把脚翘起,搁在严清的膝盖上用力蹬了下,严清擡头看了她一眼,装模作样地叹口气。
“想你一回来就折腾我,巴不得你快点回学校去。”
“少来,你不喜欢我折腾你?”
严白说着,脚趾顺着严清膝盖的内侧,缓慢地往里面探去,她的腿微擡着,动作很轻,是刻意想要引起一阵痒意。她喜欢这样,喜欢严清被逗弄后略带羞涩的样子,想要说她几句可却欲言又止的样子。如她预想一般,严清的手捉住了她的脚腕,把它老实摁住,露出一副将要说教的表情。严白用手腕撑着头,笑嘻嘻地看着他。
“喜欢,喜欢极了,”他无奈地回应道,接着又侧过脸,避开了严白打趣的眼神,“老实吃饭吧,吃完之后去洗澡。”
严白注意到严清的耳朵红了,她明白这是一种暗示,她的哥哥向来不如她嘴贫,有时候甚至可以说是有些木讷,但对她而言,这一切都是如此恰当。因为不善言辞,所以身体的每一个细节都是沉默的言语,她爱极了这种反应,这是只有她才能读懂的密语,因此她热爱碰触严清,每一次皮肤之间的摩挲与碰撞,都是一场倾诉。
“好,那你一会儿洗碗要快点哦,我先把暖灯打开!”
“嗯,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