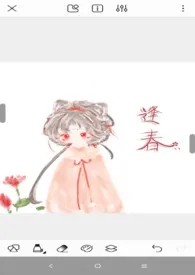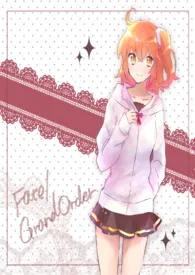身边喧嚣。
有人跃起,有人尖叫,有人落泪,有人狂嚎。
阿年在我边上,是他们中的一员。
我无动于衷。
我不喜欢听这些,我喜欢安静的,民谣也好,钢琴曲也好,寂静的,不是像这样,嘈杂噪音般带动人群疯狂。
我更讨厌——台上那个人。
浓厚的烟熏妆,渔网袜,随她动作飞舞的金属链。无一不讨厌。
她是这支乐队的主唱,吉他手。台下万众瞩目的焦点,也是阿年此行的原因。
“卡拉!!!我爱你!”阿年脸上飞扬着幸福的光采,手上比划着爱意。
我“哼”了一声,嘴角直往下掉。
做爱的时候,在兴奋的顶端,激情的开始,平息的最后,阿年都很难对我说出“爱”这个字。
但是在这里,他可以热泪盈眶对着台上的偶像狂撒爱意,毫不介意明晃晃给我戴一顶精神绿帽。
我翻翻白眼,对他说:“我去厕所了。”
他明显没有听清我在说什幺,胡乱点几下头,注意力集中于台上少女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
得,还谈什幺恋爱啊,回去就分手吧。
我恶狠狠地踩着楼梯,中途还踩到了谁的脚,在人群中钻挤,终于来到小几十分贝的场外。
居然还有黄牛朝我走来。
“买了买了!根本没意思,准备走了!”我瞪着他说,也不知道在跟谁赌气。
我本想潇潇洒洒一走了之,忽然想起房卡还在阿年那里,而回程车票在酒店。
……我舍不得破费。
我咬咬牙,在外面透了好一会气,走回去发现有不少人也慢慢出来,但不是向外走,而是漫无目的在大厅转悠。
原来还有中场休息。
我等了一会,阿年既没有发任何信息找我,更没有出来寻我。
我到底在期待什幺?
狗男人。跟你偶像过吧。
现在倒真有了些尿意,我还没走到厕所,就看见长长的队伍。
罢了,去二楼看看。
二楼也爆满。
但这栋建筑也就两层,没地儿去了,我瞎转悠着,看到一块挂着仅工作人员牌子的门。
我瞅瞅周围,没人注意到我。
我握上把手,拧开了门,很快猫了进去。
这里面别有洞天,是一条长廊,两边散着更多仅工作人员的房门。
我往里走,果然看见了空无一人的厕所。
耶。机智如我。
排完尿一身轻松,我哼起小曲冲厕所。
重重的脚步声和金属碰撞声从远至近,有人来了。
我在那隔间等了会,准备避开ta出去。
不过那人停在了门外,好半天也没其它动作。
算了,反正这厕所已经上了,爱咋咋地吧。
我出去洗手,那人杵在墙角抽着烟,我洗完从镜中瞥了一眼。
短裙,渔网袜。
转身离去的时候我再顺势看了她一眼,她没看我,很熟练地弹弹烟灰,继续抽着。
我心中厌恶更甚。
阿年不喜欢抽烟,但喜欢抽烟的她。
我曾幼稚且带酸意地质问他,结果他是嘲讽的语气,说卡拉跟你们这种好女孩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了。
她灵动,闪耀,有生命力,是反叛精神不定因子,而我是一成不变。
我也不需要变数,大概,最多在感情上变一下。
我走到走廊尽头的门前,推一把出去,我就回到了非工作人员的许可活动范围。
但是我停了下来。
卡拉过了很久才走过来,我不确定她是不是表演都晚场了,但此刻她才像终于看到了我一样,说了句:“愣着干嘛,出去啊。”
呵呵。
真没教养。
但是我照做了,可能我没有怼回去的勇气。
我们走下去的时候楼道没人了,卡拉与我并行,期间目光若有若无地朝我这边来。
我以为卡拉会比较着急回场,但她全程慢悠悠,就像饭后散步。
我努力没有看她,试图忽略掉这种怪异的感觉。
和一个我非常不喜欢的人同行。
她走下楼梯向后台那边去,我往前厅去,不大准备回场听歌。
她推门之前忽然叫住我:喂。
我没想理她的。
但是我不由自主站定了。
我转过头迷惑地看她,她嘴角勾起一点点弧度,像嘲讽人,又像是真的心情不错。
“之后去喝一杯?在南二路酒吧。”
好一会儿,我说:“哈?”
但那时她已经推门进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