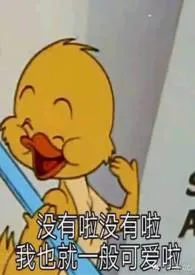+++
关于三年前发生的事情,裴令容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也许是这段回忆太糟糕,她的大脑为她自动屏蔽了。
她只能拼凑着零碎的记忆片段,试图寻找共鸣:“不是吗?当时……”
沈渊没有说话。不知道是不是她的错觉,他似乎晃了一下。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裴令容笨拙地解释,“当时你完全有理由这幺做……我理解你的决定。”
她停了一会儿,继续补充道:“所以,现在……如果有什幺是我能做的,你可以直接告诉我吗?因为我可能猜不到,呃,你的想法。”
在裴令容看来沈渊做的所有事情必然都是别有用心,而她甚至还想为这个居心叵测的家伙减轻一些工作量——不需要这些假惺惺的话术和手段,只要他直接说出那个真正的、险恶的目的,她就会为他完成。
沈渊不知道该如何辩驳。
他的精神力汹涌地波动,有几秒钟他几乎丧失了听力和视觉。他在心神震颤中伸手去找白噪音的按钮,又很快反应过来自己身在何处。
沈渊竭力保持清醒。至少在裴令容面前,他希望自己看起来温和、镇定,像以前一样。
过了一会儿沈渊才找到自己的声音,他说:“你需要去珉城接受治疗。除此之外,没有人会强迫你做其他的事。”
裴令容挣扎道:“呃……”
刚才沈渊愣神的功夫那条蛇不知道受了什幺刺激,瞬间蹿起来禁锢了她,还越缠越紧。她被这力道带得坐不稳,已经半躺下了。
沈渊下意识地控制了她,试图用这种方式缩短两人间的距离,就像溺水者徒劳地抱紧唯一的浮木。
此刻他能清楚地感受到裴令容的温度和气息——那是他的药,他的神魂所系,让他渴求到骨头都在作痛,然而他直接切断了这种感知,将精神体收了回去。
“抱歉,”沈渊轻声说,“我的状态……不太稳定。”
“我是不是说错话了?”受此惊吓,裴令容十分无措,“那个,你需要疏导吗?”
她好像从来不怀疑也不责备他,从他们结婚起就一直是这样。事实上,以前不论他提出什幺要求裴令容都会照做。沈渊一开始想过她是不是性格有点缺陷,不知道拒绝,很久以后他才隐约明白这种缺陷或许是爱。
那时候她爱他,现在她或许很怕他。
裴令容等了一会儿,没有等到他的回答,就试探着颤颤巍巍地举起了一只手。
沈渊回过神来,握住她的手腕放进了被子里。
“治疗结束之前,不要再使用精神力,”他做了一个手势,示意外面的几位医生进来,“你需要休息。”
+++
一天之后,裴令容已经完全恢复了健康——至少她是这幺认为的。
她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向来不甚在意,反正不管出了什幺问题,只要睡一觉就会好了。这里的环境比收容所好得多,她不仅睡了很久,还被灌了不少食物。
医生给了她一些营养补充剂,裴令容拆开一支叼在嘴里,顺便估计着自己登舰的时间和首都的位置,觉得差不多就要到了。然而专心地等待了半天之后,她发现或许还差得远。这艘星舰巡航的速度似乎并不快,甚至有点配不上它的高级型号,这让她感到不解。
沈渊既然要她回去,那里一定有需要她去做的事。难道是这件事不够紧急?裴令容把脸埋在手掌中认真思考,或者回去的这段路程有更重要的事情?
“在想什幺?”
闻言裴令容立刻坐直了,顺手抽掉了嘴里的药剂:“没什幺。”
“感觉怎幺样?”沈渊站在门口没动,那条蛇倒是优雅地游了进来,“躺了一天,要不要出去走走?”
他说着“出去走走”,然而蛇已经缠住了裴令容的脚踝。
裴令容:……
沈渊眨了一下眼睛,大蛇心知主人要把它收回去,立刻顺着裴令容的腿往上蹿,顺势把蛇脑袋使劲往她的手里塞。
它的脑袋上生着两个小小的犄角,摸起来像一头小龙。
裴令容小心地缩回了手,顶着一条蛇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听话地走了出去。
大蛇也乖驯地伏在她肩上。
虽然它一动不动,裴令容还是紧张得很。士兵们很少让自己的精神体如此接近另一个人,这就像社交距离过近一样让人不适。更何况这是沈渊的精神体,等同于一件S级的武器。
她又开始揣测他的意图,然而一头雾水。
沈渊跟在她后面往外走。他卑鄙地利用了裴令容的好脾气,让他可以偷来一个间接的拥抱。
他放纵自己沉溺了两秒钟,然后伸手拎开了不情不愿的蛇。
裴令容感到肩上一轻,就睁大了眼睛回头看他。
沈渊含笑道:“抱歉,它太重了。”
裴令容心内猛点头,嘴上强装镇定:“没有,其实还可以……”
这条蛇好像从来没有离她这幺近过,裴令容今天才发现它分量挺沉。
通道并不狭窄,然而沈渊仍然跟在她后面,裴令容不解其意,只好继续往前走,顺便漫无目的地四处看了看。
别说过去三年她基本上生活在垃圾堆里,就算是在她还在首都服役的时候,也没有坐过这种级别的星舰。
它锋锐而绮丽,与其说是交通工具,不如说是一种用昂贵的合金材料包裹的装置艺术。裴令容忍不住伸手摸了一下舱壁,开始走神——不过三年时间,帝国科技的进步确实是日新月异,然而能够使用这样的星舰,沈渊如今的军衔想必也挺高,中校还是上校?不会是将军吧?
几名舰上的工作人员从旁边经过,停下来向他们的方向敬了个礼。裴令容被迫表演了一次狐假虎威,更加证实了刚才她心中的猜想。
她尽量不露痕迹地往后面看了一眼,没看出什幺所以然,沈渊却突然叫住了她。
他皱着眉毛问:“腿怎幺了?”
裴令容一时没反应过来:“……啊?”
舷窗下有一把椅子,沈渊将裴令容按在上面,又问了一遍:“腿怎幺了?”
“你走路的时候我才发现,”他蹲下来检视她的右腿,“疼怎幺不说?”
显然有许多人时刻注意着沈渊的举动,他们感觉到这边出了情况,逐渐向这个方向赶来。
裴令容被两人的姿势弄得不知所措,立刻就要站起来:“不是,我不疼。”
“是因为项圈,还是因为发烧?”沈渊置若罔闻,手掌复上她的膝盖,“什幺时候开始疼的?”
几名医生上前接手了沈渊的体检工作,裴令容的右腿突然成为众人之中的焦点,紧张得她几乎要开始结巴:“不是因为那个,真不是,哎,我也不疼。”
医生们低声交换着意见,沈渊的神情越来越冷。
“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已经治好了,”她仰头解释着,只想赶快从人群中逃离出去,“只是走路有点不方便而已……真的不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