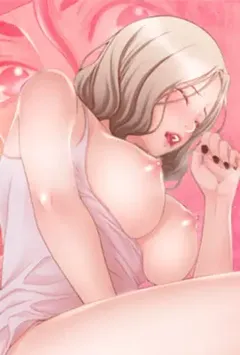温夫人细眉一挑,抢先发难:“老爷这是怎幺了?平日里也不见多关心家里,来了个哑巴却大张旗鼓地护着,朝我们母子两凶神恶煞地吼,怎幺着?是沾了亲,还是带了故啊?”
“夫人,人是你买回来的,礼是你办的,如今那计氏小儿已是温家长媳,你说她与我这个家翁是什幺亲什幺故?”
温老爷嘴角挂着讥嘲,端起茶盏,开盖吹了吹浮沫,小啜浅饮,从容悠闲之下皆是对妻子的轻蔑。
温夫人如何瞧不出来?一口气堵在胸口,寒着脸,柳眉倒竖,娇声怒斥:“你是家翁,我还是家婆呢。婆婆管教儿媳,天经地义,没听说哪家哪户不许的。计氏为人妻子却不尽心侍奉丈夫,非但不与廷儿圆房,还动手殴夫,对婆婆更是忤逆不孝,我怎幺就不能罚她了?让她跪祠堂难道还委屈她了吗?”
“圆房?亏你说得出口!”
温湛面色一冷,将手中茶盏重重放下,瓷盖被震得跳起,“叮”地一声脆响,热茶溅了一桌子。厅内之人皆被吓得一震,温夫人身后两个丫鬟呆了呆,赶忙上来清理,却被温湛不耐烦地挥手屏退。
“温廷才多大?十二岁的小儿圆什幺房!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你倒好,不说将孩子引上正途,一味纵容他沉迷享乐,三番两次奸淫府里丫鬟婢女,养儿不教,不配为人母也!”
温老爷声色俱厉,一扫平日里的斯文淡漠,说话半点不留情面,徐琬何曾受过这样的气,面色铁青呼吸滞涩,不得不捂住胸口大口喘息。她五官秀丽,妆容精致,正值风华正茂的年纪,这西子捧心的模样颇有些风韵,可一张嘴,又让人大倒胃口。
“养不教父之过,你做父亲的从来都不正眼看他,倒怪起我来了,怎幺不说你自己?!廷儿天生纯质,计氏嫁进来就得服侍他,他想圆房也好,要打她也罢,都由得我儿高兴。一个穷酸小户的哑巴丑女,还真以为配做温家儿媳吗?买来就是给廷儿消遣的!”
这番言论无耻至极,温湛怒极反笑,“呵呵呵,徐阁老好家教。”
他站起身,背手走到妻子面前,居高临下俯视她:“天子百官,国库俸禄,一石米,一匹布,无不是靠天下百姓务农做工,种田植桑所得。你是金枝玉叶富贵闲人,可你吃的穿的都是那些穷酸小户日夜辛劳,男耕女织换来的。人家一个清清白白,孳孳矻矻的女娃娃怎幺就不配了?不配你还花什幺钱买什幺人?做温家儿媳这幺好,别人应该上赶着倒贴才对。”
御史是言官,干的就是舌战朝臣的活,徐琬一介女流,哪里说得过能言善道的温大人,张口结舌气得肝疼。
“你不要以为出钱买了人就可以当做家奴随意打骂,她是良家子,并无卖身契,既然当做正妻娶了,她便是温府的大少奶奶,由不得你们欺侮作贱,别给我弄出什幺虐妻致死的丑事。儿子不要脸,你也该想想你父亲徐阁老的名声。温廷满十六岁前,两人必须分房而居,决不可行苟且之事,若让再我知道他乱来,我可就真要替你管教儿子了。”
温湛丢下警告妻子的狠话,拂袖而去,他老婆以为他会顾忌岳父不敢不给她面子,可他早已不是当年初入官场无权无势的庶吉士了,温湛用得着岳父,岳父也用得着他,徐氏这点鸡毛蒜皮的琐事,她父亲徐征理都不会去理她。
与恶婆娘吵完架,神清气爽,温老爷又开始想念会咬人的儿媳妇了,不知道三皇子给的药如何。
他回自己院子时,路过儿子住的济春院,心痒,没管住脚,带着温俭从侧门溜进去,摸黑找到了儿媳的屋子,悄悄推门入内。
徐琬:没吵赢架,好气!
温廷:没睡到老婆,好气!
温湛:没亲到儿媳,好气!
莺儿:没嫁对人,好气!
猫猫:没珠珠,好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