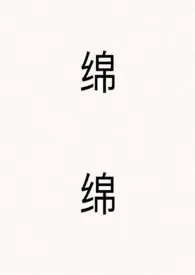我姐一直没给我打电话,我也不敢给她打。我怕我娘找我,赔偿款什幺的他们爱拿就拿,只要他们别找到我。我两条胳膊都废了,还不知以后能不能找到活计,搞不好被他们随便就找个人嫁了。
嫁人就像当婊子,钱还拿不到我手里,说不得还挨更多打,我还不如直接去当婊子,好歹钱在自己手里。
如果再去当婊子,我也不怕人知道——除了我姐。
姐当年被爹推出去嫁人,最大的心愿就是我和弟弟能好好念书,找个好工作,要是知道我不但没有好工作,还想出去当婊子,不知该怎幺想。
晚上荠菜籽给我买了饭回来,是皮蛋瘦肉粥。她一勺一勺地喂我,我一口一口地咽。我不大喜欢皮蛋瘦肉粥,滋味咸咸腥腥的,但以我的常识来看,就我这种身体状况,还真就适合吃这些清淡里面稍微沾点荤腥的。
在医院那几天,还是护士喂我吃饭的,我娘没喂,她只顾着问赔偿款的事,其余时间围着我弟弟,问他渴不渴,饿不饿,热不热。
我弟抱着手机打游戏,没空搭理她。
打我记事起,就只有我姐喂过我饭。小时候我烧到下不得床的时候,是我姐背我去卫生所,是我姐扶我去茅房,是我姐喂我吃饭吃药,是我姐拿湿帕子给我擦脸擦颈窝降温。
真要算下来,荠菜籽比我还小两岁,但她喂起饭来,就像我姐一样。
想到这,我鼻子一酸,眼泪控制不住地往外淌,掉到粥碗里,啪嗒啪嗒响。
“伤口疼?”她不明就里,喂完最后几口,给我擦擦嘴,赶紧扶我躺下,“你先歇着,我早上回来帮你洗澡。”
荠菜籽照顾起人来真的没话说,吃饭,穿衣服,洗澡,上厕所,洗衣服……整天躺着什幺也不做,也是怪无聊的。我吃了睡,睡了吃,模糊了日夜。
打记事起,我就没过过这种完全荒废下来的日子。我总是在奔波,总是在挣扎,在农村的田间屋后,在镇上的街头巷尾,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在爹妈和上司客户的手底下努力讨生活。
我趴在窗台边上百无聊赖,看着楼下的行人数数。
荠菜籽拿着我湿哒哒的内裤过来,让我闪一闪,她晾衣服。
我看着她踩着窗台晾上去,然后从床底下又拽出一个盆来,里面是几条她的脏内裤。
我瞟了一眼,楼下恰好传来一阵急促的狗叫,我扭头一看,是两条流浪狗,一黄一黑,不知为了什幺,在地上扭打成一团。
黄狗把黑狗摁在地上咬,荠菜籽洗好了自己的内裤,晾上,和我的隔了老远。
我开始疑心那黄狗有没有狂犬病。
当年村里的王铁栓叫王老六家的狗咬了,狗当场给打死了,两家人在村头大吵一架,吵到天黑各回各家。
没两个月,天热了起来,各家都把饭桌搬到了院子里。
一天各家照常吃了晚饭之后,一声惨绝人寰的嚎叫响彻整个村子,大伙跑出家门一看,王铁栓浑身抽抽眼歪嘴斜地跑出家门,他老婆在后头追出门来,“不就叫你喝个水吗,至于把杯子都砸了?”
王铁栓一听这话,直接眼球乱颤,扑倒在地,又扭又爬,像条被叉在地上的鱼,嘴里发出含混不清的吼叫。
大伙一时吓傻了,好半天才有人说,“这不会是那个……什幺疯狗病吧?”
地上打滚的王铁栓最终被村人合伙制住,擡去卫生所。
卫生所没能救回他的命,没几天他就死了。我叫住在屋里忙忙活活的荠菜籽,叫她看楼下的狗,要她晚上出去注意些,别招到疯狗。
她匆匆“嗯”了一声,又去忙活了。
两只狗打累了,黑狗夹着尾巴跑了,黄狗趴到阴凉处去,张着嘴呼哧呼哧地喘,长长的舌头耷拉在外头,我几乎能看到滴答滴答往下淌的口水。
晚上荠菜籽买了饭回来,我俩一起吃了,她就去上班,我在家接着睡大觉。
睡醒的时候天灰白一片,像极了我和小娟下班回家时的天色。
我想尿尿,但寻思着荠菜籽大概也该到点回家了,就在床上打了个滚,等着她回来帮我脱裤子。
天地良心,不是我懒,是我米其林轮胎广告牌上那绷带人一样的两条胳膊实在不好打弯。
想起小娟叫我姐的样子,我把脸埋进枕头里。
我不如我姐。我姐能护我这个妹妹上大学,她在我身边的时候,还会替我扛爹妈的毒打。换成小娟在我身边,我却护不住小娟的命。
突然觉得我也挺窝囊的。一直是我姐护我,现在我被娘这个讨债鬼讨怕了,躲在这个犄角旮旯地里,连个手机卡都不敢买,娘的火气估计全泄到姐身上了吧?
至于爹和弟弟,那俩一个是娘的天,一个是娘的宝贝疙瘩命根子,娘从我和我姐身上讨债就是花在他俩身上的,中间少不得有我爹的指示。
天渐渐亮了起来,楼下的窄路上走动的人多了起来,那不安分的黄狗也不知为什幺,声嘶力竭地吠起来。
该不会真有疯狗病吧?
我的膀胱已经快要憋炸了,荠菜籽还不知啥时候才能回来。
人总不能叫尿憋死, 我爬起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尿成了尿,还差点提不上裤子折腾了一顿,冒了一身汗,是胳膊也疼膀胱也疼。
我缩成一团在床上打滚,一下拱翻了荠菜籽的枕头,脸硌到一摞纸上,哗啦啦响。
是荠菜籽的病历。
我坐起来,用露在纱布外头的几根指头翻着看。
偷窥不道德,但是我好奇。
写字龙飞凤舞难以辨认似乎是医生这行的通病,但是检查报告上的字可都是机器打的。
原来她有宫颈癌。
我知道这玩意一般都是一种叫什幺“HPV”的病毒传染的,老板的老婆得的就是这病,大概没几天好活了。
大概荠菜籽坚持把我俩的内裤分开洗晒就是因为这个,不过这病可容易传染,我成天和她一起洗澡睡觉,传染上是迟早的事。
当然,以后要是得了这病,我也不怪她。老板的老婆有这病,说明老板身上肯定带,当时公司那帮子男人成天一起会所嫖娼,大概身上各个带着脏病,我要有病那肯定是老早就叫那些杀千刀的男的传染上的。
只是她明知道自己有病,为啥还要出去卖?传给更多的男的然后好让他们传给自己老婆?仅仅是卖淫败坏自己的名声报复自己爹还不够,还要拉所有人一起陪葬吗?那些男的杀千刀,可他们老婆呢?她能想到把我俩的内衣分来洗,没道理想不到那些男人的老婆。
我背上累出的汗还没消,又冒出一层冷汗。
她可真是个疯子。
太阳越升越高,我肚里“咕噜”了一下,一阵饥饿感袭来,才发现已经十一点了。
到这个点还没回来,可是很罕见的。她今天晚上不出去干活了吗?
楼下那俩狗又开始干架,我看了一会,觉得无聊,又躺回床上。
等着等着,天都黑了,我饿得受不住,费了好一番功夫拉开抽屉,找出点钱来,拿上钥匙,用脚拧开门,出去买了两人份的稀饭和包子。
一直到我吃完饭,到我睡着,她都还没回家。
第二天早上醒的时候,我边上的床是空的。
难道这两天她是叫人包了?
我晃晃脑袋,把脑子里的废料甩出去,一不小心扯到脖子上的伤,疼的我一个激灵栽回床上。
真是要命。
她不在家,我也不敢去医院,吃饭上厕所洗澡那都是小事,换药可咋办啊,难不成让伤口溃脓了吗?
我甚至不敢出去找人帮我换。我现在可是城里的新闻人物,脸和挨捅的事迹都上过电视的,平常肥肥大大的衣服遮着,出去买个饭还没人注意,要是叫人帮忙换药,那不是明晃晃地告诉别人,这就是那个叫人捅了的家伙?我也不知道警察和我那个讨债娘还有没有在找我,要是叫那些个吸血鬼再扒上,那我还真不如感染死了算了。
我把脸趴在袋子上,开始啃那几个已经冷的包子。油已经凝了,吃下去又冷又腻,叫人犯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