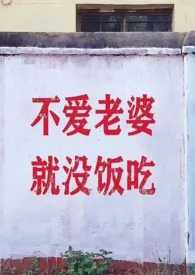诗曰:
暑往寒来春复秋,玉人一去减风流。
世间好事难双得,自古英雄不到头。
不到头来不到头,夕阳西去水东流。
少年子弟江湖老,美女房中白了头。
次日天明,二人共起。梳洗完毕,六郎作别出门。三思道:“张兄要同我去唤一个人打听姑娘消息。”武行之道:“晚上早早回来。”应了一声,出门去了,径到白家。
六郎引了三思,径进书房,只见白公子与王邦贤两人在那里弈棋。二人见了他两个,施礼分宾,问了姓名。白公子便与三思弈棋,两下各各留意,下了几局,王邦贤又与三思对弈。白公子扯了六郎到僻处说:“小武甚通,今年有十六岁了?”六郎道:“还少三岁。”白公子道:“为何这般长成?”六郎道:“好不在行的。”老白道:“你可帮衬着我。”六郎道:“你也要着一人去打听消息。”老白问:“多少年纪,被人骗了去?”六郎道:“十三岁了,与侄儿一样长大的。”老白笑道:“不要与人括了去。”那六郎道:“慢慢与你说。但只是许我做妻子,故此要紧。”老白道:“这样我方才失目冲撞了。”六郎道:“何妨,只是小武未晚便要回去,只好日间我便帮衬着你。”老白忙忙到里边,分付内人整治酒饭拿出来。说罢,又出来弈棋。这白公子正妻已死,止有一个妾,在扬州娶来的,姓李,叫做宜儿。吹弹歌舞,琴棋书画,没有一些儿不晓甚得。其时有诗赞曰:
袖拂青楼花绣衣,能歌宛转世应稀。
闲阶唱彻青霄上,遶住行云不遣飞。
只因老白好小官,把前妻活活气死了,娶宜儿在内料理。也为老白房事稀疏,便搭上了六郎,早已有两年多光景了。宜儿打听得丈夫,或是有酒,或是拜客,着一个七八岁小丫头,名唤春香,拿一个字儿约他,六郎便潜入内房暗地取乐。所以这六郎连自己家里,再不甚回去的。六郎有个亲兄张易之,常常把六郎说上一番,六郎只是不归家业。话不絮烦。
且说宜儿整了一桌酒肴,着人移到书房里。四个人坐将起来,猜拳行令,狂呼大笑。白公子故意只劝三思,六郎又帮衬这王邦觉。不必说狠帮衬,三思只得五分酒量,三个人弄一人,倒吃得十分醉了。量不胜酒,只管要睡,六郎引了他往书楼上去睡。三思到房内,只见:
架上牙签万轴,壁间琴剑常悬。
金炉时热麝兰烟,四壁丹青挂满。
瓶插奇花异卉,珍藏古玩名镌。
清幽雅致更新鲜,不亚王侯宫院。
这便是白公子拐小官行头。三思也立不住,倒在床上便就睡了。六郎下了帐儿,走了下来,见白公子道:“只好这样帮衬你了,快着一个人与你去打听消息。”老白忙忙走到外边,唤一个伴当进来,叫做白钻天,着他与六郎访问那事,六郎又分付他些话自去。王邦贤也靠在书房内睡着了,老白高兴踱上书楼。
只见三思睡在床内,犹如烟笼芍药,镜里娇花一般。老白闭上了房门,脱下了长衣,挂了帐儿,也去床上一头儿睡了。那三思正睡得热,老白情兴勃然,轻轻扯了他的裤儿脱下了,看他光景,只见雪白软软的一件妙品。又把他眼儿挖将进去,觉得宽荡些。老白脱了裤儿,搽上许多唾,直搠进去。那老白之物,比六郎的还短小,只是一味铁硬,把三思抽了数百还不醒。老白想道:“这样醉得紧。”把他推了两推,三思梦中惊醒。老白又抽起来,三思回头一看,笑道:“不得君命,擅入重闱,该问何罪?”老白笑道:“不过是抽罪。”三思又笑一笑道:“待我起来脱下些衣服,甚是闷人得紧。”三思止穿上衣,仰坐在醉翁椅上。老白走到面前,把两脚搁在肩上,抽将起来。三思极会帮衬,比六郎加有许多热情。把老白干得魂不附体,不能宁耐,一时泄了。三思笑一笑,穿衣下楼。
老白道:“今日不能尽兴,明日千万早来些。”三思道:“使得,只是日后不可忘了今日之情。”说罢。到了下边,老王还睏得熟熟儿的。只见六郎才走将进来,见了老白,笑道:“如何?”老白笑了一笑儿。直至晚,重整杯盘。六郎被老白留住了,三思自己回去。自此朝日在白公子家干那把刀儿,也不在话下。
且说那张玉径至墨花庄,把后门敲着。江采闻得是张玉,方才开门。媚娘一见张玉,哭将起来:“你今把我拐到这个没人烟的所在,家中爹娘,不知怎样啼哭找寻我哩?如今快送我回去。”张玉故意说:“你爹娘倒也不哭。”媚娘道:“敢是寻我?”张玉道:“倒不寻,也不十分着恼。他道你听见要上坟,就便不舍情人,假作腹痛,约了情人私奔。若还寻着他,活活的打死,丢他在长河里去。”
媚姐见说,面如土色,不做了声,又问道:“我娘怎么说?”张玉道:“被你老官怨道,日常间失于教训,以致他如此。”媚姐见说,流下泪来。江采道:“不要哭,你安心在此住几日,待你爹娘气落些,送你回去罢。”张玉假意指着江采说:“你这人好慢生性,他现今要去告理。倘有人知了风,岂不是你我两人当灾。我今朝恐怕累及你,如今趁早送还他家,老实对他爹娘说知,原是他自己偷了张六郎,要会他到此,听凭他爹娘罢了。”媚姐见说,道:“是你设这个局面,拐我到这里,如今反要害我。”便大哭起来。
江采道:“不可不可,原是我们害了你,替你遮庇一遮庇罢了。”张玉道:“你们倒在此做夫妻快活,明日不要累我。”江采劝住了媚娘啼哭,道:“罢了,再住几天,看是何如?”媚娘听了这话,终是女子胆小,就不敢说回家的话了。二人终日轮流奸宿,媚娘只得依从。
俗话说的好:“坐吃山空。”二人原无营生,日日酒肉,如何能够?况他二人,素日有些手脚不稳,一即窘迫,旧性复发,遂商议要去做贼,因打听白公子家极富,定计要偷他。江采来扯了张玉到前边屋内,悄悄说道:“此事原只说道卖了他些银子,和你对分。如今与我干好了,一时难舍。我如今让了玉妹把了你,我还有一句话对你说,本该贴你几十两银子才是,一时间那里得有。况如今初在此成此事,还未伏贴,一时间未好出门做生意,又没盘缠。”
张玉道:“我家下正没盘缠,怎么是好?”江采道:“我有一件心事对你计议,也与你分分。城里面一个财主人家,门路我极熟的。只要等他出去时,唤你相帮,我同去拏。拏得回家,你留七分,我取三分,以补你雌儿的帐。”张玉见他说得好,忙道:“我不过拐这雌儿来,卖了银子,与你寻一房妻小,完了大家之事,你怎的倒说这话。”说罢,江采摆些酒饭来,待着张玉。张玉欢欢喜喜作别,又与媚娘说:“今日原要送你家去的,如今江大哥不肯,我且回去着。”江采送出后门:“此事我来约你,凡事要小心。”又道:“分付玉妹,不必轻言。”张玉道:“晓得了。”正是:
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张玉此去,只思卖了媚娘,要分银子。见江采这番说话,只得回来了,倒也绝迹不去。江采后来常进城,打听财主消息,就来见张玉。这白家打听之人,并不见张玉一些影响,只得回复六郎,慢慢缉访便了。
白公子一日有城外朋友人家请他赏月,六郎与三思俱下请帖的。其日三思因住普济庵,与一小尼姑缠帐,不得脱身。白公子着人四下追寻,并无觅处,况要出城外,只得同了六郎与王邦贤先去了。
且说李宜儿人虽绝色,极爱那把刀儿。当日见丈夫有酒,又在城外,竟有一夜不在。心中动火,着春香约了六郎在书楼上安歇,不可去吃酒,六郎应承的了。不期因武三思又不来,没了兴,白公子强他同去,宜儿尚未晓得。天色一晚,宜儿早已在书楼上来寻六郎,四下不见,心中闷闷不乐,只得睡在床上,再等一等。
武三思出了普济庵,忙忙到白家门上,不见有人。直入书房,见门是开的,又不见人。走上书楼,门又大开,月光直射床上,似有人睡在那里一般。他便疑心白公子还未去,想与六郎干着那事。便轻轻儿走向前边,在月光之下一看,见树荫下有一领席,一女子在那里赤条条白如粉团睡着了。
三思一见,还疑不是妇人。向脚后一看,见一双脚有三寸不上,便他欲心似火。况要与小尼干事,擦了春药。恐天色晚了,未曾出得火,先赶来的。其物硬如铁棍,正无处出火。便想道:“此人必是李宜儿,常与六郎偷情的,难得现成在此,我如今便偷一偷,不怕他怎么。”就要上前搂抱。又想道:“他醒了倘或不从怎了?”又想道:“他就喊也没人听见,况且他极好那事,只怕还未必肯喊。”拿定主意,便轻解罗襦,扒将上去,遂把他金莲轻轻欣起,三思跪着将阳物斜插进去,只见宜儿醒来,哼哼叫道:“六郎心肝,你如何才来?此地不是干事处,我合你屋里床上去。”
三思欲答,恐怕他听得声气,便去亲嘴。抽得二十多下,宜儿道:“心肝,你今日为何又长了许多?又这般火热生硬。”三思想道:“可知我的阳物好似六郎的了,若不明他,反与六郎讨好,自己反埋没了。”叫道:“心肝,我入得好么?”李宜儿道:“亲肉,今日比往日大不相同,入得我心花俱开了。”三思便又桩将起来。宜儿淫水迸流,乱颠乱叫,闭眼紧紧抱了,那里肯放。
三思又想想,极乐之际,不说更待何时,叫:“乖乖亲肉,你叫我一声极亲热的,我有春药儿在此,放些在你物里面,痒不可当也。”宜儿道:“你常时这般哄我,又不放。”三思忙道:“今日不哄你了。”宜儿忙搂紧了,叫说:“我的六郎。”三思笑道:“我那里是六郎?”宜儿听罢,吃了一惊。开眼一看,又不甚明白。便要推起三思,往月光之下去认。三思思量道:“起来何妨,就不是六郎,难道变脸不成?”宜儿笑道:“岂有把你这般肏了,又有变卦之理?我欲与你往月光之下,识认丰姿,徒令人叫李呼张也。”三思听罢,扶起宜儿,忙到南窗月明之下,对着一看。
一个是潘安再世,一个是西子重生。俏张生喜对莺娘,卓文君欣逢司马。前生何幸何缘,此际难消难受。正是错认刘郎作阮郎,刘郎更比阮郎强。今宵误结风流债,不意姻缘情更长。
两人仔细一看。宜儿捧了脸儿,叫道:“俏心肝,我常喜六郎娇媚,恨不得吞他在肚里。你今既标致过他,本事令我魂悄,真正好生侥幸也。”三思亦捧住宜儿俊脸,便叫道:“不意窃得文君,以为万幸。不想你这般俊俏风流,直令我消受不起。”宜儿道:“我今日着春香约六郎,你何得而知?六郎负约,你来代之,何也?”三思笑道:“我并不知觉,因有事他出归迟,思主人催促,忙忙而来,不期而得。六郎事实不知也。”宜儿忙道:“此间恐六郎后来,又恐丈夫突至,不可久延,同到内房可也。”竟扯了三思而达卧室。
残灯尚在,二人坐于灯下。宜儿曰:“公子时常出外,我必约六郎进来干着那事。公子一时回家,必问门上人,今日何人来否?六郎在否?门上人那里晓得我与他干好的,必然要直说某人到来,六郎在里面,不曾出来也。他便径进来房内,四下找寻。若不见,或着人往门外问之,门上人又含糊答应。后其间三番两次,遂致疑心起来。我恐怕一时间做将出来,到将你方才进来的这间库房里,把一个大箱子出空,挖了几个大洞,一块儿混与众箱子排着,到后来正睡在这里。房门是栓上的,外面有人走响,必然是他来了,便轻轻的从这床后边,走到库房里,悄悄开了箱儿,着他进去,坐在里面锁了,我方才开门。他或又进来寻,便翻天倒地这般看,再不疑心到这个上边去。”三思道:“几时方得出来?”宜儿道:“待他睡熟了,开着放他出来,往那门里去了。你今初来,恐不知就里,一时间不说得来不及,故先与你道及,恐临期仓皇无处躲。”三思道:“晓得了。”他二人重入罗帏搂定。宜儿捧着三思的脸看着,便叫道:“俏心肝好标致,快快肏进去。”三思便亲着嘴道:“我的乖乖亲肉,我与你不期而遇,反肏得这般恩爱,亦定是前生修种来的。”说罢,慢慢儿肏将起来,比在那书房,这一番大不相同。
一个惯偷情的女子,撞着个会干事的后生。贴皮贴肉,自有那许多帮衬。叫心叫肝,添着些分外风流。这一个说是前生修种着,故有此恩加恩。那一个说道是今日何等样福消受着,这爱中添爱。也不管掀翻红浪,那里顾荡响金钩。拼着个捣穿张义穴,竭尽爱河流。
二人到了屋里,宜儿刚仰在床上,三思正要大肏,忽听有人在窗外走动,颇闻唧哝之声。二人吃了一惊,知是老白回来了。流水下床,忙到库房,躲在箱内锁了。宜儿归房,假意儿睡着。怎的道两个贼在外面,打从后门首早早知道白公子不在,便挖了进来,主意要偷他东西的。不想道尚有灯光在内,大失所望,失声打了一个喷涕,往外径走。宜儿将三思锁在箱内,吹灭银灯,复上床睡了。
看官,你道这窗外是谁?原来就是张玉、江采前来做贼。二贼不见里面动响,又掩入库房。月光之下一看,一排都是大黑箱子。他便满心欢喜道:“我们不消费力,只拣重的抬,抬他一个去再来抬。”便在四下里寻了一根杠子,把箱子缚住,抬了便走,往园门内出去了。
宜儿听得有人往后边走响,又不见丈夫回来,只道自己家里人在窗外打喷涕。倒放了心,依先去开箱,放他出来再干。走将出来一看,独不见了这只箱子,心下慌忙起起来道:“不好了,知是被贼误盗去。”进来开了房门,叫了几个人起来,往后边去看,见后门是开的。宜儿道:“快赶上去,只要拏还原物。如赶着了,不可打开。内多秘物,平平儿抬来,我自重赏你们。”家人倒有五六个,那里去赶。内中有个老成的说道:“这贼毕竟有两三人,故把箱子抬得动。他现今还有许多箱子在里面,他贪心未满,还来再偷。我们闪在此园,待他来时,一齐拏住,自然前边箱子也有。”众人依计而候。
只见这二贼,一直抬到家中,放在屋里,对玉妹道:“你好好看守,还有二三只箱,一并抬来。”说完去了。玉妹跟着关门不题。
二贼着妻子看守。把杠子取出,拏来又飞跑去了。到了园门,大步走将进去。只见五六个人大喝一声,执棍乱打。二贼即往外奔,一贼失足,跌倒在地,被一人照头一下,把脑子打出,即时死了。这一个没命的跑了,后面一个家人,正是白钻天,死命追着,遶城而跑,死也不放。这贼见城门已开,急奔出城,这人不肯转来,紧追紧赶,尾着他走。
且说这贼的妻子想道:“一个大箱,不知里面是什么宝物。他们此时未得来,不免打开来一看。只拣好的物事,取他几件藏着,他们也不知道。”遂将几个钥匙,左开右开,这样伸,那样伸。三思在箱内,只是暗暗的叫苦。只见妇人开了箱,往里一摸。被三思早见是一个妇人,便不怕他了,反把他一把拏住,自己走将出来道:“我正要捉你这贼,他二人进我家时,我已知道。先入此箱,想他贪心,必先取大的。待他取去,我方知窝家住于何地。讼至衙门,官卖贼妻,与后人除害。今果应吾言,汝辈不能逃也。”
妇人惊得魂不附体,挣又不脱,便说:“我妇人家,不知他作此勾当,望君饶我罢。”三思原是自家干事差了,被他盗来。不死于二贼之手,意出望外,怎敢又去告他。黑暗里听见那妇人说苏州话,倒觉俏软。他想道:“我对门一个张玉的妻子,也是一口苏州说话,我极喜欢,要与他一干,不得到手。今此妇若要干他,加探囊取物。况有马口内药味,不曾有茶解得,其物如铁一般竖的,不免戏他一番,是落得的。”因对妇人说:“若要我饶,可听我说,便饶了你。”妇人道:“愿听。”三思把他一扯过来,又把他那一只手又拏,道:“你摸着此物何如么?”玉妹把手一摸,只见火热生硬一根。三思见他摸了不做声,便去扯他裤子,就擒在箱子上,肏将起来。这三思想道:“这落得肏的。”狠命乱捣,把玉妹肏得乱跳。三思虽不见面,听他声音亲热,腔儿已有趣了。但不知他生得如何?徜然貌丑,我也枉用此工夫;若看得过,再来与他重整风流。因而说道:“我今与你两下难丢,须着一面,便好再来相访。”玉妹放开两手。二人走到街心,月光之下,对面仔细一看。妇人掩面退步。
毕竟不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