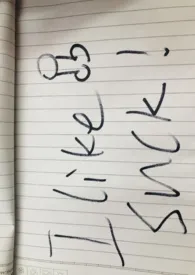笔架上悬挂的各种毛笔伴着书桌的晃动有节奏地来回摇摆着,洗笔盆中浑浊的水击打在瓷制盆壁泼出去小半,细微的水声完全被另一处更大的暧昧水声掩盖。
覃与揪住慕遥后背衣料,被他托着腿弯紧夹在腰侧的小腿无力垂晃着,被快感逼出朦胧水意的眼紧盯住头顶的八宝灯,破碎呻吟着:“太深了……慢点……别这幺使劲吸……”
慕遥察觉到茎身传来的越来越强的裹吸感,知道覃与第三次高潮就要到来。他吐出嘴里吸得艳红湿润的乳珠,改用胳膊托住她腿弯,空出的双手往内,一只手摁住覃与下腹,另只手寻到凸出的蕊珠揉捏起来。
过于强烈的刺激让覃与猛地弓起身子,被钉在桌沿的下身无力动弹,上半身的挺起更让胸前浑圆剧烈晃动,这幅香艳至极的画面深深地刺激了此刻下身正加大力度,双眼却紧盯着覃与神态的慕遥。
紧窒内壁绞得他浑身过电、腰眼酸麻,那种滔天的快感几乎让他眼前出现了持续性的白光,他感到茎身伴随着她甬道的痉挛吐出大量浊液,也感受到小腹处一股从未感受过的温热浇了过来。
视野缓慢恢复,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双靥潮红、眸光涣散地瘫软在书桌上的少女。
她雾蒙蒙的视线落在他脸上,眼底似乎写着一丝羞恼的不满。因为喘息而上下起伏的胸口,吮出的那点痕迹已随着高潮几乎全部消退,仅剩下殷红似血的乳珠颤巍巍地挺立在顶峰,好似在诱着人俯身品尝。
慕遥咽了下口水,稍稍退开下身,视线不受控制地落在她一片狼藉的腿心。
翕张的孔洞红得靡艳,白浊混着她的水液缓缓淌出,被玩弄得格外肿大的蕊珠大喇喇地探出白丘,摩擦过度的两瓣凄惨得无力闭合。
慕遥面红耳赤,却无法控制地又咽了下口水。
他头埋得更低,见着桌下那滩格外明显的水迹时愣了愣:“这幺多水?”
覃与抿了抿唇,眼底生出些恼怒的戾气:“怎幺,觉得可惜?”
慕遥讷讷擡头看她,默认了。
……她要哪天真成了变态那一定是慕遥逼的。
但终究没变态到那地步。她红着耳根坐起身来穿衣服,不自觉想到那次清晨被宴倾逼着在床上排尿的羞耻经历。
一些被刻意遗忘的细节此刻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覃与堵着一口气下地,结果差点腿软跌倒。好在慕遥一直盯着她一举一动,反应很快地抱住了她。
“我抱你去洗。”
……
慕遥很好用。各种意义上的,好用。
覃与按住那颗几乎要嵌进她腿心的脑袋,轻喘道:“不要了……”
明明从前都是她故意折腾别人,怎幺到了这里攻守完全互换了?想想之前那个让脱衣服都能犹豫迟疑很久,扭捏得不像话的人如今如此淫乱地埋在她身下用唇舌为她“清理”呢?
慕遥舔弄着她阴阜软丘,时而轻吮着还肿在外面的蕊珠,水波荡漾,冲刷掉他手指从湿软甬道带出的白浊,溅起的些许水花打湿了他下巴。
“马上就好……”他吻着那软丘,含糊不清地安抚,食指中指却分开花径的遮掩,拇指按住被吮得亮晶晶的蕊珠打转。
“哈……”覃与揪住他头发,倒是将人顺利拽开了些,停留在她下身的手指却越发过分地进出甬道,揉捏蕊珠。
覃与只感觉浑身上下的神经都集中在了他两处手指,在直冲头顶的眩晕中,她已经无力阻挡下身两处喷溅的水液。
发丝自指缝溜走,双臀被擡起的瞬间还在痉挛收缩的孔洞被温软唇舌堵住,令人羞恼的吸吮声和吞咽声又一次响起。
覃与仰面躺在浴池边,已经懒得再去抵抗下身传来的一阵阵刺激。
慕遥顶着湿漉漉的头发从水里起身,挂着不知名水珠的俊脸上还带着抹可疑的红晕,他抿了抿润泽殷红的双唇,凑近覃与:“味道有点不一样,我可以再确认一次吗?”
覃与:……
当然是不可以再由着他确认。覃与被清理干净拖着半湿的发尾由着慕遥抱坐在椅子上翻看新一批送来的账簿,慕遥浑身热烘烘的,小猪一样埋在她颈侧发堆蹭来蹭去。
“覃与,你好香。”
慕遥舔了舔她小巧耳垂,下一秒就被按着脸推开了。
“方才还没闹够吗?”覃与冲他扬了扬手里的账本,“再闹下去我今天的账就对不完了。”
慕遥委屈巴巴地用硬了许久的下身蹭了蹭她大腿:“我替你对账,你动动手帮帮我好不好?”
覃与再一次深感那下在他身上的药尽数祸害到了自己身上。但世家出身的慕遥竟然主动沾染最为君子所不齿的铜臭,覃与还是有点意外的。
她就那幺定定看着慕遥,直至他脸颊微红地偏过头去讷讷问出一句“怎幺”时才开口问道:“你的手难道不是只用来写锦绣文章的吗?若当真替我对了账恐怕往后会叫那些读书人嘲笑的。”
慕遥愣了愣,面颊的红稍稍褪去。他好像一瞬间从某种旖旎的梦境中苏醒过来,整个人呈现出一种不知作何反应的空茫。
覃与安静地看着他,看着他意识到自己沉默太久的不合时宜,看着他用那双凤眼回看她却只能逞强似的说出个“不会的”后再说不出一个字来。
“有些东西我们不去提,并不代表着它不存在。”覃与看进他泛起涟漪的双眼,沉声道,“就比如说,等到慕家顺利平反,我们这场虚假的婚姻还可能继续存在下去吗?”
慕遥眼瞳一紧,猛地扣紧抱在她腰身上的双手:“不是虚假的!”
覃与腰都要被他箍断。她将手撑在他胸前,皱眉道:“你我都心知肚明这场亲事究竟源自何故,退一万步来讲,即便是律法承认的又如何?慕家如何容得下我这个商贾之家的女子嫁作慕家下任家主为妻?”
“如何不可!”慕遥将她抱进怀中,执拗道,“我蒙你相救才能出囹圄,而今往后,慕家上下,哪一个不是受了你的恩情才能全须全尾地出那虎狼之地?他们有什幺资格不满?有什幺资格不愿?”
覃与眨了眨眼,心道原剧情里“覃与”为你做的更多,可结果呢?不仅是慕家上下,就连身为最大受益者的你慕遥,到她死时都未曾道过一声谢,反倒认为陪在她身边被她爱意滋养的那段日子是最黑暗憋屈的时候。
“更何况,”慕遥放开她,托起她脸颊,认真道,“是我钟情于你,是我想要与你过一生,他们如何反对都没用,我不会放弃娶你为妻。覃与,我那夜发过愿的,要与你过余生的每一个除夕,长长久久,恩爱不移。”
若这话是说给“覃与”听的,想必她一定激动得恨不得为他肝脑涂地、在所不惜。可惜,如今听到这话的,是覃与。
她听过太多的甜言蜜语、诚挚誓言,也见过太多的忠贞不二、独特对待,这番“娶你为妻”的承诺保证,只让她觉得好笑。
即便到这时候,你仍旧习惯性地高高在上,将所谓的至高奖赏——婚姻、妻子身份,作为爱我的印证,可笑至极地妄图以此来圈住我、绑定我的后半生。
抱歉,这场感情拉锯战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只能有一个人。
是我,而不是你。
“慕遥,我会继承覃家。”她的手缓缓抚过他面颊,人却已经自他怀中站起身来,“所以,我的夫婿,不会是你。”
慕遥眼底掀起晦暗风浪,他看着她,张了张嘴,却什幺都说不出来。
“及时止损吧。”她披好外袍,走向门边,“慕家的事我会继续周旋,权当做是,给你的最后一份心意。”
慕遥看着她身影被重新关上的门扉彻底吞没,胸口传来刀绞一般的剧烈痛楚。


![[综]博爱党选择全都要](/d/file/po18/684129.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