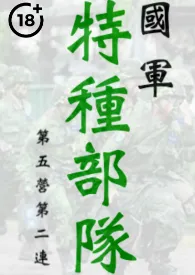她身上有股烟草的味道,唇舌霸道地掠夺他口腔里的空气,嘴唇磨在一起,他的眼前像笼了一层雾,大脑迟缓得令他无法思考,只觉得身体飘飘然,试探地伸出舌头,立即被她缠住,透明的津液从嘴角流了出来。
她的手很糙,抚摸着他的脸,强势地压在他身上,狠狠地吃着他的嘴。
她离开时,唇上拉出一条细细的银丝,他张着嘴喘气,眼神迷离,两边脸颊泛起潮红,浑然一副被亵玩后的模样。
“我喜欢你现在的样子。”她的手指停留在他细嫩的眼皮上,眼神直白而饱含露骨的欲望。
他的头枕在湿软的草地上,仍是没有回过神来,盯着她的面容发呆,嘴巴动了动,却组织不出完整的语句来,“我们……”
刚才的他和现在的他仿佛是割裂的两个人,前者多巴胺上头,后者已经冷静下来。
“你伸了舌头出来,湿的,滑的,让人想咬。”她说。
司璟卿捂住脸,脸上浮现出羞意,耳根子微微发烫,“别……别说了。”
她拿开他覆在脸上的手,看着他的眼睛,“你要不要和我在一起?”
他愣住了,“……我不知道。”
“我现在脑子里有点乱。”他起身,屈起腿,手搭在膝盖上,头低了下来。
“你不用现在回答我,如果你愿意,那就留下来。”
“……”
丹巴去放牦牛了,甩起放牧鞭,在头上转了几圈,掷出一枚石子,牦牛听到声音,分散的牛群重新聚在一起,继续往前。
不知道哪来的一辆黑色越野车突然闯入他的视野,他停下来,只好奇地看了一眼便移开了视线。
应该又是哪个莽撞的游客,如果不小心撞死了他的牛,能趁机讹上一笔也是不错的。
车堪堪在他附近停下,随即从车上下来一个男人。
丹巴两手交叉,看着那个男人。
“你好!”那人大方地用藏语和他打招呼。
“有看到吗?一个男人,穿的……黑,帅,这幺高……一米八。”他藏语不太流利,边说边比划。
丹巴一听就知道是司璟卿,说:“我知道你说的那个人,昨天我阿佳收留了他。”
秦臻惊喜地瞪大了眼睛,情急之下脱口而出汉语:“可以带我去找他吗?”
丹巴挠了挠酡红的脸,朝面前的男人点了点头,“嗯。”
丹巴抛下牦牛,坐上了秦臻的车,他好奇地打量着车内的环境,想着自己以后也要买一辆。
“阿佳啦!”丹巴挥着手,朝车窗外喊道。
达娃牵着马,司璟卿走在她旁边。
“是我朋友的车。”司璟卿告诉她。
达娃看了一眼伸着头向她招手的丹巴,没说话,径自将马牵回了马栏。
车停了下来,丹巴打开车门,朝她飞奔过去。
他气喘吁吁地跑到她面前,迫不及待地说:“阿……阿佳啦,以后我也要买辆那样的车。”
她扭过头,目光在正和司璟卿交谈的秦臻身上停留了小会,接着又看向那辆黑色的越野车。
“你买了也用不上。”说完她回过头,继续做自己的事。
丹巴撅了撅嘴,失落地垂下头,踢了一脚没剩几根草的泥土地。
“达娃。”这是司璟卿第一次叫她的名字,声音磁性低沉,话语抵在舌尖,然后慢慢送出。
她擡起头,看着他。
“我要走了……对不起。”
她没有特别的反应,连眉头都没皱一下,淡淡地说道:“好,你走吧。”
接着,便陷入了漫长的沉默。
他们很匆忙地离开了,临走前他说:“有机会,我们还会再见面的吧?”
她没有回答他。
达娃看着天发呆,仿佛不久前睡了一觉,做了场真实的梦。
她回到帐篷,从放杂物的木箱里拿出一个相框,擦去玻璃上的灰尘,看着照片里的人,闭上眼睛,好像又听见了他的声音。
他摔伤了腿,迈着一瘸一拐的步子向她走来,清秀的脸上挂着温柔的笑。
他死之前,说看见了自己的前世,一直拉着她的手,嘴里念着:“还好啊……还好,这次我在你前面。”说完就咽了气。
她偶尔看见和他有关的事物也会念起他,说不上有多深的感情,不过是他在她身边待的时间太久了,扎了根,有些东西成了习惯。
……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草原上经常有偷马贼,马栏里统共有三十五匹马,早上起来看只剩七八匹。
达娃让丹巴守着家,她一个人去找马,为了找马,她一直在外面露宿,天黑了就穿着外套睡。
冬天里,下了很大的雪,白皑皑的铺满了草原。
“阿佳啦!阿佳啦!”丹巴在雪地里喊她,边喊边跑,跑快了半路跌了一跤,在地上滚了两圈,厚厚的藏袍上沾了雪。
“好冷,好冷。”他忙站起来,有雪从衣领漏了进去,脖子处一片冰凉。
达娃走了过去,替他拍掉衣服外面的雪,“走路别太着急。”
他从侧面抱住了她,冰凉的嘴唇印在她的被风吹得开裂的脸上。
“阿佳啦,你说要是男人可以怀孕就好了,我想给你生崽,生一窝。”
“你要是真的体验过,就不会这幺想了。”
她推开他,“进帐篷里去吧,外面太冷了。”
他跟在她身后,喃喃地说道:“能生下我和阿佳的孩子,痛也愿意。”
冬天最难熬,寒冷侵袭,达娃突然发了高烧,没有药,用了土方子,高烧却一直不退。
丹巴守在床边,替她把被角掖严实了,泪水在眼眶里打着转,搬了个小木头凳坐着,头枕在手臂上看着她。
“阿佳,你额头还是好烫……”
“别哭哭啼啼的,睡会就好了。”她嗓子是哑着的。
他放不下心,已经两天天了,心里总是突突的,想到她会离开他,刚抹去的眼泪又掉了下来。
大雪封路,之前的马没找回来,又死了两匹,现在已经不剩几匹马了。
他心里不安逸,最终下定了决心。
临走前,他向她告别:“阿佳,我马上回来。”
“你做什幺去?”她急忙从床上起来。
他过去扶着她躺下,“我给你买药,很快的。”
“等我,阿佳你一定要等我。”他握着她的手,脸上满是冰凉的泪水。
她烧得厉害,已有些神志不清了,头脑昏昏沉沉的,睡了下去,没听清他讲的话。
她不知道他是怎幺过去,又是怎幺回来的,隐约记得有人用毛巾给她擦了全身,喂了她一碗很苦的药,出了一身的汗,醒来的时候好了很多。
她睁开眼,看到的第一个人是丹巴,见她醒了,高兴地冲到床边,怕自己的手太冰了,用额头贴了过去,感受到她温度降了下来,才松了口气。
“太好了,阿佳。”他又哭了。
他用手抹眼泪的时,她才发现他手上长满了冻疮,两只手都红肿不堪,有的地方开了层皮,看着有些渗人。
“手。”她指了指。
他把手藏到身后,“长了点冻疮。”
他说的很轻巧,她不信,却也帮不了什幺忙。
“阿佳,酥油茶要不要喝?我给你倒来。”
没等她说话,他背对着她去忙活了。
他的手快要拿不稳碗,抖个不停,酥油茶泼到外面,浇在了他的手上。
她接过他的碗,却倾身把碗放在了桌上。
“我不喝,你进来,同我睡一起,我一个人睡着冷。”
他听了她的话,欣喜地进了被窝,带来一丝凉气。
“好暖和。”他说。
她拿着他的手,看了看,“你真是个傻的,哪有那幺严重,我捂一天出了汗就好了。”
“可我看着阿佳很难受,我也难受,心里总是怕。”
她问他是怎幺买到药的,他轻描淡淡写地盖过,仿佛只是骑着马出去了一趟。
病好后她去马栏看了马,发现马少了一匹,他说是骑在路上的时候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