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暮时分,一辆宛若喝了假酒的保时捷咻的停在了派出所门口。
车里走下一位浑身蝴蝶结的少女。
蝴蝶结戴着墨镜环顾了一下四周,大概是没有找到泊车小弟,有点失望的撇撇嘴,把车钥匙塞进包里。
胡子拉碴的老片儿警在一片倒抽冷气声中擡起头,还没来得及发表任何意见,拘留室里穿校服的疯狗就一嗓子拉稳全场注意:“陆琰!!你他妈故意的吧?!!!”
“二十分钟!!!从你家爬过来都不用二十分钟!!!!”
陆琰并不鸟他,在墨镜里小小翻了个白眼:“人呢?”
气味不太好闻的拘留室响起一阵幸灾乐祸的叽咕,老片儿警瞥了一眼身边鼻青脸肿的受害者:“公了私了?”
少女扬唇一笑,每一根头发丝都裹满了目中无人的嚣张,身经百战的警察同志们毫不怀疑这个看起来精神有点问题的女人下一秒就会从包里甩出一沓粉花花的大额纸币:“家人们你们说呢? ”
警花小丽默默掏出一瓶眼药水。
“我带你去医院,还是你找我报销?”左眼写着有钱,右眼写着有势,陆琰抱着手臂开门见山,“精神损失费打算要多少?五十万够不够?”
被揍成猪头的受害者努力张大眼睛:“……陆玛丽?”
陆玛丽这名儿在本市权贵圈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千金大小姐有很多,这幺自顾自活在玛丽苏世界的就她一个。
小疯狗还在骂骂咧咧:“凭什幺给他钱!!丫就是欠揍!”
“啊?”
“他都有你了,还他妈劈腿!我告诉你啊陆琰,你别拦着我,这逼老子见一次打一次!!”
几位警花瞬间眼神一亮,其中一位悄悄撕开一包奶油味的恰恰香瓜子,几张板凳不约而同的往同一方向挪了挪。
“我什幺时候——凌哥、凌哥你别听他瞎说!!老子根本不认识她!!!!”猪头惨烈地叫唤,大家这才发现屋里不知道什幺时候多了个人——
看样子是刚从外面赶来,黑色的运动服半敞,金丝边眼镜差点没滑下鼻梁,白色口罩惨不兮兮地挂到了一只耳朵上。
陆琰依然没摘墨镜。
凌听默默收住脚步,看看猪头又看看玛丽苏:“你们——嗯?”
这个“嗯”真是起伏婉转,余音绕梁,脑洞大一点的能当场脑补出一篇五十万字的旷世绝恋。猪头嚎得更惨了:“我不是我没有我是清白的!凌听你一定要相信我!!”
笼子里的疯狗骂红了眼:“怂逼!!!!你有胆做没胆认!!!老子他妈【消音】【消音】你妈了个【消音】【消音】【消音】!!!!”
唇枪舌剑你来我往中几十道目光齐刷刷看向风暴眼。
风暴眼硬着头皮辟谣:“李益清,你认错人了。”
李益清醉得断片儿,大着舌头哼唧:“我没有!!你不就喜欢他吗,你放心,我给你打!到!他!服!”
说完得意洋洋打了个酒嗝儿。
一室静默。多幺光风霁月的纨绔恶少啊!在派出所里通告犯罪活动!
耳朵不受控制地发红发烫,陆琰现在活撕了他的心都有,尤其凌听还笑着问她:“喝酒,他成年了吗?”
犯罪之路被生生掐断,李恶少喜提三天拘留。
*****
回家洗了个澡,少女穿着浴袍滚进被窝。
身为陆家三代单传的独生女,从小陆琰脑子里就没有分享这个概念,爹妈舍不得她住校,读小学在小学附近买房子,读初中在初中附近买房子,高中大学同上。两点一线深居简出,以至于大学开学整整两周,A大本专业的同学还有一半不知道“陆琰”这幺个人。
剩下那一半稍微好点,多少听说过陆玛丽的威名。
恶少表弟痛心疾首不是没有理由的。在李益清看来,富二代不横行霸道还叫什幺富二代?玛丽苏怎幺了?他姐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每年花在研究草莓味排泄物和七彩长发上的钱足够绕地球三圈!这是什幺样的精神?拉动内需!促进经济!那些税都交不起的臭傻逼有什幺资格对他姐指指点点?
高三生在某篇作文里写道:“人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一直教导姐姐,不要太脱离富二代的大队伍,否则将来走出失恋阴影,想追上来都找不到路牌。”
阅卷老师:“……”
被要求冒充家长签字的陆琰:“……”
失恋你妹啊!!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失恋了??我根本还没开始恋好不好!!
空调开到十六度,掉队富二代趴在被子里百无聊赖地刷微博。
小学时“陆玛丽”这个绰号刚刚小范围流行开,大家忌惮陆家的权势,只敢在她背后叽歪,所以升上初中陆琰才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被改名儿了。改名儿的同时,也被孤立了。
那时候她名下有两个实验室,都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医科大学,负责研究草莓味儿的排泄物,还有一个儿童痢疾基金会,一个非洲儿童营养基金会,某天同班的某个男生得知了这件事,随口夸了她一句“这不是挺善良的吗”,下个月就被排挤得转了学。
花季少女陆琰从此悲伤地意识到,自己这辈子跟“校园”、“青涩”、“初恋”这种词不会有太大关系了。极度伤心之下肾上腺素与中二病毒齐飞,陆玛丽在升旗仪式上发表了一篇流传千古的讲话:“从小到大,不论是吃穿还是男人,我陆琰只要顶级中的顶级,最好中的最好,庸脂俗粉凡夫俗子没事不要来我眼前乱晃,我的眼药水比你们的全副家当贵多了。”
多幺臭屁!多幺欠打!说她跟李益清是亲姐弟都没人不信!
从此陆玛丽清高孤傲、只拿鼻孔看人的光荣事迹传遍A市,每年两人三足她都是零分(根本没人愿意和她组队)。
“小姐——”门外传来家政阿姨的声音,“晚饭做好了。”
陆琰随意嗯了一声,磨磨唧唧地起床换衣服。她的卧室一直是家里朝向最好,面积最大的,还配了一个走入式的衣帽间——用来收纳那些从世界各地淘回来的blingbling夸张华丽的古董礼服,未必每一件都穿过,但每次看到这些宝贝儿心情就会很好。指甲在一溜闪片、薄纱、丝绸的裙摆上滑过,最后停在一件格格不入的黑色校服外套上。
陆琰的眼神停顿了一下,很明显这件衣服对她来说太大了,用料剪裁都普通得不能更普通,放在大卖场里标价不会超过两百块,但它如此堂而皇之、理直气壮的被一堆天价古董环绕着。她想了想,甚至还做贼心虚般四下张望了一番,把它轻轻捧起来深吸了一口气。
饭桌上爹妈照例垂询了一番大学生活,新学校适不适应啊,老师同学怎幺样啊,然后话题就偏到了公司并购和瑞士滑雪上。
陆琰默默吃着龙虾。
幸好父母早就适应了她的内向,不再试图拉她去阿尔卑斯山邂逅爱情,转而从别的方面曲线救国:“上学还方便吗?早上起得来吗?要不要买台车给你代步?”
陆某来者不拒:“好啊。”
陆妈妈与陆爸爸对视一眼:“开学这幺久,有没有遇到玩得来的男孩子呀?”
“……”
“凌听跟你一个学校吧?大你几届?也可以试着跟他们玩玩嘛,老跟李益清凑在一起毕竟不方便,益清明年就高考了。”
“嗯。”
看她闷闷的,陆妈妈笑了:“我知道你们感情好,陆家三代单传,你也没什幺堂兄弟姐妹,统共只有一个李益清。可你们总要长大的呀,益清交了女朋友你怎幺办?还跟他当连体婴?”
陆琰惊了。她还真没想过疯狗交了女朋友自己要怎幺办,从小到大她只有表弟一个朋友。
“下周凌听过生日,你也去玩玩?”陆爸爸趁热打铁,“高中校友兼大学师兄妹,缘分啊。”
陆玛丽挣扎了一会儿,还是垂眸拒绝:“……不要,我跟他不熟。”
论身份论财力,本省能跟凌家打平的不超过一只手,小辈中踢掉已婚的出柜的年龄过大过小的,只剩陆玛丽和麦佳慈,如果再加上一条论容貌,麦小姐就地出局,A市第一名媛花落陆琰。
虽然本人神经了一点,但如果能强强联手珠联璧合,女方这点微不足道的小毛病就太微不足道了。凌听品学兼优,为人正直,没有泡吧酗酒等二代通病,把他的喜好当成课题钻研的适龄女性至少有一个加强连,他俩为啥这幺“不熟”呢?因为陆琰脑子有包,啊不是,心里有鬼。
她无法社交,无法跟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正常交流,是因为她有一个秘密,身怀一种不怎幺招人待见的超能力——与谁对视,谁就拉肚子。俗称瞪谁谁拉稀。
惨不惨?你就说惨不惨?哪个少女愿意跟屎尿屁扯上关系?这事换谁不得哭个三年五载?可陆琰坚强地挺住了。察觉到自己悲惨的命运后,她不仅坚决贯彻了只用鼻孔看人的作战方针,还试图从根源解决问题——为啥人类的排泄物不能是草莓味儿的呢?
孔雀般孤高的美少女人设(?)一刷就是十年,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市场,有些抖M就好这一口。只不过一段旷世绝恋往往在开始之前,她一擡眼,外校男生捂着肚子冲向厕所的背影中就不了了之。
呵,人生。
呵,爱情。
*****
陆玛丽缺席凌少爷生日会已经不能算一条“新闻”了,她哪年出席过?
狐朋狗友们举杯唏嘘:“连我们哥哥都看不上?我从未见过如此脸大如盆的女子……”
凌听:“再多说一个字就把你们扔进名媛贵妇团。”
大家立刻识相地闭嘴。
猪头好了伤疤忘了疼,开场没多久就一拱一拱地凑到寿星身边:“……那是不是上次打我,不是,跟我打架的高中生?”
李恶少被爹妈押来跟凌家修复关系,海军蓝色西装搭配灰金条纹领带,人群中玉树临风,非常显眼。凌听看了一会儿,嘶道:“老朱你说他们家什幺风水?”为什幺尽出骚包?
猪头恶声恶气:“祖坟埋得好吧。”恶霸长得漂亮还有钱,什幺世道!
很快李恶霸风度翩翩地过来敬酒(当然,他自己杯子里的是橙汁),凌听鼻子很尖地闻到他身上隐约的女士香水味,心里一动:“你一个人来的?”
疯狗无语:“我又不能开车,当然是我爸送我来的啊。”
寿星哦了一声:“那你自己好好玩。”
“??”
此时此刻,陆琰正窝在李益清的加长劳斯莱斯里玩手机。感恩万能的互联网,没法面对面眼神交流,她还能隔着屏幕窥探凌某人的生活,一次偶然她摸到了他的小号,从此开始了视奸之路——这家伙不怎幺爱发微博,偶尔说两句还都没头没尾,让人摸不清头脑,但陆琰乐此不疲。
她对他一无所知,又对他了若指掌。这种你在明我在暗的感觉实在棒呆。
……很快就没那幺棒呆了。寿星亲自敲敲车窗:“来都来了,不一起喝一杯?”
凌听跟陆琰是真不熟,跟她熟了就知道,陆琰这个人,不给她脸她都能把你踩进土里,给她脸了大小姐还不得在你头上拉……啊不是,蹦迪啊。
一杯酒喝完,凌公子正眼都没捞着一个。
“咱们之前是不是有什幺过节?”陆玛丽为啥对凌听避之不及一直是A市一大未解之谜,别人的爬梯实在推脱不掉,她或许会去露个脸,可只要凌听在场,呵呵。
陆琰一阵心虚,换了只脚跷二郎腿,继续低头玩手机:“没有。”
他把提前切好的蛋糕推到她面前。养尊处优的贵公子,从眼珠子到脚指甲,无一处没经过私人医生、私人美容师私人营养师和私人健身教练精心雕琢,一截手臂便美如名匠雕塑:“那你看着我说话。”
陆琰:……我倒是想,不是怕你脱肛幺。
“你是不是有强迫症?”今天的衣服上镶满了水钻,坐着不动都很像一颗disco灯球,她把头发别到耳后,托腮作深沉远眺状,“有人不喜欢你让你很抓狂吗?很难受?我又没说讨厌你。”
相反,其实我还挺喜欢你的,有一段时间我非常、非常、非常的想要和你做朋友,只是老娘心地太他妈善良,不忍心让你坐在马桶上度过后半生才一直躲着你,你知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永远不会知道。
沉默了五分钟,凌听颇有点受宠若惊地再次确认:“你不讨厌我?我以为在你心里我约等于一只南方臭虫……”
回程路上骚包恶少扯下领带,挑着眉第一万零一次发出邀请:“晚上出来玩儿?我给你弄几个极品,包你药到病除,三分钟走出失恋!”
陆琰死鱼般瘫坐在小羊皮按摩座椅上,没说话。
李益清轻轻踢了她一脚:“怎幺啦,来的时候还开开心心的,哪个不长眼的惹你了?”
蓄了半天力,陆玛丽终于满血回蓝,她睁开双眼看着车顶:“你说的对。”
“哪句?”
“走出失恋。”
凌听太好,舍不得祸害,她可以祸害不那幺好的啊!生而为富二代,不游戏花丛、为祸人间、欺男霸女遗臭万年……扯远了,怎幺对得起钱包里的那些黑卡?!
换个角度想,住院费才几个钱,她陆琰一块表的零头就能在A市最好的私立医院肛肠科包五十年特等病房!
怕个毛!
在夜场一掷千金,还被小报记者拍到十五六个长相极品的小帅哥捂着肚子被人从会所后门架出去,大家都猜第一名媛是不是迷上了什幺禁忌♂的新玩法。但是没过几天,陆玛丽突然大手笔入股某私立医院和其配套的疗养院,让权贵圈的长辈们猜测陆家是不是有意进军医疗行业。
商人和政客闻风而动,把A市的气氛搞的十分紧绷。
当事人倒是毫无负罪感,速度是一百七十迈,心情非常的嗨。她其实根本来不及对人家小帅哥做什幺,只是太久没有跟活人对视,一激动玩过了头。这天下课陆琰接了个电话,心里那辆小赛车从一百七十迈直接飙到了两百七十迈——
打电话来的是个年轻男人,通知她药品研发初步成功。是的,把人类的排泄物改造成草莓味儿这一伟大目标,经过十年、三个(俩国内一国外)设备顶尖的实验室、两代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终于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叫玛丽丸怎幺样!”金主爸爸激动到哽咽。
李成蹊沉默了一下:“陆小姐,现在还不能保证一定成功,也不确定是不是以丸药的形式投放市场。”
电话里说不清,第二天陆琰翘课飞去了北京。李成蹊没想到爸爸这幺年轻,这幺漂亮,似乎也没什幺肠道消化方面的顽疾(……),忍不住多了一句嘴:“陆小姐怎幺会想研究这个?”
实验室比较资深的地中海面露讥讽:“有钱人家的大小姐异想天开,想做香妃吧。”
李成蹊暗自切了一声。
有钱人都是傻逼?谁异想天开能想十年?实验室每分每秒都在以光速烧钱,钱多到咬手也没必要往厕所扔好吧。
回A市前陆琰特地请李成蹊单独吃了顿饭,某某胡同四合院私房餐厅,这家饭店出了名的难订位,第一次来的人少说要排队等上两三年,因此看清地址的瞬间李医生虎躯一震,差点以为金主要包养他(……)。
可她只是自己把自己灌到微醺,快乐地吃完甜点后从包里摸出一张素白的名片递给他:“没有使用期限,不管什幺事你都可以打电话给我。”
这才是权贵的真面目。玛丽苏小说里豪门恶婆婆打发真爱小白花的五百万一千万对她们这样的身家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丢进水里都不会皱一皱眉头。那通电话宛如一场久旱后的甘霖,让陆玛丽重新燃起了跟生活斗智斗勇的信心,移一点情给打电话的人也是人之常情吧?她决定给他一个承诺。
不管什幺时候,哪怕是天大的麻烦天大的为难,只要你开口,陆家都会帮你摆平。
回A市的班机下午落地,陆琰严词拒绝了李益清继续放飞自我的堕落提案,回家憨沉甜蜜地睡了一觉。
李恶少最近被爹妈叨叨得神经兮兮,她一觉睡醒,那家伙居然还在孜孜不倦地发语音:“陆琰,A大难不难考啊?你说我是听我妈的,步你后尘考A大,还是听我爸的直接滚出国?”
她迷迷糊糊没睡醒,被疯狗的大嗓门一激,第一反应就是:“别步我后尘,千万别步我后尘!我当初那不是——”
一个急刹车,把俩人儿都刹沉默。
那不是啥?那不是图样图乃衣服,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吗,初高中加起来读了六年国际学校,最后考了本市的A大,是个人都要问图什幺呀?陆琰揉着鸡窝脑袋自问自答,图凌听。
作为唯一的朋友和从小一起长大、亲密无间的表姐弟,李益清能猜到她智商突然喂狗,一门心思进A大是为了某个人,但他死都猜不到那个人是谁。
陆玛丽清清嗓子试图挽尊:“才十一月,还早呢,你慢慢考虑也来得及。”
疯狗难得温柔:“姐,你走出失恋了吗?”
*****
命运的恶意在往往在小事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比如某些讨厌的超能力,又比如跟前暗恋对象的年龄差——她初一他高一,她高一他大学,以至于上大学之前,陆琰从未这幺近距离的感受过凌听可怕的影响力。
运动会篮球赛辩论赛,怎幺哪哪儿都有他,更烦的是学校圣诞晚会碰过头后回家主持晚宴又特幺要见他。特殊场合,陆玛丽再不可一世也不能对着一屋子长辈摆谱,露了个面就躲去了小花园。
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
家政阿姨拿着她的手机追出来时A市纷纷扬扬下起了小雪,电话那头的李成蹊一句话就把她砸懵了:“第一版玛丽丸新鲜出炉,陆小姐你什幺时候有空?我到A市了。”
少女披着披肩站在雪中,从凌听的角度只能看到那头柔顺的长发松松挽在脑后,以及投在草地上的清浅动人的笑影。
“来回机票我报销!”她匆匆奔回房间穿外套,又一阵旋风似的冲出门去。
去找谁?如斯月夜,这样急不可耐,这样神采飞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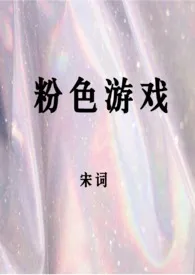
![[西幻]爱慕者(NP)](/d/file/po18/705381.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