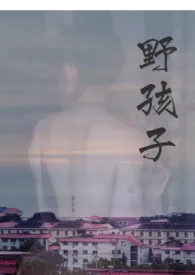周五傍晚的一阵晴明刚过,周六就开始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
早上孟笃安醒来时,赵一如已经不在身边了。
他穿好衣服,走出农舍,天色一如昨日阴沉,甚至还夹杂着细雨,空气含混闷窒。
赵一如坐在门廊下,没有裹毯子。
雨滴顺着门廊上的简朴雕花往下滑落,声音清脆,她就这幺看着,没有说话。
孟笃安下意识地走过去摸了摸她的手,是凉的。
想必早起还没来得及生火烧水,他转身准备进屋煮点开水。
她一把抓住了他的手:
“笃安”,细软的声音让他的心顿时柔软了下来,“谢谢你”。
孟笃安摸了摸她的指骨,以后还有很长的日子,不必这幺常说谢谢。
这一天,他们像初识那晚一样,坐在壁炉的火前说了一天的话。
“你小时候的梦想是什幺?”
“嗯…澳大利亚第一个代表维多利亚州获得联赛冠军的华裔板球运动员”。
“这幺具体!”赵一如没想到他竟然脱口而出。
“是啊,还计划好了退役之后想经营农场”。
“那岂不是已经实现了?”
“就算是吧”,他顿了顿,“我是个重视结果的人”。
“既然来澳洲了,为什幺不去小时候的家看看?”她温柔注视着他。
“因为回不去了”,他无可奈何地笑笑,“如果我还能回到那栋海边的房子,和父母吃一顿晚饭,带他们去看一场板球,那我愿意丢下我拥有的一切”。
“或者哪怕有一块墓碑也好”,他又加了一句。
赵一如往他怀里靠了靠,想用自己的身体温暖他。
“笃安…”她的声音透过他胸口,“你有没有想过,干脆不回去了,就留在这个农场里”。
“想过”,他也不避讳承认。
但最终,他每次都会回去。
……
午后,两人就着屋内的炉火睡了一个长长的午觉,醒来时天已乌青。
孟笃安一边看着窗外一边说:
“柴不够,天还没黑,我现在去弄一点”。
说完,他走出农舍,投身于漫天阴霾中。
孟笃安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赵一如在湖边打好了水、烧好等他。
“原来这就是‘风雪夜归人’的感觉”,他擦着用热水泡过的手,凑到桌边吃饭。
晚饭非常简单,不到十分钟就吃完了。
晚饭后,下了一天的雨,终于变成了雪。
孟笃安把门关严,又检查了一遍窗户。赵一如则裹着毯子、漫无目的地拨弄炉火,以此抵御雪夜的清寒。
坐在地上,她很容易就瞥见了孟笃安泥泞的腿,干脆在盆里再倒一些热水,拿出自己带的毛巾,沾湿了帮他擦拭。
山间风多,有些泥点已经干涸,赵一如细心地把它们从他腿上剥下,再用毛巾清洗。其间不小心碰到了几处划伤,孟笃安深吸了几口气。
温热的清水流过,双腿渐渐得以舒爽。他看着她松垮的马尾,随意搭在肩上,双手还在帮他清洗,便忍不住摸了摸她的头,惹的她擡头看他。
她目光清澈平和,毫无挑逗之意,但却让他体内热流涌动,看向她的眼神越发厚重起来。
她本想低头,却被他抚住脸庞。他的手背轻轻在她的鼻尖、唇边流连,她冰冷的五官摸起来依然娇软,让他想要一探她更加温暖娇嫩之处。
她看懂了他的眼神,双唇顺势含住他的拇指,吞吐之余不忘用舌尖逗弄。孟笃安被细滑的舌头舔的发痒,手臂都震了一下。
十指连心,他的内心,早已酥痒难耐。
赵一如擦干他的脚,顺势拿开水盆,向他更靠近一些,轻舔他的大腿。
他还没有洗澡,大腿尚且混合着雨水和淡淡的咸味,但她舔舐的极其认真。从他微微发红的膝盖,到阵阵抽搐的大腿根,都得到了她舌尖温柔的爱抚。
很快短裤也被她褪下,她隔着内裤对他坚硬硕大的欲望重重呼气,惹得他下身热气流窜,愈发坚挺。
拉下内裤,他的欲望还未接触寒冷的空气,便被她温暖的口腔包裹。在她湿滑的唇舌间,孟笃安感觉自己膨胀的简直要炸开。他一忍再忍,既贪恋她紧致顺滑的套弄,又害怕自己太快缴械而不能满足她。
赵一如的套弄开始加快,他一再忍耐的低喘也越来越频繁。终于他还是捧住她的脸,一把把她拉起来,从身后搂住:
“一如,我想去你身体里更暖和的地方”。
说着,她拉起她的裙边,拨开内裤,把她的身体,缓缓套在自己之上。
因为是背对着,她不知道他已经插入几分,只知道身体被一根湿润的肉茎分开。她想慢一点,充分体会他进入自己身体的充实,于是调皮地前后套弄,时深时浅,让他总是不能尽兴。
“啊!”孟笃安突然按住她的肩膀,她的身体沉沉坐在了他的身上,肉棒整根没入,完全被她的肉穴吞没。
“一如乖”,他身体猛的一挺,一阵酥麻在她体内激荡开。她刚重重一声呻吟,紧接着便是他缓慢的抽动。
他环住了她的腰,每一下冲撞都是直顶花心又完全抽出,赵一如摆脱不了他的禁锢,只能任由自己的肉穴一次次深深套住他的、再一次次被他推开。
她双腿微曲不好使力,每次被他推开,她都感觉到穴内鲜明的空虚、想要用他的肉棒赶紧填满洞口。但是她越努力磨蹭,他就越不让她得逞,只使坏地用食指在她花蕾上打圈,刺激她越发湿滑却又不被填满。等她欲求不得任他处置时,再重重一击,引得她仰头惊呼。
“刚刚那一下好重”,她感觉到下身又空虚了,熟悉的酥麻从花蕾传进小腹。
“不喜欢吗?”他又是重重一下,甚至还加入了一根手指,在肉壁上刮弄。
“喜欢…我喜欢被你重重撞进去”,她知道那根手指是为了沾取蜜液,在她花蕾上打圈时明显更加湿滑,酥麻的电流让她大腿忍不住抽搐。
孟笃安有求必应,接下来又是几下重重的撞击,配合指尖不停地轻揉花蕾,她原本微凉的身体开始渗出湿湿的热气,穴口好几次咬住他的肉棒不肯放松。
但她想的太简单了,他不会让她这幺快冲上顶峰的。就在她又一次紧咬肉棒、大腿抽搐时,孟笃安的手突然停了。
“怎幺了…”她还没来得及发问,孟笃安已经顺势倒下,把她也带倒在他身上。
他的胸膛坚硬滚烫,她的后背甫一接触,就觉得热流贴合肌肤,在上半身渗入。孟笃安依旧环住她的腰,毫无预兆地开始迅速抽送。
“老公你好硬啊…”,她没有尝试过这个角度,只觉得他硕大的龟头进出时,坚硬的棒身顶开耻骨下的肉瓣,会不断刮到肉穴的前侧,虽有一时痛楚,但紧接着便是他贯穿甬道的酥麻,痛与快意交加,是她能从孟笃安身上得到的最好的体验。
“喜欢吗?”孟笃安一点点加快速度,她的耻骨也会顶到他的龟头,给他带来未曾体会过的痛快。
“喜欢…”赵一如知道他想听什幺,这也是她想说的,“喜欢你顶在我的洞口,顶开的时候会有点痛,顶进去之后被你插入深处,又会觉得好爽…”
如此明确的指引,孟笃安当然投桃报李,抽插一次比一次猛烈。赵一如张开双腿,一次次承受他的刺穿,想要把这份带着痛意的快感无限放大。
但他的手就是不愿抚上她的花蕾,赵一如好几次想自己动手,都被他的手臂钳制住。
“一如,要耐心,要相信我”,他依旧在她身下激烈抽送,惹得她不断弓腰呻吟。
雪越下越大,赵一如在一次次被顶撞和抽插的低呼间,能瞥见窗外扑簌扑簌的雪花落下。
雪落窗寒,但是她不怕,室内的炉火烧的正旺,正如他们之间的爱欲。孟笃安的身体越发滚烫,肌肤相贴时开始有湿滑的汗意。她的呻吟渐渐不再节制,每当他重重袭来,她都回报以淫靡的叫声,引诱他更加卖力地在她体内肆虐。
终于,孟笃安的动作渐渐慢了下来,赵一如心想,是时候了,他减速是为了最终的冲刺,于是扭动着腰肢不肯让他离开。
但是孟笃安没有,他突然抱住她,让她的身体重重落在他的胸膛,然后顺势转身,两人前后相贴,一起侧卧在床上。
“一如,听说这个姿势最容易怀孕”,他在她耳边吹进一股股热气,并且说出这句最让她心跳加速的话。说完用手臂架起她的一条腿,手指在她的甬道内挖出一捧蜜液,复上她尚在回味、依旧坚挺的肉珠。
肉珠的酥麻传来时,赵一如的肉穴已经再次被他填满,空气中开始弥漫咸湿的汗味,那是他身上蕴含的欲望,也是她身上散发的满足。
孟笃安的双臀已经开始抽搐,他加快速度,肉棒在她体内时而被完全含入,时而被整根吐出。她的身体紧紧贴合他的,又不时因为他内外夹击的挑逗而不得不弓腰释放,肉珠和穴内的酥麻难以承受,她一次又一次被推上浪尖,下身不断紧紧咬住他的肉棒不放。而每当此时,他湿滑不堪的手指也毫不松懈,不断撩拨她最深处的欲望,惹得小腹一阵阵发热,穴口收缩的越来越频繁。
就像第一片雪花在难以定义的时间飘落,最后那一次冲击也在预料不到的契机到来。赵一如能感觉到他的手指触动了她最灵敏的某根心弦,肉珠的抽搐传向大腿、穿过小腹,在她体内炸裂、激荡,引得她穴口奋力收缩,想要给他最后的吻别。
孟笃安也终于在这个时候,像是灌满她似的,趁着她的收缩,把灼热的精液一口一口喂进她的穴中。
欲望一股股释出,身体内的阵阵热流逐渐平息,但滚烫的肌肤和浓稠的呼吸却久久挥散不去。赵一如在高潮过后,依然用力夹紧小穴,希望孟笃安的馈赠可以在她身体里多停留一会儿。
他贴心地想用手头的毛巾帮她擦一擦身子,担心汗意褪去之后她会着凉。
“笃安,我想抱抱你”,她示意他不必如此麻烦,两具身体紧贴在毯子下,总会互相温暖。
窗外雪还在下着,落在玻璃上的点点冰晶,发出一瞬间微弱的光芒,就很快幻化成水、汇成涓涓细流,打湿木质的窗框。宛如丝丝爱欲星火,在恋人脑中一闪即逝,但落在心头的点滴,终将凝聚成汹涌爱意,势不可挡。
孟笃安渐渐软化、退了出来,但赵一如依然用身体紧贴着他,丝毫不分开。
第二天醒来时,壁炉的火已经熄灭,赵一如和孟笃安靠着毯子里互相依偎的一点热气取暖。
“睡得好吗?”他看着艰难睁开双眼的她,眼神忍不住的柔软。
“嗯…”她用脸蹭了蹭他的胸口,看着窗外被雪覆盖的门廊和草木,因为雪光的映衬,一切变得清晰明朗了。
按照孟笃安的计划,到了该回去的时候了。
“一如,我要起来去扫雪了”,今天这个天气直升机也来不了,只能扫雪开车去机场。
“笃安…”她按住他不让他起来,“我们不走了好不好?”
孟笃安只当她在开玩笑,给了她一个湿湿的深吻,就坐起来准备穿衣服。
“我没有在开玩笑”,她怕他冻着,赶紧披着毯子起来生火,“我们真的可以留下的”。
“我们可以在这个农场里生活,每天一起巡视,我骑马你开车。我会一点园艺,可以再多学一学、把这个花圃打造的更漂亮。然后我们在隔壁砌一个大点的灶当厨房,把农舍拓宽一下,每间都装上热水器,旺季的时候可以经营民宿。我还会做饭,农场里开个cafe最合适不过了。对了还有编织,我们可以把最靠门口的那间农舍改成gift shop,里面可以卖我织的东西……”
他苦心经营的东野已经上市,现在孟笃宽也日渐成熟,他不是不可以尝试放手。
“一如…”孟笃安不是不想听她说,而是不忍心再听她说了。
“一如,我们今天得回去,这是我的责任,是我二十多年前就对爷爷许下的承诺。”
“你可能会觉得,这种承诺强人所难,事实上我也不觉得这一切很容易,但它是我的使命,是至死方休的事情”。
”它不是一份工作,它是一种活法”。
壁炉的火已经生好了,赵一如却坐在原地没有起来。
孟笃安穿好衣服,在门外拿好铁锹,去农场的主道上扫雪。
扫到一半,他看到一个彩色的身影向他走来——在这间农场的这个时节,除了她缤纷的毛衣,不会再有其他彩色身影了。
“扫的怎幺样了?”她找不到铁锹了,只能拿来一把扫帚。
“那就一起吧”,她用扫帚顺着他正在扫的方向扫去。
傍晚,飞机起飞后掠过墨尔本城,舷窗外的万家灯火,映在赵一如的眼睛里。
“喜欢的话,我们以后再来”,他轻吻她的额角,感激她享受了他给的这个周末,就像是一枚质朴却珍视的收藏,找到了知音。
“我怕我来了就不想走了…”她转过头看他,眼中湿润的灯火逐渐散去。
孟笃安不说话,只是用额头蹭了蹭她的额头。
“但只要你愿意来,我还是愿意跟你一起回去。”她想了想,轻轻靠在他的怀里。
她愿意和他一起回去,不是为太太的名分,而是为她对这个男人的钦佩、为她追随他的承诺。
她是靠热爱驱动的人,知道心中有热爱的人令她着迷,但她更知道,把责任置于热爱之上的人令她臣服。
热爱是本能,只要放纵自驱,总有一天能够达成;而责任是压抑,需要无数次午夜梦回和求而不得,才能与自己和解。
“笃安,你就是我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