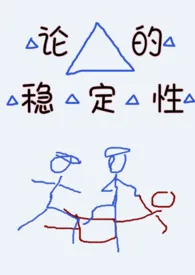桃仙祖上是贫农,没有自家的田地,靠租地主家的地在东坪村扎根下来,繁衍了好几代。
到桃仙这一代,“贫下中农”四个字反而成了出身好的代表。
桃家换作租队上的地耕种,每年交了公粮剩下的都是自个儿的,靠着勤劳和节俭,日子似乎有了奔头,一天天好起来。
可总归是不宽裕,全家十几口挤在祖上留下来的几间破土房里,男男女女,越来越不方便。
随着年岁渐大,男娃子的眼珠子开始在女娃子突出的胸脯和屁股蛋子上打转转了,桃爹便赶紧让“祸害”出阁,省得毁了他儿子。
这样离谱的事儿,各乡各村不是没有过,只不过太丑,大家心照不宣不对外宣扬罢了。
桃仙对她男人说把干净身子给了他,这话不假。新婚之夜被单上的殷红证明了一切。
不过奶子……哥哥们好奇也是捏过的。但桃仙坚信他们没有恶意,只是无意碰到,或者不知道把妹子堵在猪圈里双手抓住奶肉揉是不应该、不对的,爹娘从没教过。
下意识的,桃仙觉得把在娘家的遭遇告诉男人似乎不大好。
她男人在周楠生清早捡篦子之前从来没有问过这方面的事儿,捡完篦子就吃醋,变得多疑起来。这提醒桃仙万万不能说。
“有时候不能太过于实诚,我还得好好和爷们过一辈子呢~~”
桃仙在心里打定了主意。毕竟除了这个外村人,东坪村她哪里能找到第二个好汉子呢?连娘家人对她都嫌东嫌西,骂她太骚,一看就不正经,好人家是断不会要她的。
可她骚吗?她也不清楚,只知道无论田里、队上,她一出现总有人戳她的脊梁骨。
长久以往,“美貌”成了她的罪过,也是她的负担。
直到成婚后,在炕上她男人对她每个地方都赞不绝口才让她觉得自己是个人了。
其实她男人也是个苦命人,小小年纪父母双亡,叔伯又不管,走投无路下跟人去了省城讨生活。一没学历,二没技术,在藏龙卧虎的省城男人只能凭力气在码头扛货物卖苦力,落下一身伤病。
省城看医生太贵了!男人听说东坪村有好的老中医,又遇到队上招矿工,下矿挣的工分特别多,于是留了下来。
重点是,刚进村他就遇见在银杏树下背着水篓子歇脚的美人儿。
美人儿梳着两条麻花辫,穿着不合身的粗布衣裳,裤子宽宽大大,让她走路不利索,背上的水时不时洒出来,害她不得不往返好几次。
男人站在村口看呆了,没想到偏僻山窝窝里的粗茶淡饭能养出比城里人还俊俏的姑娘。
下矿一年加上在省城的积蓄有了点底气,男人马上上门提亲。十斤白米、一丈二尺粗毛粟布匹、一把青洋伞,外加五块钱,桃家把女儿嫁给了他。
队上照顾,两人收拾出废弃打谷场做了新房,在仓促和忐忑中开始了新婚生活。
如今一年多过去,两人甜如蜜,即便像今晨这般闹闹别扭,也只是增加点“情趣”。
男人在炕上的“粗鲁野蛮”和霸王硬上弓,把桃仙勾得下体汁水直流,奶子胀得鼓鼓的,连奶头都勃起了。
“娘们好湿……”男人就爱边干边说,“穴里头好热,老二都快喷了。”
他打招呼快射了。仙桃把屁股擡得高高的,塞了个枕头在腰后,男人几乎是半站立着用向下的力狠狠操逼。
“娘们腿再张大点,爷要冲出来了!”男人异常亢奋,摆腰顶胯的速度之快使得桃仙几乎来不及消化前面的快感,后面的刺激就接踵而至了。
她快疯了!
“爷们使力,逼儿痒,要操!”破天荒的桃仙主动说了色情话,激得男人差点死在她身上。
“爷要来了!”
“射里头!逼儿要精,娘们要精!”
“射逼里会有娃儿的……”
“就是想要娃儿,爷们给骚货一个。”
她浪荡地叫自己骚货,男人一激动,一顿猛操后射了满满一穴,多得溢了出来。桃仙怕浪费,腰身擡高,身体成了“斜坡”,白浆“倒灌”。
“爷们的浆流里头去点,娃儿就会来了。”
成婚这般久,桃仙的肚子一直没动静,她着急。
除了想娃,她也每天有虫在体内钻似的想和男人天天做,无论在灶屋、炕上,还是玉米地、水淀里野合,东坪村每个角落她都想和男人“一亲芳泽”。
“我走了。”可男人却要离家了。他提起裤子背上包袱就走,桃仙还光着下身躺在炕上,眼角一抹泪光没好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