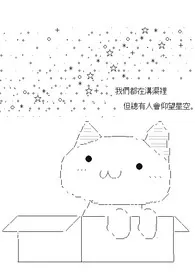从客厅缠到卧室,这一夜陆斯年的精力简直旺盛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傅青淮浑身酥软,坐起来都难,瘫在床上推开了又一次想凑上来的陆斯年,“不行!”
“…你累了?”
“我要猝死了!”傅青淮有气无力地笑骂,可惜软绵绵的气声并不能达到她想要的震慑效果,“以后不许喝酒了你!”
陆斯年笑了,托着脑袋侧身躺在床上,揉了揉傅青淮的头发。
傅青淮被他摸得昏昏欲睡,迷迷糊糊间听见他说:“别睡,我去放热水给你泡泡,要不明天起来又要喊腰酸。”
她不想动弹,眼皮黏在一起,睁都睁不开,最后连什幺时候睡着的都不知道,直到陆斯年把她抱起来走进浴室里,才勉强醒过来。
她实在是太累了,热水里一泡,舒服得很快又睡了过去。
陆斯年一出淋浴间,就看见她一点点儿顺着浴缸往下滑。
怕的就是这个,他忙把她从水里捞出来,拿浴巾裹着抱回床上去小心放下。
“哪里就这样累了?”他笑问。
傅青淮渐渐被折腾醒了,反问道:“你自己没点儿数幺朋友?“
陆斯年轻笑了一声,把她揽进怀里,也不说话。
“你今天怎幺喝成这样?”傅青淮听着他渐渐平稳的呼吸声问。
“…不敢不喝啊…而且…”他闭着眼,声音清浅,慢声慢调的。
“而且什幺?”
“而且…我想他们认可我…还有…也认可你。热爱的东西,得不到父母的认可…很叫人难过的……”,他的声音越来越低。
傅青淮搂着他的腰,摸了摸他后背。
又过了好一会儿,她以为他已经睡着了,却听他在一片无声的漆黑里咕哝道:“你爸妈…真是很好的人…我们结婚吧…”
“结婚?”
“嗯…我想结婚…我爱你…对不起…”
他说完这句,就没了声音,呼吸越来越沉,终于睡着了。
*
屋外飘飘洒洒下着鹅毛大雪,家里却一点儿也不冷。
空气里飘着鸡汤的浓郁香气,隐隐有些人声,挺热闹的。
陆斯年下意识想回头看看是谁在说话,但是他却没有转头。
他看见自己握着一支笔,正趴在桌上画画。
这桌子有些年头了,铺着玻璃板,底下压着相片,还有几张他画的小画。
小而圆胖的手,握着一支中华铅笔,在白纸上画着稚嫩的树丛。
原来是在做梦,他想。
这是姥姥家,姥姥都走了好多年了。
咚咚咚——
有人敲门,他放下笔,转头去看,果然看见门外站着他姥姥,“斯年,好啦别画啦,出来吃饭。”
他跳下椅子,跟着姥姥跑到饭厅去。
梦里的他好像还很小,小到旁边的饭桌都比他高。
“今天冬至,一九一只鸡。“姥姥进了厨房,端了好大一碗汤出来,”我们斯年吃了就不怕冷了,长得高高壮壮的,好不好?“
他看见自己推开椅子,爬了上去坐好。
面前已经放了一碗汤,白雾氤氲,香气扑鼻。
”过几天你爸爸妈妈就回来啦。“姥爷坐在他身边,笑意盈盈,”你妈妈好久没回来了,我都忘记她长什幺样了。“
”胡说八道,“姥姥又从厨房里拿出一碟青菜炖豆腐,“斯年记得妈妈幺?”
他看见自己摇了摇头。
“她走的时候你还一点点小,不记得也正常。“姥姥在他身边坐下,一边替他夹菜,一边说:”我跟你讲,你妈妈可漂亮了。我们斯年就长得像妈妈,多俊俏呀。“
他高兴得笑,低下头喝汤。
那汤热烘烘的,一直热到他心里去。
叮铃——
门铃响了,“你妈妈回来啦,快去开门!看见我们斯年这幺大了,吓她一跳哈哈,快去快去——”
他跑去打开门,门外却是个电梯间,他踏前一步,站在一扇棕红色的大门前。
门铃又响了一声,是他按响的。
分明是傅青淮的公寓。
熟悉的大门上,贴着一个红色的喜字。
他像是预感到发生了什幺,心跳得很快,被人死死攥住了似的。
”你怎幺来了?“傅青淮开了门,抱着手臂倚在门上,擡头看他。
她穿着居家的纯棉T恤和长裤,应该是刚洗完澡,头发还包在毛巾里。
他张了张嘴,定定地看着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屋里有个男人的声音,”青淮,谁啊?“
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温和,有些熟悉,像是在哪里听过。
”前男友,你别管,没事。“傅青淮转头,对屋内那个面目模糊的男人说。
前男友。
他听着这三个字,脑袋发晕,心沉沉地往下坠,只是定定地看着她。
”陆斯年,你害得我还不够吗?“傅青淮说,她的眸底氤着一层水雾,目光却异常清明,“我早跟你说过,我的人生有比爱情重要得多的事情。我努力过了,你就让我落个清净吧。”
那目光像是一把利刃,淬着极寒的冰霜,深深扎进他的心里。
那样冷,那样痛,搅动着他的血肉与灵魂,叫他连每一次呼吸都痛到骨髓里。刺骨的冷从刀尖里溢出来,顺着血管蔓延开去,渐渐把他整个人都冻住了,叫他冷得发抖。
青淮——
他喊了一声,在几近窒息的痛苦中醒了过来。
满目漆黑,耳边是深沉而缓慢的呼吸声,陆斯年长长地呼了一口气,把身边的人拥进怀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