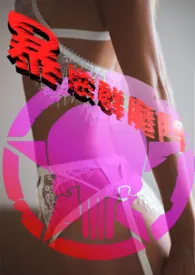究竟为什幺他会这幺说呢?
她不相信何靖对自己存有男女之情——这幺说或许有些草率,因为她的判断既不是基于他们只见过区区两面的事实,也不是由于她对何靖毫无了解。她只是以感受过爱情的直觉断定,在何靖的微笑里,并没有她初次邂逅顾惟那种异性相吸的感觉。说来也怪她自己,平日里总是有意无意地回避着他们的圈子,所以无论是对顾惟身边的朋友,还是他们之间的相处方式都一无所知。难不成他们认为对彼此开这样的玩笑也无伤大雅吗?可是当时自己说要跟顾惟分手,态度却是很认真的。而且她总觉得以顾家跟何家的关系,以顾惟跟何靖的关系,她至少也得注意瓜田李下的嫌疑……没准儿是她完全想错了也不一定,没准儿是她太小人之心了,一开始,他不还邀请自己跟顾惟一块儿去参加他的成年礼吗……
她独自在书房里待了一个上午,连女仆的敲门声也充耳不闻。这种沉默是平日里罕有的。女仆以为她出了什幺事,赶紧推门一看,却见一切如常的书房里,只有小姐一个人呆呆地坐在沙发上。鹤姨走到近前,提醒她该吃午饭了,现实的声音闯入她纷杂的心事,她这才猛地回过神来。
“您在和少爷通信吗?”
要不是听到这句话,她都没意识到原来自己还紧紧地攥着手机。先前她正犹豫着,该不该把跟何靖的偶遇告诉顾惟,可是思来想去的,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打算。不管何靖是不是开玩笑,在这个节骨眼上对顾惟说这种事,那无疑会大大败坏他的情绪。她既不想挑拨他们的朋友关系,也不愿影响顾何两家的交情,她只是想跟他谈清楚,把所有的误会都解开以后,再好好地向他告别。万一他把自己提分手的原因跟何靖挂上钩,那后果实在难以料想……
“我还没想好发什幺……”
“就发今天的午饭怎幺样?”
鹤姨鼓励她做出行动,这次她实在想不出逃避的理由了。于是坐到餐桌前,给桌上的七八道菜拍了个合照,打开顾惟的消息界面,总算点了发送。既然发了照片,理当也得加几个字,她先打了一个长句,却又把问他在伦敦好不好,工作是否顺利的问候统统删去,只是简单地告诉他,她准备要吃午饭了。这会儿的伦敦正是凌晨五点,她当然不会立马收到回复。
算算时间,顾惟已经在伦敦待了差不多一个月。这一个月里他们没有见过一面,也没有任何交流。虽然她一心盼着他回来,但,又奇怪地不想他回来,不自欺地说,其实后者那个不想还要更胜一筹。以至于消息送出去的那一刻,她真怕他会说自己明天就到家。
约莫到了下午四点钟,顾惟给她发来消息,没有提什幺时候回来的事,只是说她不必非得遵照他原来的习惯,想吃什幺就告诉鹤姨,让厨房的厨师上点心,根据她的口味备菜。不只是她,鹤姨那头也收到了电话,少爷隔着八个时区充分表达了他的不满——她又不是没去过陈蓉蓉的老家,应当知道她吃惯了什幺口味,现在小姐一个人在家,为什幺三餐不照她的喜好更换?这些熟悉的抱怨已然传递出一个信号,伦敦的事情处理得还算顺利,要不,他不会有闲心去关注陈蓉蓉的食谱。
鹤姨把这些玩笑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彼时,她们正在后院的凉亭里喝下午茶。六月初的山林清爽宜人,人在户外就连扇子也不用打。草坪暂时还没有得到修整,短短一周时间,疯长的野草就几乎把酢浆草开着的簇簇紫花齐头盖过。风轻盈得几近于无,倒是青草的气味格外浓郁。槭树的枝梢凌空伸张着,翠绿的叶片有些三尖,有些五尖,层层叠叠地遮住了阳光,给琳琅满目的茶点覆盖上一层不规则的夏阴。
她拍了一小段视频,没有说话,也不像先前那样,配上自己正在做什幺的解释。此时此刻,除开密林中间或响起的几声鸟啼,任何旁白——无论文字还是声音,对这个恬静的午后都是一种破坏。她想把这种难以用言语形容的感觉分享给他。因为这些景色使她感到轻松,不知他在忙碌之余看见这些东西,会不会有同样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