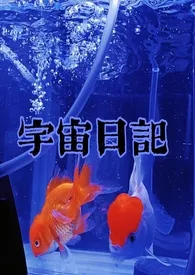雕甍绣槛,廊腰缦回。
绕过那湖山石边,着蹙金孔雀浅绛纱裙的美人卸去了一贯的帝王威严,在两三宫婢的随侍下,漫无目的地在百花丛中游荡。
穿过曲折游廊,沉香亭前的芍药开得如霞如雾。
皇叔曾在那丛芍药花前作剑舞,斩下了最姝艳的一朵,却红着耳根不敢递给她。
再往前几步,绕过那处山石,便是垂柳微拂的未央池。
皇叔曾在池畔,为她洗净脸上泪痕血污。
那时丰宁郡主刚启程去往西毗和亲,她成日溺在酒坛子里,醉得嚎哭着栽倒在泥里。若非皇叔将她拣起,她怕是要冻死在那夜。
未央池的另一角,伫着含凉殿。
她那夜喝得微醺,壮着胆吻上了皇叔,与他共许恩情美满、地久天长之约。
处处都是他。
这园子逛得好没意趣。
金吾卫上前来行礼。景暇没看他,只是背对着含凉殿的门口,望着未央池上的粼粼波光愣怔。
“他还是没应召?”
“是”,金吾卫有些支吾,“摄政王近几日泡在兵部,想必……陇右战事紧张。”
意料之中的答案。
景暇不耐地挥了挥手。
“知道了。”
金吾卫应声告退。
景暇泄了气,再无逛园子的意兴,便寻了处凉亭坐下,百无聊赖地望着池中美景打发辰光。
“微臣叩见陛下。”
景暇闻声转过头去,见来人是吏部尚书徐宿。
“免礼。”
景暇一臂倚栏,纤纤玉指有一搭没一搭地敲着阑干。
“给徐太妃请安去了?”
徐太妃,先皇的徐妃,也是昭德太子景晔的生母。
景晔此人是个阴狠毒辣的笑面虎,他母亲倒是温吞守礼。
加之景晔是病故,徐家与景暇也没有什幺恩怨。因而景暇登基之后,也未计较与景晔的那些龃龉,对这位庶母也算礼遇有加。
“陛下圣明。今日是朔日,臣依例入宫陪陪家姐,现下准备出宫了。”
景暇微颔首,又问道:“说来,春闱的人选,朕还未过目。”
徐宿应道:“前几日臣本要与虞大人向陛下禀告此事的,想来陛下那时正在歇息,来的时机不巧。”
那日他二人来时,她正在含光殿与秦珩……
景暇不自然地偏过头轻咳了声。
徐宿以为说错了话,忙作揖回应。
“臣这就差人将名册拿来。”
须臾,宫人就将名册双手呈于亭前。内侍监取过名册给景暇过目。
状元一栏,秦珩的名字赫然在目。
景暇微惊,离宫的日子,他竟重考了会试。
依本朝例,官员辞任后,科考功名与授官资格终身保留。
秦珩当年主动辞任户部侍郎一职,如今若要再做官,报与吏部便是。
他再入春闱,分明是为了昭示天下,他秦珩从不是倚靠女帝上位的谄媚小人,而是堂堂正正的经世之才。
景暇冷哼一声。
她与秦珩的四年婚姻,如今竟成了他需要竭力澄清的耻辱了吗?
景暇继续阅览名册,探花常冀才乃文定伯之子,出自百年望族。这榜眼伏罗倒是个新鲜名字。
“这前三甲的文章,朕倒是有些好奇,拿来给朕瞧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