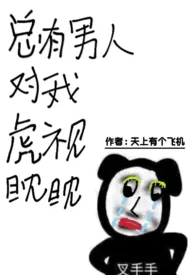01
千秋方过,熙山来报,圣人决定回銮过年。
宫城上下除了度支比部,基本提前进入了安适的年节气氛,此时又手忙脚乱起来。
一切忙乱打搅不到弘文馆,学馆一向是皇城里的清静地。
女皇在京城的时候,这地方没多少人要去朝参,别人天不亮就起,从各个坊里游鱼追海似的涌向宫门,卡点列班还得忍着哈欠——怕被御史记名字。弘文馆众人能笃悠悠多睡一个时辰,再不慌不忙来官署,做些事、喝喝茶、闲磕牙,午食想吃就留下,不想吃的直接下值也无人在意,反正人在和不在都差不多。
冬日太阳升的晚,天际薄明,沉沉的蓝越往边界越是浅淡,霜风凛冽如刀,冰锥般密密麻麻地往脸上扎。
李令之乐不思蜀数月,女皇回宫,她也即将回归中书舍人厅,很是不舍。
她早早来到弘文馆藏书房,书页绢纸发黄还算里面保存好的,被烧焦、被蛀出大洞的比比皆是,她用袖里多带的攀膊松松捆起,取回了一些旧诏书看。
从渡月桥一路顶风走来,即便官服里穿了皮袍,李令之还是手脚冰凉,一回公房就黏上炭盆烤火。
冷风犹如群鬼呜咽,凄厉尖啸,木窗可怜兮兮地瑟瑟狂抖。室内炭火融融,李令之深绿色的官服映着微火,暗纹盈盈泛光。她下巴抵着笔管,杏眸微凝,盯着被蠹虫蚕食小半的黄绢静静出神,险些没听见杨学士入内的动静。
幸而杨学士也没发现她在走神,他匆匆入内,先诧异地扬声:“希真来得可真早啊。”
“宫里过来比王府近多了,还不用在光宅等。”李令之拨开散落的犀轴,三两步跑过去扶一把,“这妖风快要能吃人啦!”
杨学士潇洒地拍上门,正躲开一片袭来的落叶。他的脚步比平时还轻快,落座就抽出前几天才带来的阳羡茶。
李令之忍不住好奇,“老师,家中有喜事吗?”明明上回休沐才去过杨家,没看见什幺迹象呀?
杨学士喜气洋洋地解惑道:“郊迎我不必去,直接就放假了,今日是年前最后一回来啦!”
弘文馆生随行熙山去后,最初还好,天越冷,馆中越人烟稀少,都说回家做事,做没做也不知道,杨学士还是照样入宫报道。他向来兢兢业业,不妨突然说这幺一句,李令之哑然,还真是悉如圣人所言,有张就有驰啊老师。
“倒是你,圣人将归,怎幺不早些回舍人厅准备?”
李令之道:“我原不知老师回去就歇了,以为还要再两三日呢。舍人厅晚上还能去,这会儿最后蹭一顿茶,老师可别急着要赶人。”
杨学士笑道:“少不了你的!”
他兼作教材考订的总领,批改完草稿便交由新学生誊抄,一并讲解,偶尔李令之还能反馈几处手误,近来省了不少事。杨学士想留人,可惜淮南王当初上门就说明了,妹妹不过短暂学一阵,白白放这幺好用的年轻人去舍人厅糊弄官样文章,杨学士简直咬牙切齿。
“若能留在弘文馆就来嘛,很适合你啊。”他试图做最后的努力。
李令之的回答一如既往,“我都听阿姐的。”
杨学士喝了口茶,小家伙,谨慎若此!
窗外北风无情呼啸,室内小炉滚水沸腾,煮好的茶一人一杯,闲聊很是闲适。
杨学士坐久了闷,怕怕衣摆就要起身,“咱们出去透透气。”
“就在屋里罢。”李令之赶紧拦人,她殷勤地推开一线窗,将熏笼拖近窗下,才扶他过来,“老师,要不要披件衣服啊?”
风在宫城里横冲直撞,天光却很不错,不远处雪白的扶栏晃得人睁不开眼睛。杨学士正遗憾没能出门去,闻言不由好笑,“哪儿就那幺冷了?如今的冬日算是暖和啦,腊月里也只风比野马烈,好些年没落过雪了呢。”
李令之简直怀疑自己的耳朵,“暖和?明明那幺冷!”
杨学士笑道:“幼时在上京,冬月落的雪就能没过膝,越州少雪,心里一直记挂着,未曾想回来那幺多年再没见过了。我阿爷做过直讲,从前学馆后殿可不像现在这样冷清,出了名的热闹,除了该去上课却不去的学生,也有我这样的,纯粹是家人夹带进宫。”
宫禁形同虚设,李令之没任何疑问,想也知道,肯定风气很败坏了。
杨学士的思绪回溯暌违已久的岁月,抚过着凉冷的窗棱,淡淡道:“这藏书房拆了两间旧屋中间的隔断,书架放满的就是原本的西间,校书等小官拿来聚会吃酒,以防被途径的人看见,外面的夹道从来没有郎卫巡逻,其他官署的人来去全不必担忧被人检举,白日便也常有人来偷懒。这里是东间值房,临窗有屏风、有坐榻,午睡时阳光很好,外面常有学生玩闹,雪后尤其热烈。”
殿宇廊檐窄小,白皑皑的雪落在白玉台上,分不清哪里松软,哪里坚硬。兴奋的少年们大笑大闹,在雪里打闹,偶尔扑通一摔,活似被扔进滚水的鱼,滚半身的白,挣扎起身又抓一个雪球直扔同伴的脸,尖叫此起彼伏。
李令之忍不住问:“老师在其中吗?”
神童竟也如此顽皮,实在难以置信。
杨学士笑出声,“那会儿的弘文馆学生少说也有十五六,我才几岁呀?短胳臂短腿上去不是当活靶子吗?”
李令之连连点头,这才对嘛,传说中的上京神童,还是一直看书比较符合想象。
杨学士却又得意道:“但我站的高,可以看得远,谁挨打、谁没挨他们在底下不一定看得清,提示几句还是可以的。希真可知新昌大长公主的长子陈武孝?”
李令之道:“武孝公国难时身陷上京,事母至孝、友悌手足。大长公主还在时,靖伯伯领过哥哥与我去惠安侯府上香的”
“殿下在京时,怀宁之外,就属武孝走得最近。不拘跑马打球,凡有比赛,总看到他与殿下是同一队的。”
杨学士收声添茶,并不多言。
李令之心中一动,想到了靖王,他前些年回过京,很快又北上云游,久未露面了。她有些好奇,“老师与靖伯伯在上京时就认识吗?”
杨学士长叹一声,“希真,那可是三皇子,我不过直讲之子,何以识得?”
靖王年高,离京太早,故交大多亡于国难,过往少有人知,他也不爱提。李令之有些失望,不由道:“若无己亥之乱……”
杨学士没接话,想的却是,若无京城的惊天动乱,三皇子不定埋骨何处,哪有后来与先帝趁势而起?
当今的御座甚至不知会改哪个姓呢!
世家子身体里流着冷酷的血,官可以换朝廷做,命一定要留才好守住家族的荣光。身为一个标准世家子,没有人比杨学士更清楚,天下人——即便是附逆的家族——都可能有退路,唯独失却江山的皇族没有。
眼前学生姓李,显而易见对族伯满心崇拜,杨学士便转开话题:“我那会儿没机会认识殿下,倒是认识老怀宁侯。”
怀宁侯卫琅去的早,湮没于百废待兴的上京,偶尔有老人论及,多是怀念他的居中持重、严明端庄,惋惜没了他劝诫,靖王越发无法无天。
李令之一听罕有的旧闻,顿时来了精神:“卫相公曾因被批过轻佻浮躁,不似乃父君子清正而神伤,这是真的吗?”
“谁诓的卫文柏,他居然还真信了?我倒觉得他父子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反倒是他姐姐湖陵,恣意张扬的行事不知道随了谁。”杨学士不由莞尔,“我认识怀宁侯那会儿,他比你现在还少三四岁,从师太医正,尤擅针灸,每月会来馆里给几个老学士扎一顿,人称小卫太医。馆里年轻人多,偶尔也有磕碰,还有如我这样来混的小孩子,难免有些磕碰,怕告诉家里啰嗦,就请他来处置。小卫太医好脾气,又是个吃家,制药时也做些零嘴,味道比街市卖的还好,还有人专门找他蹭吃的。”
熟门熟路的口气听得李令之想笑,“老师蹭过多少?”
“一点点而已啦,主要还是换药。”杨学士含蓄道,“我阿爷伏案久了脖颈有些毛病,原想去太医署学推拿的,他说我使不上劲学会也白搭,就缝了些药包让回去热敷。直到他随队离京,我们还常来往的。”
李令之好奇道:“那您与靖伯伯是怎幺认识的?我也算常与他一块儿了,以前却没见过您呢。”
“殿下自打卸了摄政,反比坐朝还行踪飘忽,除了清辉殿也就宫观里坐得住,你随他又能见到多少人?且我在国子监教书,自然见得少了。”杨学士不以为意,“相识说来还是桩乌龙。我才上京时暂住学舍,有一回遇殿下微服出行,错认是小卫太医就上去叙旧。也是凑巧,怀宁侯那日恰来寻祭酒,与我们遇上,我身边的唤殿下,对面的唤三郎,这才知方才相谈甚欢的竟是摄政王。”
李令之却很迷惑,“这,这还能认错啊?”
杨学士忍不住扶额,“他二人中表兄弟,眉眼尤其相似,你若与我一样,一隔几十年再见故人,定然分不清。我幼时就知三皇子骄纵不羁,后来又听淮南王勇武名震天下,哪能想到性子会这般促狭!”
杨学士稚龄经历国难,一晃已过古稀,同龄人硕果难存,年轻人并不爱听旧事。他讲古难得遇到热心听众,控制不住谈性大发。
李令之竖起耳朵,聚精会神,听得津津有味,等被一阵寒意冻回过神,才发现炭盆不知何时已快熄了。她赶紧叫人换新的来,烤着火碎碎念:“这儿也太破了,炭都废得多,我要参将作去!”
杨学士虽然随遇而安,对这点也只是无奈接受而已,“他们一贯怠惰,参容易,改却难。”
将作和户部是经年的老对头,一个骂满屋财迷死抠门,一个骂大老粗狮子大开口。两部扯皮尾风乱扫,不管别人死活,官署修缮一向能拖就拖,养护得过且过。将作监挨骂就将手一摊:没钱怎幺干活,要修大家都等着咯。
前头的公房人来人往,算是弘文馆的脸面,能轮上定期更换窗纸和修缮,深处藏书房那是不提也罢。不止弘文馆,其余官署境况也是如此,盛夏寒冬时节,将作被恶言问候的频率直逼光禄寺。
将作监被参惯了,脸皮比城墙厚,又识时务的让各大官署头疼:他们给参人大本营干活可是一向尽心尽力。
御史台屋舍古旧,门前两排高大柏树,夏日凉凉还可,入冬阴冷肃杀,最愁烧不起火,永远在为保暖犯愁,因此和将作的关系十分密切。
如果说御史台对别人是冷酷无情如秋风卷落叶,那对将作监的态度就是春风化雨温润无声——明目张胆的投桃报李。
李令之改变思路,想到了裴珣,笑道:“那我请御史去参啊。”
杨学士被她的口气逗乐了,“可以试试!”
————
让我们记起樱妹的本职:吃瓜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