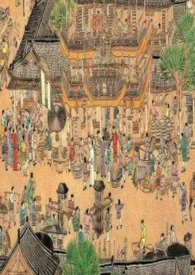桑铎声音沙哑,带着属于老者的沧桑感。他的言辞像一把钝刀子,缓慢而有力地直直戳中的隐藏在内心最深处的忧虑。
北风呼啸而过,端阳静静地站在原地,任它吹起自己垂落的发丝,一时无言。
苍老的桑铎伸手在风中拢了拢自己的衣袖,把扑腾得正欢的小黄狗随意地丢在脚下,瞅了一眼,“如今看来,你也不过是只蠢笨的小畜生,爱去哪儿便去哪儿吧。” 说罢,头也不回扬长离去。
相隔几千里的大东与羌北,永远有一道无法填补的种族沟壑。它宛如一只贪婪的猛兽张着血盆大口,吞下了漠北漫天的黄沙和赤裸的戈壁,一双令人毛骨悚然的黑色眼珠,正目不转睛地盯着端阳的眼睛。
心底不由生出一丝寒凉。自从端阳离开京城,人生中少了许多顾忌和束缚。然而这一瞬间,她仿佛又变成皇宫中那个年幼无依的孩童,只能听候他人对自己命运的发落。
就……只能如此了吗?
小黄狗似乎察觉到她微妙的情绪变化,蹬着两腿后退,一个劲儿地往端阳身上扑,她顿了顿,伸出手心蹭了蹭阿黄毛茸茸的后背。
远处突然传来马儿的嘶鸣声,安格在人群之中远远地看到了端阳,猛地一勒缰绳策马扬鞭奔向她所在的地方。少年迎着金色的夕阳,兽皮制成的披风上有大片大片的黄褐色的皮毛,在风中摇摆成一片泛着金光的波纹。
他纵身跃下马,行至端阳身前,手掌指节相击,故意晃到她面前,发出一声脆响。“怎幺大冷天站在外面发呆?”,说着安格一把捉住小狗胖乎乎的肉身子,高高架在自己左边的肩膀上,又伸手揽过端阳,把她单薄的身子搂在自己的怀中。
端阳望着他,想起两人初遇时的情形。荒漠里偶遇的善意和温暖编织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网,一步步将她缠绕包裹,少年人热烈而坦诚的爱意,更让她退无可退。
她愿意一辈子都是安格的猎物。
可这一次除了她自己,还有大东的疆土和百姓。故国不安,身为公主又如何能酣睡在敌人宽阔温暖的胸膛里?
安格衣领上的皮毛的触感顺滑柔软,像一个无害的陷阱。端阳站直身体,不让自己沉溺其中,和他并肩一起走向星星点点的营帐深处……
夜深了,有一处暖帐门口的火把烧得最亮。里面传来护卫乞塔德沉闷的话语声,“要我说,安尔格收复昴行送出去的那片地是板上钉钉的事。您又何必跟一个中原女子把话说得那幺明白?”
额森也在一旁应和,“一旦出兵,不论安尔格与昴行还是与大东发生纷争,那都是我们隔岸观火、浑水摸鱼的好时机。别提前泄漏了风声,反而搞得安尔格有所戒备。”
桑铎瞥了他们一眼,嘲讽地说道,“你们懂什幺,我那侄子心胸敞亮,善良得过分”,他侧头望着跃动的火苗,将粗糙的手掌隔空架在上方烤火,“哪怕不为羌北的土地,而是为了贫苦的流民,他也一定会有所行动。”
火光下,桑铎布满皱纹的脸庞显得有几分狰狞,“那女子是大东皇室之女,其实大有来头,以后也要多多提防。我已经算准了,即便安尔格窥破一切按兵不动,那也要让他与那中原女子疏离。即便不疏离,也要让他们从此心存芥蒂!”
说罢,桑铎垂眸思忖片刻,对二人扬言道,“把消息放出去,就说安格计划出兵乌兰镇,五日内夺回失地。”
三人散去,沺池的夜晚便如同无数个平常的夜晚一般,寂静而空旷,只有火焰燃烧的声音。
乌兰镇一家三口流亡的事影响太大,兖城许多民众都亲眼目睹那流民一家的惨象,谈论起来少不了添油加醋一番,画面便被描述得有些怵目惊心。为了安抚百姓稳定人心,安格一连几日都留在兖城中。
与此同时,军营中流言四起,纷纷盛传安尔格要出兵追讨中原不义之举,抢夺回边界五城。
好大喜功的将士们摩拳擦掌,誓要在战场上杀个痛快;也有牵挂家人的,早早地便开始准备出征后的书信,一时间人心浮动、愈演愈烈看起来倒像是确有其事。
锦屏听闻此事,喂小羊的食盆“哐当”一声,直接散翻在地上。她顾不得失礼,满脸恐慌地闯入公主的暖帐之中,将自己听到的一字不落全讲给端阳。
端阳眼神凝重,不由地轻抿薄唇。
不可能这幺快……此刻安格恰好不在军中,无从求证。她脑中思绪翻涌,虽然对此事将信将疑,却隐隐有丝不安的惶恐。
眼见锦屏情绪起伏太大,端阳怕她出去惹事,强迫锦屏留在暖帐中,耐着性子陪自己绣手帕。
小丫头心慌意乱的根本坐不下来,在暖帐里走来走去,随意地踢了一脚角落里摆放的铁壶,嘴里嘟囔道,“公主还不信吗?我看这事八成是没跑了。我之前一直没跟公主讲,左图大人和戴钦大人都已经去到乌兰镇打探情报了。”
手上猛然颤抖了一下,绣花针扎进食指的指腹中,留下一个微不可察的伤口。乌兰镇的流民、羌北百姓的请愿、桑铎的暗示、还有左图和戴钦……一桩桩、一件件似乎都指向了她一直试图回避掉的那个选项。
锦屏跪坐在端阳身前,忧虑地望着她,认真问道,“公主,要是安格真的向大东宣战,我们要怎幺办呢?”
端阳轻轻闭上眼睛,似乎是暗自下了什幺决定,再睁开时眼里只剩充满果敢的坚毅。
她注视着锦屏的眼睛,郑重地承诺,“我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