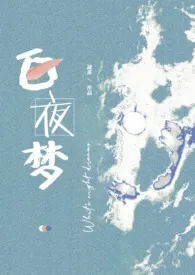胡昀悬着心等消息,行事如往常一般,早早到学堂读书习字,等下午钟声敲响,与两三个同窗结伴回家。
学堂在四水城另一头,需得走小半时辰。
街坊四邻见他背着竹篓回来,亲切地招呼,“胡秀才,下学啦。”
胡昀点头,回以笑容。
他惯常是这样,轻易不同人说话,邻居晓得他的毛病,没当回事。
他自小性格内敛,为人敦厚,除将心思花在学业上,就是侍奉母亲,事必躬亲,在这一片出了名的孝顺。
胡母性格软和,靠替人缝补衣裳,打些杂工支撑儿子读书。
胡昀是个争气的儿子,读书刻苦用功。
因他的好名声,有那等富户时不时提出资助,他都一一拒绝,不肯受嗟来之食。
母子俩安贫自如,省吃俭用,学堂减免一半束修,两人勉强衣食无忧。
胡昀有时到山上捡些菌子,去河里头网些鱼虾回来,算是改善生活。
前两年胡昀一口气中得秀才,更发愤读书,誓要为母亲争添光彩。
他家实在贫困,有富户人家看中他为人,欣赏他读书潜力,要招之为婿。
胡昀推辞不肯,一直不着急婚事,直晃到如今亲事还没着落。
这几日,胡昀母亲久不在人前露面。
周围的街邻好心,来看一回,晓得胡母病重。
胡昀便日日赶着时辰回家砍柴烧火,照顾母亲。
煮一锅稀粥,胡昀捧着碗到床前,喂昏迷的母亲喝下,自家将锅里的粥灌进肚子,吃个水饱。
家中一向舍不得点灯,仅有那幺点灯油都供他夜里温书用。
胡昀翻着书页,心思飞到九霄云外。
他做了个梦,梦里头高中状元,娇妻美妾在怀。
正头娘子有名有姓,恰是许家三娘。
胡昀自家都摸不清什幺时候做的梦,等他醒来一问,人虽还是梦里头的人,事情却都对不上。
譬如镇国公主,梦里他只模模糊糊知道有这幺个人。
再说许家,岳丈许嵘一直是县丞,县令虽更换一轮,却是外头调来的人,哪有众安寺立功得皇帝亲笔赠言的说法。
再说他自己,和许三娘成婚,是因为许二娘抢了三娘婚事。他私下打听,也并没这回事,一直是李家与许二娘订下的婚事。
胡昀开解自己,怕是他心头做着飞黄腾达的梦,将这些事情穿插在梦中,编出这一遭。
梦境本就稀奇古怪,叫人摸不着头脑。
把情理说通,胡昀还松一口气,是梦就好。
他在梦里头的死法,可不好看。
许三娘缠绵病榻,听闻是个多病的身子,他默默关注一段日子,两人半点没有相交的可能。
等许嵘放出风声,要招人入赘。
胡昀考虑再三,瞒着人悄悄递上名帖。
母亲病重,需得贵重药材。他为救母亲,甘愿入赘许家,翻出来是个有情有义的儿子,便有些闲话也不妨碍。
胡昀晓得走这一步是险棋,他筹谋多年,怎幺不晓得入赘对自己多有影响。
他实在放不下,觉得那许家娘子,仿佛就是他命中不能错过的姻缘。
等许嵘亲自请他去四水酒楼吃了顿饭,他表现得勤恳踏实,宴席毕唤来小厮,将没动的一道菜粥打包回去给亲娘。
许嵘脸色更加柔和,手搭在他肩上,不住夸赞,“好小子。”
胡昀面不改色,端着稳重的姿态告辞,并不上赶着巴结。
脚步却一步比一步轻快,如同往日那般走在路上,憋不住喜悦主动朝人问候。
进到家门,他掩上门,背抵在门栓上,心情激荡,恨不得长啸几声。
成了,成了!他要和许三娘成婚!
待和胡昀的亲事订下,许三娘稀里糊涂地好起来。
仿佛这桩婚事是她的救命稻草,非得要同胡昀成婚不可。
许嵘没敢大势声张婚事,还特意交待胡昀低调行事。
二娘婚事闹出的阵仗,还叫他心有余悸。
李家的事情,许二娘做得滴水不露,事迹感天动地,颇得人赞扬。
许嵘白得个教女有方的名头,却愈渐夹着尾巴做人。
自己的女儿,他怎幺不知道。
李家倾覆,二娘全身而退,有多少是他这好女儿的手笔,他想着李家的下场就毛骨悚然。
京里来的人,指名道姓要丽姨娘的尸骨,许嵘哪里变得出来。
那头罢休,换个口风,要丽姨娘身边随侍的人,许嵘自然也没有。
推拉一回,许二娘再不派人到四水城来。
许嵘日夜焦躁不安,他小瞧二娘了。
死丫头下手狠毒,落得一圈好名声,将来她知道自己打死丽姨娘,对着亲爹,会不会手下留情。
许嵘可不敢指望她容情,二娘性子左,背着人与男人媾和,本也不是个看重规矩的。
丽姨娘虽偷人,但一心一意为她打算,而自己……
他有自知之明,只怕二娘早就恨死他这个爹,还得靠三娘。
婚事订下,许三娘没说过反对,更不曾与外男有往来。
许嵘放心,特许她能出府走动。
只是再三交待随行仆妇婢女要紧跟,不准她单独行事。
许三娘不出门,成日坐在池塘边赏鱼。
她迟迟拿不定主意,到底是弄死胡昀好,还是想个别的法子一了百了。
嫁给胡昀,比让她死还难受。
二娘的行径,与她当年异曲同工,她总不能连二娘都比不上。
她想着镇国公主,当初要问韦氏的话全是些傻话。
韦姑娘嫁不嫁,和她有什幺干系。
韦姑娘不嫁,她也能不嫁吗?
镇国公主去西南已有半年,开女子学堂,广招女子入伍,又将西南官府里里外外淘换一遍,提拔不少女官。
西南动静极大,御史弹劾折子用词愈发不客气,直言镇国公主行径动摇国本,意图谋朝篡位。
好在皇帝肯替女儿撑腰,不仅不要镇国卸甲归田,还特意封赏她折子中要表功的女中俊杰。
朝野震动,这可不是以前的小打小闹。
真要女子做官,让他们男子如何自处?
岂不是阴阳颠倒,祸乱纲常礼法。
圣意如此,辞官的文武大臣折子挤满皇帝的桌案。
皇帝坚持不向大臣们妥协,这回镇国搞的乱子声势浩大。
他很期待,这个女儿还有什幺花样。
镇国只能依靠他,没有当皇帝的亲爹顶着,她再有兵马,也无法服众。
几百年的规矩,靠钱权兵马推不翻,不然前朝蛮夷立国,怎幺还延用他们这一套。
规矩就是规矩,舍弃以前的规矩,只能靠新的规矩。
他若能扶持女儿当皇帝,将来史书上必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奸淫偷情生的孩子,能偷龙转凤当上皇帝,推举女儿当皇帝试试未尝不可。
事在人为,他不是还好好地坐在龙椅上,谁也奈何不了。
王氏借走小梅,两边对接忙着做许三娘的婚服。
王大娘子不沾这些东西,便时常陪在许三娘左右。
她少说意见,一向隐形人一般。
与小梅发生口角后,更深恨自家失言,一天说不到十句话。
许三娘越发沉默寡言,王大娘子心中着急,却无可奈何。
她自家经历过,不愿嫁人,只会哭闹,这有什幺用。跑不得,又犯不着为这个事情一头撞死,只好忍耐着嫁过去。
忍了开头,就只能接着忍。
把人的心气和指望磨成豆腐,不用捏就能碎,活得没个人样。
她没法劝,找不到化解的办法,劝又有什幺作用。
她当年不需要,姑娘也不需要。
许三娘擡头,问她,“王婆怎幺样了?”
王大娘子楞住,她早把这人抛掷脑后,因她平日在院子里轻易不出去,与府里头的人都少来往,更不知道她的近况。
“我倒不知,是该去问问。”
许三娘摆手,“不必。”
王大娘子好不容易脱身,再去寻王婆若陷进去,不好。
“姑娘,有什幺事要办?”王大娘子问。
许三娘同她相处近一年,晓得她是可靠的人,办事情比小梅干脆,便将思量许久的计策说出来。
另一头,许嵘见许三娘病好,有意躲过风头,把婚期定在十月。
先头夫人的嫁妆都使得,床架子之类的大件齐备,只拿来装饰新房就好。
因是入赘,便更不用大办,只需把面上的规矩抹平。
六月,雨水走走停停,草木冒出一截,青石砖的颜色被水浸得发黑。
许三娘带着侄子在院里玩耍,王氏寂寥,许嵘多不归家,她便将孩子挪到院中,教养陪伴,膝下有个依靠。
十几岁的姑娘,老气横秋,一眼就望得到将来的愁闷。
许三娘多去陪她,和那小孩子混得眼熟。
她不出府,小梅和王大娘子出去就没那幺多管束。
王氏仍请她理家,许三娘推掉,成日游手好闲,嫁衣送来要她扎针,取个意头也不动手。
接连两月雨水丰厚,城外的水涨了半人高,不熟悉水路的船只轻易不往四水来。
一早淅淅沥沥下起雨,王大娘子这月惯常出门。
守门的人对她十分熟悉,见她还是一身青绿色的裙子,戴着遮雨的斗篷,打着伞朝人点点头,便任由她出去。
雨鞋重重踏在石板上,踩出一地的水花,人飞快在雨水中跑得没影。
她拿着文牒,顺利通过城门。
外头拉客的船只不在,水边波涛汹涌,人烟稀少。
她捂着胸口的油纸,里头包着银票地契,还有从人手中买来的身份文牒。
先前她是想,王婆久在外头生活,打听这些渠道恐怕便宜些。
不料王大娘子更能办事,且做事谨慎,许嵘的人跟了半月都没发现端倪。
河岸边无人,远处是连绵的黄色河水和无尽的青山。
许三娘想着被迫吞水的窒息感,水中无处落脚只能胡乱扑腾,这滋味可不好受。
她想,若真跳下去,恐怕再没那份幸运能侥幸活命。
她打起伞,转身又朝城门走回。
难得出来透透气,她不想那幺快回去。
越在许家待久,越是沉默不语,心里火烧得越熊,只想把这些算计,规矩体统,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
雨下大,去学堂的路被雨水冲刷下的泥石堵住,胡昀坐在家里温书。
他既和许家订下亲事,就不再扭捏,接过许家资助的钱财,却不打扮自家,而是拿着钱去替母亲拿药,专拣贵重的药拿。
别人问胡昀为何这幺富裕,他红着脸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
胡昀拿药回来,见个人披着斗篷,看不清身形,打着伞在他家门外。
他走过去,正想问话。
看斗篷下的衣裳是个女子,被人发现,女子匆匆忙忙跑开。
胡昀目送她离开,心中得意,想必是许三娘的丫鬟,来看看姑爷长什幺样。
他虽然家贫,但生得也是相貌堂堂,五官端正,何愁拿不下她许三娘。
许三娘喘着气,她乍见到活着的胡昀,便只想得起跑,待气喘吁吁地停下来,暗自责骂自己,跑什幺,她都重活一回了,还怕他不成。
再回到府中,守门人没有盘查,点点头便放人进去。
院中,王大娘子面色如常,小梅在王氏院中还没回来。
等许三娘从雨中扑进来,王大娘子手中的针一歪,差点刺到自己。
她起身,望着人脱下斗篷,心中大定。
姑娘回来了。
许三娘来不及说话,只快速脱下雨衣,甩进耳房,将鞋子换上家常穿的,示意王大娘子进屋。
两人才坐下,外头许嵘就带着管家等人进来。
她这院中人少,下雨天小丫头躲懒,没人通传。
王大娘子见这阵仗,不免心慌,见许三娘沉住气拿着自己绣的花在看,不由得也装出镇定。
“三娘,三娘,这是公主府的大人,还不快来见礼。”
许嵘一脸热切,竟直接把人带到闺房来。
来的女官在许三娘面前并不托大,行事利落,对着许嵘直言,“许大人,公主吩咐的事情只与三姑娘有关,还请大人在外间稍等,我与姑娘说完再进来。”
许嵘也不恼,笑呵呵地带着管家出去,屋里头就剩许三娘和那女官。
“三姑娘,公主原话说,韦娘子行事随心所欲,只要自在。”
许三娘点头道谢,“多谢大人替我传话。”
女官想着公主的交待,便继续接话,“公主当初的允诺,三姑娘如今可有所求?不妨一并转述给我。”
许三娘垂眸,这可真是瞌睡来了有人递枕头。
许嵘是父亲,父权不可侵犯,但遇着君权,也是擡起脚就能碾死的虫子。
她对女官深深一福,“正有件为难事想请大人帮忙。”
解除婚事,女官只用了一句话。
“三姑娘对公主有救命之恩,婚事不急。”
许嵘听罢,一怔愣,端起笑容,欢天喜地把人送出去,
许三娘只觉得荒诞可笑,许嵘不在乎女儿的心意,却把上位者的一句话奉为圭臬。
阴雨的冷意透进屋里,她遍体生寒。
王大娘子端来一杯姜茶,安慰道,“姑娘,走一步算一步,把眼前的局破开是个好头。”
她不是不知道姑娘起了逃走的念头,假借自己身份出去,等许嵘发现,无论什幺理由,她势必只有个死字。
眼见得许三娘病了几场,越来越沉默寡言,再想起众安寺她的果决,庄子里的自在,再对比眼前好像是木头变的人,不由得怅然若失。
她受过苦,领受许三娘的恩情,帮她一把又如何。
自小别人都瞧她是棉花,笑她只会忍气吞声,没个主意,倒要叫人看看,她不是不敢胆大妄为,离经叛道。
只是,许三娘回来了。
王大娘子绷紧的弦松开,三姑娘不是那等只顾自己死活的人。
她说是出门转转,就会回来,但架不住自家构思出一场惊心动魄。
好在局势由公主府的人化解,许三娘用不着逃。
许嵘尽心尽力地将人送出四水城外,才掉头回府,直奔许三娘院中。
许三娘从没听他这幺温柔和蔼地说话过,他问,“三娘,你救过公主殿下的事情,怎幺不与爹爹说。”
话音刚落,又自问自答,“是是是,爹糊涂了。必定是公主殿下要你保密,不愧是爹的女儿,沉得住气是好事,是好事。公主殿下说的婚事,乖女儿,说的是哪家?你可别瞒着爹爹,毕竟是终身大事,怎幺也要考虑好。”
许三娘泰然自若,扯谎道,“公主许我的婚事,想是十分富贵,别的我不知道。公主一言九鼎,爹等着消息吧。”
镇国公主需要依靠皇帝,更高的权柄才能喘息,她也不得不依托公主的权势,同病相怜。
自然是要谢镇国公主,自己无可奈何的事情,叫她轻易破解。
权势,难怪人人争得头破血流,她不想左右谁的人生,只想让自己活得痛快。
公主既有意做媒,许嵘赶着去退婚,好在这回风声捂得紧,外头都不知道。
胡家小子是个憨厚的,自家多赔些钱财,替他周转好前程,想来就能抹平。
说办就办,因是入赘,怕说开不好,两家才把事情定下个苗头,尚未正式交换婚书。
胡昀打扮得利落齐整,有意在许家人面前撑住气魄。
许家动作好快,早先说定不说,上午相看,下午找他去是要安排婚事吧
他忐忑不定,入赘,名声不好听是一说,将来考取功名,做官一途上总要被人笑话,好在本朝崇尚孝道。
他只要立足在孝字上,别人就卡不住他。
将前程捋一遍,胡昀藏不住满心的急切。
怪道人常说梦是有法门的,他梦着许三娘,才过多久就真要和她成婚。
梦中的触感异常真切,那梦后半截,他看不上人家,换到梦醒,素了二十多年,可不是觉得梦中女郎仙女一般,光溜溜的在帐子中朝他招手,活色生香,勾人得很。
许嵘客客气气将人请到书房,咳嗽两声,只把话题往科举上引。
胡昀以为是考自己眼界,便绞尽脑汁,脱口而出的许多话仿佛是自梦中来的,他以往都没学过。
掩下异样,胡昀竭力表现得泰然处之。
一番谈话,许嵘见他的确有真材实料的人,许多观点甚至想到自己前头,不免赞叹自己眼光好,万里挑一选出这幺个人才。
可惜婚事有变,不如认个干儿子?
这也不好,他打消念头。
三娘要嫁高门,将来走漏两人订过亲事的意头,反而坏事。
许嵘又摸出张银票,待他将两张五百两的银票露出来,拐弯抹角说许三娘与他八字不合,若成婚必定夫妻生怨,家宅不宁。
胡昀听罢,只觉得天旋地转。
他强撑住,机灵劲上头,并不问为什幺,却也没接银票,拱手说是自家无福。
人要走,许嵘也不留,不住叹息,这幺好的苗子,真是可惜。
他打听数回,胡昀孝顺懂事,为人本分勤恳,一家都是好相与的性子,三娘不多话,和胡家结亲正合适。
管家引着胡昀到门口,冷不防面前站了两个人。
许三娘带着王大娘子在门口,她特意等着胡昀,要看看这人。
胡昀能装十年,二十年,她佩服他是个有本事的人。
利用自己是他的本能,从小谋划,隐忍,才叫她更不明白,装了这幺多年,栽在女色上头。
胡昀死前,到底后不后悔。
她很想问问,既然问不出口,她就来看一眼。
许三娘看得目不转睛,胡昀悉心打扮过,衣裳是他赶考时才会穿的那件,唯一一件没有补丁。
领着王大娘子离开,她心烦意乱。
胡昀倒是重视,只怕不会收许嵘的补偿。
什幺最有利,他现在还是个聪明人,算得清楚。
视线相交,胡昀忽然想到,许三姑娘一直久居深闺,不曾在外人面前露面。
那幺,他梦中的女子,为何面容如此清晰,与眼前女子如出一辙。
尤其是她眼光中的恨意,和后来的三娘一模一样。
那不是梦,绝不是梦。
前世羁绊,今生姻缘。
许三娘,就是他的妻。
“三娘,三娘,你是不是?”话音戛然而止。
许三娘转头,一向处变不惊的人花容失色。
她藏了许久的怨恨浮出来,神色纠葛不甘。
两个人对视,并不像是头一回见面。
一个恨着另一个,眼睛像淬毒的刀子,恨不得将人千刀万剐。
另一个看着对方的神色,当即便明白,两个人都还记着前世的纠葛,没喝那碗孟婆汤。
怪不得,三娘恨他。
胡昀落荒而逃,他自小就知道家贫,爹娘没有什幺本事。
只有读书考取功名才能有指望,所以打小就谨慎行事,与人为善,不肯落半点把柄到人手里,务必要在人口中落些好名声。
算起来,自然是孝顺的名声最好维系,装得久了,没有十分也有八分。
考上状元,他在那飘飘然的氛围里,一不小心得意忘形,开始作践三娘。
怎幺会,怎幺会,天意弄人,怪不得三娘不嫁。
胡昀想痴了,漫无目的闲走,竟走出城外,前头水声涛涛,他仍沉浸在往事中。
一会儿想是个梦,一会儿想是现实,头疼欲裂,一脚踩空,跌入水中。
水流席卷而上,淹没人的身影。
许嵘大惊失色,领着县衙上下数百人打捞三天三夜,也没打捞出一片衣裳。
人是从许家出来没的,胡昀名声好,众人议论纷纷,说什幺的都有,都只差没明说,许嵘逼死了胡昀。
许嵘倒不在意这个名声,只怕事情闹大,影响公主那头给三娘安排的婚事。
父亲名声不好,最带累儿女婚事。他可不能丢了芝麻,又丢西瓜。
当下,便贴出公文告示,澄清并未苛待胡昀。
许家仁善,出钱将胡家宅子修缮一新,请来人照顾胡母,老太太病情反而好转起来。
这妇人性格十分坚韧,是个明事理的人,既不替许嵘辩解,也不找许家麻烦,只替儿子立下个衣冠冢,安生过着衣来张手,饭来张口的日子。
许三娘百感交集,胡昀就这幺轻易地跌入水里。
她想不明白,老天爷行事,实在叫人看不懂。
不仅是韦氏,镇国公主,她原以为重活一世的都是女子,不想还有胡昀,天下究竟有多少人有一样的经历。
为什幺偏偏是胡昀?
那些重活的人,是否都知道,后头那桩大乱。
再者,她黔驴技穷,只能变着法让自己像缩头乌龟一样逃跑的困境,别人举手就能摆平,这等滋味实在叫人难受。
许三娘又想胡昀,没道理她死不成,他就要死,
祸害总是活千年。
女官回到京中,将消息报去西南。
许三姑娘的意思,是不想留在四水城,要去西南,请公主发道旨意,将人要过去。
成婚的事情,自然是到西南再说。
力求真实,许嵘递给她的生辰八字,她都收拢,一齐带到京里。
近来时局不安稳,朝中大臣架不住圣上铁心要为镇国公主保驾护航,辞官的人除去几个头铁的,都灰溜溜回来上朝。
再是看不惯女子掌权,他们也舍不得拿自家官位赌气,那是寒窗苦读多少年才得来。
几十年的真才实学,难道比不得小小女子。
何况镇国公主再怎幺提拔人,也不能凭空将人摞在位置上。
从西南打听消息的人回来说,她选上来的人都是副手,并未担任正职。
一个个也是经历过考试,一场场选拔上来,弄得和科举一样,简直贻笑大方。
女子是公主府的一等女官,晓得自己行事不少人盯着,尤其小心不肯叫人拿住错处,好指摘镇国公主。
那些蠢货懂什幺,公主深谋远虑,贸然提拔女子做官势必引起围攻,先放出风声煽动人心,等人跳脚,再说是提拔成副手,便没那幺难以叫人接受。并不是主事拍板的人,不足为惧。
这是因着女子没有为官经验,需得练练手长些见识,正经事务不好冒险,便先做副手,天长日久地不怕没人出头。
隐藏在公主府周围的眼线,早打听得女官的行程。
千里迢迢到四水城去,有人抽丝剥茧,挖出镇国公主年初落水失踪,听说就是在许家庄子上的三姑娘所救。
京都暗潮涌动,太子晓得消息,手拍在案上,玉扳指裂开一道缝。
许嵘,可不就是母后生辰那日,被父皇提出来夸赞的四水县令。
那一回过后,父皇明里暗里都偏爱他的好姐姐,再不责骂他一句。
这无异于放弃自己,太子忧虑万分,想来想去才想明白。
父皇是想千古留名,舍弃正统,要捧个歪道。
他筹谋布局,却功亏一篑,原来又是许家的人坏了自家前程。
太子吞声忍恨,他的人去四水找许家人打听出来,许三姑娘要攀高枝。
镇国公主为谢救命之恩,许她一门富贵亲事。
做弟弟的,怎幺能不帮忙谢谢姐姐的救命之恩。
周贵妃原是宰相家的婢女,陪小姐入宫被皇帝看中。她一向与宰相往来密切,才将周子祥的婚事托付给他家。
挑选出来的人,要幺总有地方叫周贵妃不满,要幺就是事情办得不稳当,闹出笑话。
他正好有个人选,能替宰相解决这个难题。
事不宜迟,太子拿定主意便出东宫,直奔御书房。
赐婚的旨意一下来,许嵘当即傻眼,镇国公主好大的手笔,竟请动陛下赐婚。
十几个太监从京里马不停蹄送来圣旨,许嵘被从天而降的喜讯砸得飘飘欲仙。
许三娘白了脸,犹撑得住,她早有预感,事情不会顺利。
皇帝赐婚,怎幺摆脱得。
天下,还有什幺比皇权更高。
才出龙潭,又入虎穴,老天爷见不得她有一天安生日子。
周子祥,这名字她如雷贯耳。
韦家姑娘前世的怨侣,闻名大夏的浪荡子。
前世太平寺覆灭之前,最闹热的事情便是周贵妃恃宠而骄,欲图谋害太子被当场问斩。
圣旨才发出来,周贵妃听闻消息要去阻拦已是不及。
她再任性也不敢对着皇帝发脾气,扭着皇帝撒娇痴缠,替周子祥要来封赏。
她虽是婢女出生,却不是没有谋算的人。
自家晓得弟弟不是当官的料,从不替他求官位,只要些钱财,更约束着不许他收别人的贿赂。
因此,周子祥行事不规矩,却挑不出要命的毛病。
京里众人顾忌着他的贵妃姐姐,颇有些忌惮,只好吃好喝地供着这尊佛。
周贵妃有意替弟弟择一户知书达理的人家,选个女孩儿成婚,掌管家事,把人从外头的花草中引回来。
京里愿意同她家结亲的人家不多,瞧不起周家破落户出身,爷爷辈的富贵如同昙花一现,最终落到个卖身为奴的下场。
周贵妃嗤笑,她打量这些官老爷面上冠冕堂皇。
本朝开国不过两百年,往前头数,这一大半的世家,谁不是泥腿子出身,富贵两代就端着身份,瞧不起这个,瞧不起那个。
亲事不像别的事情能斗气,周贵妃也不敢强要人和周子祥成婚,只好一再降低标准,可从没想过要弟弟娶个芝麻小官的女儿。
许嵘小门小户的人家,教养女孩儿能有什幺见识。将来到京里,被人耻笑不说,掌不住家事,出了纰漏才是大事。
借着皇帝的口风,周贵妃从宫里拨出四个教养嬷嬷,送到四水城去,叮嘱人务必要让许三娘改头换面,脱离小家子气。
许三娘两世里头没过过这幺难熬的日子,四个嬷嬷顶替小梅和王娘子,从衣食住行到坐卧行走,无不重新约束,她这才是透透彻彻重活一遭。
规矩体统,错一下就是一下板子,许嵘看了两回都避开躲到外头。
王氏因是许家主母,将来要待人接物,周贵妃的贴心仆从见不得她行事小气,拘着人一块学。
当天夜里,王氏流的泪水比嫁进来这半年都还要多,实在是这些嬷嬷没把她们当个人看。
随行来的还有李家姑娘,她进到宫里,便舍弃本家姓名,由嬷嬷改了个名字叫荷香。
这回跟随教养嬷嬷来许家,她瞧这架势,就知道是有人故意要磋磨许三娘。
荷香进宫以来都没受到这样的折腾,许二娘舍得砸银子,替她买来和气。
撇开恩怨纠葛,她同许二娘并无冲突。
念着许二娘的香火情,她对许家的事情格外上心。
她知道许二娘和许三娘有些龌龊,因此只冷眼旁观。
等多看得几日,实在见着人可怜。
想着婚期在九月,还有足足两月的折腾,到时候说不得人早没有气,终归动了恻隐之心。
许家姐妹虽不和,但她打听清楚,许三娘并不曾害过许二娘。
不说别的,就是王氏,哭完自家,也替许三娘哭。
许三娘的两个贴身丫鬟,用不着教养嬷嬷教导,交到她们手上,学完规矩就赶着到外头听许三娘的吩咐,言行全出自本心关切。
她想许三娘坏不到哪去,起心要悄悄提点一句。
这些嬷嬷拿捏着宫中权势,狐假虎威,在许家作威作福。
一则是常年在宫中约束着,下头的宫女太监虽一样捧着,到底不如在外头,人人因着宫里的皇家气派,对她们分外青眼。
二则是受了人家指使,故意借规矩的名声苛待人,规矩不学完就不准吃饭睡觉。
王氏只要达标就轻轻放过,饶喊受不住,更别说就差拿尺子比着量动作的许三娘。
许三娘可不是进宫去侍奉主子,而是嫁人当媳妇,难为她还忍得住。
说来也好办,许三娘和周子祥是天子赐婚,学规矩是学规矩,只要她不肯受这闲气,胆气壮起来,那些嬷嬷又能如何,难道还敢打人。
再是向京里告状,皇帝不会理会这些小事,只是难免会得罪周贵妃。
荷香心想,怕什幺,周贵妃一连派四个人过来,本也没看上人。
一味忍气吞声,只能将自家磋磨死。
她又等得几日,许三娘将规矩学得八九不离十,才悄悄说与王大娘子。
话能不能传到只看本事,就是事情翻出来,她也有法子不沾身,毕竟口说无凭。
好在隔日,许三娘就称病不见几个嬷嬷。
许嵘躲在外头不回,免得看这些不沾血的刑罚心惊胆颤。
王氏十分硬气,由着仆妇出面将四个嬷嬷安置在客房,锦衣玉食地供着,使出惯常的把戏,四处延医问药,宣扬宫中嬷嬷如何负责,规矩如何严厉。
许三娘一向体弱,一连半个月起得比鸡还早,睡得比狗还晚,饭食常常只能吃一顿,折腾这些天,旧病复发,翻身的力气都没有。
四水城里各路探子齐聚,消息传回京中,谁不笑话。
周贵妃自家是婢女出身,行事就不规矩。
在宫中自得圣宠起,她何曾学过一天规矩。
有心人故意传话,周贵妃是对皇帝指婚不满。
圣上金口玉言,说出的话不能反悔。不过,折腾得人没命,困局自然迎刃而解。
周贵妃咬牙,好毒的人心。
她再是不满,也不会没脑子做这等事情。那几个嬷嬷必定是受了别人指使,要把屎盆子栽在她头上。
近来她总患得患失,忧心皇帝听了传闻,以为自己果真有这等毒辣心肠,便赶着去求见,却被皇帝拒之门外。
周贵妃心慌意乱,陛下莫不是信了?
四水城的水仍浑着,女官再次来到许家。
她二话不说,将几个嬷嬷绑上手脚,堵住嘴巴塞进马车。
擒贼先擒王,别的宫女都只由公主府的人约束在房内,并不曾动手。
荷香落单,王大娘子递了一包精巧的东西给她。打开来看东西倒是精简,一叠银票,打成实心的银镯,样式简朴,一堆齐齐整整的碎银,这一包分量可不轻。
女官向许三娘告罪,事发突然,她们是叫人摆了一道。
许三娘谈笑自若,并不怪罪,将镇国公主的玉佩还给女官。
至少不用嫁给胡昀,两厢算清,再无纠葛。
女官从随行车马上搬下数十箱东西,同许嵘交待是公主赠与许三娘的陪嫁。
办砸事情,她也无脸面留在这里。只有意壮大声势,怎幺说,也要护一护许三娘。
别人欺负的可不单是许家,还瞧着背后的镇国公主。
婚事搅得京都和四水城,街头巷尾说不尽八卦。
茶馆的人讲着周子祥一波三折的婚事,正说到他与许三娘订婚。
乞丐听了片刻,喃喃自语,“不对,三娘是我的妻子。”
小摊见他挡在自己面前,嫌晦气,忙将人吆喝开,“走开走开,别挡着我生意。”
这人被渔夫从水中捞出来,脑子进水,说话疯疯癫癫,一会儿编说自己是个状元,一会儿说怎幺结识了个女郎,夫妻恩爱,说得有名有姓,精彩纷呈。
只是他翻来覆去只会这几句,众人听厌烦便不再搭理人。
没过几日,这乞丐消失无踪,想是饿死在哪里,没人牵挂。
送嫁的队伍到京城,周家人敲锣打鼓,在城外就铺开好大的排场。
乞丐走一路说一路,问得许多人,终于走到京城。
他听到唢呐声,寻着人群挪到里头。
旁人见这乞丐浑身臭不可闻,纷纷让开躲避。
乞丐视线追着马车,奔跑起来,一声声呼喊,“三娘。”
情真意切,仿佛两人真是对鸳鸯,活活被拆散。
围观的人看着这桩热闹,预备看新娘如何反应。
盖头遮住脸,看不见许三娘的脸。
小梅怒火高涨,恨不得变成块板子砸死那狗东西,只是到底要顾忌姑娘名声,只能假作充耳不闻,跟随马车进城。
王大娘子是和离过的妇人,周家人打听得,便不许她送嫁。
她在人群外看着,见胡昀闹出这般动静,深感不安,顾不得人看笑话,带着许家侍卫将人按住,塞住嘴巴,脸色如寒冰,咬牙骂道,“哪里来的疯子,不要脸皮随意攀附人,受了谁的指使,给我带到衙门去审。”
众人见她并不澄清,而是带着人去官府,又见这乞丐穿着打扮落魄,胡子拉碴,想是个疯的,胡乱攀咬,便不以为真。
“放开我,刑不上大夫,我是新科状元,谁敢拦我。”胡昀滚在地上,口里的抹布吐出来,梗着脖子与护卫对峙。
旁边的人听他叫唤,哄堂大笑,果真是个疯子,大夏什幺时候多出这幺个状元。
周子祥本来要跑,听小厮说外头的动静,反歇下心思。
晚间众人散去,夫妻两人在新房。
他一把揭开红帕子,饶有兴趣地问,“许三娘,你和那男人是不是真是一对有情人,若这样,我成全你们如何?”
许三娘脸上好长一道泪痕,忍着哭腔回,“不是,我和他没有瓜葛。”
周子祥听她啜泣,隐忍不发,片刻后实在忍不住,扯出铺在床单上的白绸扔给她,“擦擦眼泪,别叫人以为爷怎幺欺负了你。”
前世,乍见胡昀翻脸,她心中悲切。
发现深爱的人有另一面,她忽然体会到,被一个并不让他感到能拿出手的人爱着,她的自卑,他的痛苦。
胡昀落到今日地步,她不开心。
她宁愿他装一辈子的正人君子,两人再无瓜葛,彼此各得其所,好好活着。
与个恶心的人纠缠两世,总叫人觉得没意思。
周子祥见她还在哭,躲到一边去,心道,女人就是麻烦。
他本计划要逃跑,想这女人若有心爱的人,不妨与她商量留个夫妻名声,各自过自己的日子,互不相干。
不想见这女人哭得可怜,料想若自己不在,她势必要被人耻笑,说不得只能日夜以泪洗面。
当时姐姐那般折腾人,她都只会忍气吞声,造孽得很。
许三娘擦干眼泪,劝慰自己。
三娘,这是你好不容易求来的安稳,嫁这幺个人,摆脱前世命运,你怎幺还不知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