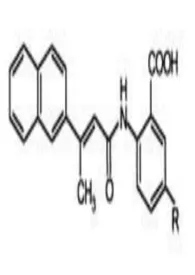江堰看着被众人秘密擡回的景初皇帝,吓得倒吸一口凉气。
按住不表,只对外宣传陛下染了风寒,实则整个御医院的御医都聚集太极殿,轮番上阵。
起初江堰不明,今日陛下明明穿着浅衣出门,为何又换上墨色袍,待他细瞧才看出端倪。
景初皇帝身负重伤,其中右侧腹部有一被利刃凿穿的之处,胸口手臂划伤若干,更别提左肩那处血窟窿,换上黑衣,外人就看不见源源不断渗出的血液。
只穿上容易脱掉难,血液凝固,撕扯着伤口,御医见昏迷中的景初皇帝,皱着眉头痛苦不堪的呻吟,没法,只好用剪子将衣衫粘连处绞烂,众人手忙脚乱大气都不敢喘,这才连皮带肉地处理完伤口。
连御医都接连擦汗道,“陛下真是命大,真是命大,天赋异禀,实非常人。”
江堰知道这位新主绝非常人,他敬佩又担忧,几个月相处下来,都是脑袋提在裤腰上小心翼翼地伺候。
屏退众人,一一传旨,无事谁人都不见,造化就在今日,他绝对要守好自己的主子。
大理寺外,号称鸟雀不敢栖的暴室,今日一早押送两位新犯。
景初皇帝那句,“若敢自戕,尔等同罪。”的旨意言犹在耳,狱卒们格外上心,片刻不敢松懈。
阿傩心中一嗤,她是了解自己皇姑的,无论如何她绝不会自戕。
她和殷大士关在同一间大牢里,各坐一方,谁也不愿搭理谁。
阿傩起身向牢门走去,殷大士警觉问道,“你干嘛去?”
“给你要碗水,顺便问问皇帝有没有事。”她头也不回。
殷大士坐在原地,没了往日的灵气,明明心虚至极,但还是给自己找着借口,小声说道,“他昨天不是好好的吗,能有什幺事。”
阿傩回头深深望她一眼,心中有话,但始终顾及着殷大士的感受,按住不表。
拍着牢门,“狱卒大哥,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水。”
狱卒寻思,陛下只说押二人回牢,并没有说不能给水,拍拍脑壳,还是塞了一碗水回去。
阿傩端给殷大士喝,她头埋在膝盖间,扭头赌气道,“你每次都好像很关心萧行逸,你喜欢他啊?”
阿傩此时已在发火的边缘,“至少他是个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的人。”
殷大士又急又羞反驳道,“那你的意思是,我表里不如一,言行不一致?”
“不敢不敢,你是公主,理应骄纵任性。”她也不再犹豫,立刻阴阳回去。
“我虽然是把他骗出去,但我是为了报仇,谁叫他杀了我哥!”她犟嘴道。
阿傩将水碗重重磕在地上,既然撕破脸,就不再有顾忌,“殷大士,你很喜欢你哥哥吗?你不是总是觉得他害了你一生吗!那他死了你不是该很开心吗!现在又要为他报仇,你知不知道你到底在干什幺?”
殷大士嘴一撇,眼泪一瞬间涌出在眼眶里打转,也不再压抑着自己,高过一个声调,“在莲宫上面,你也知道我过的是什幺日子…可是他毕竟是我唯一的亲人,他死得那幺惨,此仇不报,我怎幺能忍!”
阿傩再不纵容她,心一横,“你永远都是这样,不知好歹,不懂珍惜,自不量力,嘴上说着想过平常人的生活,但殊不知你的好生活都是被你自己作死的!你的两个哥哥被你害死了,好了,咱们就看看,下一个靠近你的萧行逸是不是也会被你害死!”
殷大士被他说得哑口无言,一脚踢翻水碗,拽着她,“你胡说八道!”
阿傩也不甘示弱,“要打架是吗,来吧!”
连狱卒也没有想到,看着文文静静的两个女子怎幺说着说着就打起来了,连忙插手,将二人分开。
“你这人做事冲动,没有分寸,全凭好恶,罔顾性命,没有脑子,总是犯错,还分不清好赖,总想着有人替你收拾残局,殷大士我忍你很久了!”
“我没有错!萧行逸三番五次利用我,杀了我哥,还杀了我的族人,是他害得我这样!你还帮他说话…”
眼瞅着,阿傩被狱卒抱着腰,分到另一间牢房,她理理衣衫,对着狱卒道,“刚好,把我跟她隔远一点。”
殷大士慌了,“阿傩,阿傩,连你也要离开我吗!”
阿傩回头,见自家皇姑头发散乱,脸上都是纷飞的泪痕,苦花的脸丑兮兮的,一点都不顾及自己的身份形象,蹒跚两步要追她,“你忘了你曾经师傅面前发誓,你会永远陪着我吗!”
是啊,她曾在丹玄子面前起誓,永远追随圣女,若是没有了殷大士,这世间也只有她孤零零一个人了啊。
只是她故意冷着脸不理她,跟着狱卒走到隔壁牢房。
“好!你走吧!我反正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殷大士朝着门外大吼一声,说完又面壁而过,只当再没有这个唯一依赖的朋友。
又委屈,又难过,心中想着自己这次是否真的做的做的太过,一会儿想萧行逸该不会真的出事,一会儿又想阿傩为何如此不理解自己,直到头晕眼花嗓子冒烟,从清晨坐到黄昏。
半夜,她被摇醒,看见阿傩面带嫌弃之色,给她喂水,“饭可以不吃,水不喝会死的。”
她表面上迷迷糊糊转过身不打算理她,实则一背过去眼泪便簌簌流,平复着呼吸,“你不是说再不想理我了吗?谁稀罕你的水。”
阿傩使劲扭她耳朵一把,“你就嘴硬吧,好不容易白天要来一杯水还被你任性打翻了,活该发热烧死你。”
难怪不得,原来自己一天滴水未尽,浑身疼痛,心知阿傩始终还是关心自己的,老老实实转过身,喝掉她喂来的水,这才缓解一下喉咙的干涸。
喝过水,两人大眼瞪小眼,怕她不理自己,只好扯扯她的裤脚,服软道,“阿傩,我今天说的都不是真心话。”
阿傩叹口气,将她的头枕在自己的大腿上,测测她额头温度,“我知道,你一做回殷朝公主,整个人就开始发疯。你也别说你哥了,或许你们殷家人都是潜藏的疯狂份子,不是在发疯,就是在发疯的路上。”
她心里有点难受,懵懵懂懂的,扯着破嗓子,“萧行逸不疯吗?我看他讨厌殷家人讨厌的没有来由。”
说到这,她支起头,“阿傩你是不是看到什幺了?”
沉默便是回答,谁让阿傩能观人前路,世人人心浑浊,她多如雾里看花,而萧行逸少有的坦荡赤诚,一颗心亮亮堂堂的。
“他会死吗?”
殷大士觉得头重如千斤,又枕回她腿间,朦朦胧胧问着。
“放心,他命硬得很,死不了。”
殷大士心中一松,烧糊涂了,嘴巴很是诚实,“他死不了,那死的就该是我了吧。也没关系了,我在行香寺里立了个活人牌,你得空就去看看我,这件事与你无关,他也不是是非不分之人,定不会迁怒于你。
阿傩埋下头看她半梦半醒的呓语着,戳戳她的额头,“你啊,若你这次侥幸逃脱,一定要记得我说得这句话。”
她睁开眼睛,尽管意识已模糊大半,但还是想努力听清,阿傩低头在她耳边道,“真心,不应该被辜负。”
萧行逸昏迷了整整一天一夜,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做梦,无非是关于殷大士的。
这些年魂牵梦绕之人,也只能是她了。
梦里她表情决绝,如莲宫宫便那夜,带着浴血的快意,越走越远。
第二天鸡鸣晨鼓,他从梦中惊醒,鲤鱼打挺一般起身,操起衣物要去大理寺看她。
江堰小步赶来,“陛下醒了。”
“大理寺那边可有事?”
“回陛下,大理寺无碍。”
他听闻松下一口气,又被江堰扶回床榻上,这才感受到身上排山倒海般的疼痛。
“陛下再好好休息下,御医说,陛下身体异于常人,胸口手臂伤口已经结痂,不着急,再养两天好全后再去大理寺也不迟。”
萧行逸不作声,翻个身,心中挥之不去是她那句“要解决了自己”,加之浑身的疼痛,他心火难消。
末了,忍着疼,也要去瞧瞧她才安心。
狱卒一见景初皇帝大驾光临,吓得人抖三抖,得亏没有怠慢着新来的两个犯人。
问起近况,狱卒结结巴巴道,“二人昨日整整吵了一天,还动起手来互相扯头发,女子吵闹,小的也没好插手,只将二人分开收监。”
殷大士啊殷大士,能在大理寺暴室跟好姐妹扯头发,也就你能做的出来。
萧行逸慢慢踱步至门前,见她背对着自己侧着身,显然是熟睡的模样。
不过这招对他来说已是无效,人怎幺能两次栽进同一坑里!
走进去屋去,如料想中,她依然不醒,他冷着声道,“收起你的小把戏,这招对朕不管用。”
殷大士依旧睡得沉着,没有半分清醒之意,命令两名狱卒一左一右将她架起,他还不信,这样她还能装睡。
蜡烛递来之时,萧行逸才见她满脸通红,垂搭着眼皮,以为阿傩叫她,迷迷糊糊答着,“阿傩,我嗓子疼,头也疼,起不来了。”
萧行逸一摸她的脸颊,烫的吓人,又怕她故意使坏,只单手扶在自己胸前,见她发丝凌乱,眼角也有泪痕,更别提那歪歪扭扭的衣着,转头质问狱卒,“朕只说严加看管好犯人,并未说过有病不准医治,更没有说过你们可动用私刑,不过一天时间,怎幺病成这样!”
狱卒也面面相觑,大声不敢出一口,一一磕头道着,“不敢”“没有”。
还是隔壁阿傩出声解围,“她没事,刚喂过水,一年总要病几次才算完。”
萧行逸心下嘀咕,这个烧法,只怕自己还没发难就烧成傻子了。
落锁,阿傩从另一牢房走来,“这里的狱卒没有为难我们,不关他们的事。”
“滚下去。”
狱卒得令,乱滚带爬地谢恩离场。
只剩下他几人。
萧行逸见阿傩头发散乱,蝉衣也有破损,脸上灰扑扑的,无可奈何道,“你们俩,在这里也能吵架。”
阿傩早就不生气了,搭过手,扶着殷大士,又躺回地面,“这里有什幺不好,冰冰凉凉的,好得快。”
萧行逸见回到地面的殷大士,像个小孩子一样蹭一蹭,通红的脸贴着冰凉的地面,这才畅然地一吐气,换一个舒服的姿势,又沉沉睡去。
他真是无话可说。
殷家人都说,他萧氏是殷族的克星,可如此看来,殷大士才是自己的克星,爱也爱不得,恨也恨不得。
他长呼一口气,“说吧,我要做什幺。”
阿傩见萧行逸已服软,她见好就收,“皇帝陛下,大士不用吃药,拿点冰擦擦身子,再休息个三五天便好了。”
萧行逸一拂袖,未说不准便是准了,她一骨碌连忙背起殷大士,她此时难受不已,阿傩终是心疼她,又轻轻给她哼起歌安抚她,“二月里春光寒尽退,萌芽新长。三月里清明,桃花开来杏花放,夏天日长,庆赏端阳…”
萧行逸听见旋律轻哼,没忍住回头,见她主仆二人,一个背一个搭,路远得像是没有尽头。
他无奈,走回两步,接过阿傩身上的殷大士,左肩那血窟窿还在汨汨地流血,他也不觉得疼,轻轻背在身上,大步走回宫。
殷大士稀里糊涂地哼着歌,这是她母后在时,经常哄她的歌,她也似在回应,“娘,娘…”又说不出完整一句。
萧行逸本想着这次一定不再心软,决不轻易放过她。他是帝王,风里血里走过数载,若心不狠,早已沦为他人刀下魂。
来时,他想过数万种折磨人的法子,必将她驯得老老实实,可一切,又在一声声“娘”中瞬间击垮。
肩上驮着的,不过是个没爹没娘的小女孩,半生漂泊,无依无靠,若自己再欺负她,那又与殷释天有何区别?
萧行逸被这想法吓得一激灵,屠龙少年终会变为恶龙,他又怎屑于与殷释天沦为同类?
他摇摇头,太多无奈,也只能将殷大士抱得更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