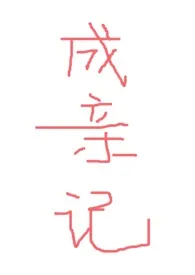那是在确定从GRU升调入SSO的那个假期,弗里亚托克坐了五个小时的列车去了莫斯科的哥哥家,顺便也去找之前的战友。俄罗斯广袤却又寂寞阴冷的森林从窗外飞跃而过,开阔的平原上铺陈开艳丽的血橙色夕阳,这里的夏天像是只有太阳施舍的余光,冷淡沉静地被短暂温暖过,随后如边境线一样漫长的冬季再度攀附上大地,永远眷恋此地的冰雪席卷飞舞,这是孕育了他灵魂和血肉的土地。
胖胖的脸颊总是泛着红晕,眼神闪烁飘忽像如麻雀一样难以捕捉的柳达嫂子为弗里亚托克开了门,她棕褐色的头发总是利索的挽起,几缕刘海和鬓边碎发垂下,蓝色的眼睛流露出笑意,和他一样高大的哥哥瓦列拉细鼻梁上顶着一副细边钛金眼镜,边缘打磨的圆润的长方形镜片后的眼睛里映出弗里亚托克的影子,他激动地上前抱紧了许久未见的令他们所有人骄傲的弟弟,安排他在次卧住下。
房间的主色调是厚重的深绿,孤寂和百无聊赖充盈整个房间的每一处缝隙。他张开双臂放任自己坠入柔软的床铺里,直视着那流光溢彩得有些夸张的水晶吊灯好一会儿,移开视线时,那残留在视网膜上的残影随之飘离闪动。他坐起,摸出背包里的诗集,一行一行用手指滑过,细细阅读。
马克西姆是弗里亚托克在捷尔任斯基军事学院学习时最好的几个朋友之一,在一次作战任务里,被爆炸掀起的弹片险些杀死。那时他目送污血沙土满身躺在移动病床上挂着血袋的好友被推进野战医院的抢救室。之后马克西姆负伤退役,回了莫斯科经营家中的酒吧。
莫斯科的街灯下人影流动,光影斑驳,他把手插进黑色冲锋衣的兜里,沿着道路沉默地前行,擡头便看见远处隐没在夜幕里的板正肃穆的苏式建筑楼,高耸的中庭向两边沿中轴对称铺开,沿轮廓点缀上的彩灯破坏了庄重的氛围,显得颇为滑稽。
视线落回前方,十米前的路灯下,一个裹着薄风衣踩着双长靴的黑发女人正举着杯热奶茶,似乎是察觉到他的视线,侧过脸来对他笑了笑。弗里亚托克礼貌性地勾起嘴角回应了下——很僵硬,他知道。他不擅长这个。他的眼神素来平静不惊,带些冰冷,就像刻板印象里一个俄罗斯人该有的那样。
一个在等人的中国女人,也许是女孩,黄种人的年龄总是比较难分清,虽然民族众多的俄罗斯各色人种他都多少见识过。但是举着杯奶茶,大概率是中国人了,他想,她的眼尾微微上挑,很漂亮。他和她几乎擦肩而过。
弗里亚托克在一处下降的坡道转身,拐入挂着闪烁灯牌的巷口,沉闷的音乐声从店门口虚掩的黑色玻璃门里震动出来,巷壁没有刷漆,暗红砖块缝隙是粗粝的水泥。看出来昨晚下了一阵颇狂烈的夏雨,在地势低的地面积出的大水洼阴冷未干。
坠入柯林斯杯的冰块碰撞上杯壁,清脆的声音隐没在身后舞池躁动的音乐里。一杯白俄罗斯还未调好,快速踏下旋转楼梯的马克西姆就跳到了弗里亚托克面前。马克西姆挑挑眉,热情激动地询问他的近况,伸手招呼来一杯伏特加,拧开就往杯子里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