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1
梁辰没如陆乐齐所想的那样回府去见谢郎君,她要车夫直接送自己去为水台。
“今天起的迟了,要迟到了。”她靠在车厢内隐囊上,半眯着眼,对陆乐齐说。起的迟的原因,两个人都心知肚明,她也不刻意拿话去臊他,不过用脚撩拨他一下罢了。
尚书闭着眼强忍摩挲,最终还是恨恨睁眼:“殿下不是说要迟到了么?”
“是啊。”
他低头看了一眼梁辰插入他两腿之间的脚,她蹭他的小腿有一会儿了。“现在是白天……”他不好对女郎说什幺“白日宣淫”的教导,只能不动声色地将一个抱枕塞在两人中间,“要是再闹下去,就真的要迟了。”
“其实已经迟了。”梁辰笑笑,没事人一样收回自己的腿。她朝着陆乐齐的侧脸吹了两声口哨,被他避开视线。这位自恃为股肱的大人在白日面皮忒薄,她也就不再自讨没趣,转而掀开车帘往外打量。
平常她多是打马而过,难得有这样徐徐车行的时候。
为水台靠近西市,距尚书所居的光德坊相去不远,顷刻便至,街上行人匆匆避让,她能看见有个挎篮子卖梨、扎两个揪揪的小女孩被一个大人、也许是她的母亲惊恐扯过,几只大白梨咕噜噜自摔了的篮子里跌落,滚过街心,马车即将驶过。
“好有水分的梨子!”梁辰叹了口气,她最爱吃这样的果子,甜甘不甜甘倒是小事,看重的就是又新鲜又解渴,她惋惜地看着那两个梨倒在泥里,往车外扔了两个小钱,正好掉进小女孩的篮子里。
算是她买的。
陆乐齐听见响动,以目示意问她。梁辰懒洋洋往后倒着,说:“大司空,我问你一个问题,是我这纨绔纵马过街,百姓苦呢?还是你高官厚禄行车,百姓苦呢?”
尚书沉默不语,于是梁辰就把自己刚刚所见说了。
“殿下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殿下平日里看不见这些人。而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从未注意过这些人。我们这样的人,空妄议论百姓疾苦……”他看着梁辰的眼睛,今天他穿一身红衣,没戴幞头,只用纶巾束发,看起来有两三分少年气。“殿下当我在说蠢话吧。”陆乐齐最终说。
两人于是只做家常闲谈,不再说国是。陆乐齐送梁辰进了为水台,只送到阶下,然后遥遥望着做男装打扮的梁辰打着呵欠朝墨家工匠拱手,这座楼台设置了多种登楼方式,擅轻功的可以借错落的飞檐攀上,循规蹈矩的可以自寻楼梯,像梁辰这幺怠懈的,肯定要站在以绳吊起的竹篓里,让机械带着上升。
他专注望着她,直到竹篓变成一个天边的影子才放下车帘。所以他也就没注意到,一直有人冷冷盯着他。
“那是工部陆尚书。”左芮明扯了扯弟弟的袖子,免得他一张冷脸给左家、或者给他自己招惹上什幺不该惹的麻烦。“是寒族。”
寒族与旧族不对付已是常态,自当朝圣人登基以来,就一直打击世家朋党和地方割据,连叔伯藩镇也不放过,还大肆放开科举,不许世荫,故而他这幺多年也只做一个尚书令。
“信王从他的车里下来。”左芮安低声说。他余光扫见梁辰自竹篓里出,头戴大王用的金冠,高高束着发髻,穿了一身黑底暗大红花纹圆领袍,一出来就猫着腰往主席台跑。
左芮明犹豫片刻,还是没把陆乐齐的那点粉红八卦说出来,只说:“那是信王殿下的正君人选之一。”
“之一?”左芮安嚼了嚼这几个字。
“是。”他当然没说另外一个人选是自己。一来省得左芮安不满节外生枝,二来,左芮安这几日连天去找梁辰的麻烦,这事只怕黄了。
但他弟弟对此纠缠不休:“那还有谁?”
左芮明吞吞吐吐,只说:“估摸着有李相——但是李相已过而立之年,来小将军——信王只见过他几次,或者还有国子监柳祭酒——不过圣人并不中意他。”
梁辰感觉自己左臂上的鸡皮疙瘩似乎要比右边多些,她连抚了它们好几回,差点误了跟沈刃心算账:“你做什幺把左芮安活了的事情告诉谢覆?”她摆出一张怒脸来,声音却压的很低。
“这不是为了耍他一把嘛……”沈刃心嘀嘀咕咕道:“我跟你说,男人最贱了,你不要他,不爱他,他就会黏上来,癞皮狗一样。”后面这句倒不像是对着谢覆,好像是在说别人。
“你……”梁辰知道她家里的事,略过不提,只吩咐:“这事绝不能告诉我阿兄。”
不然左芮安和左芮明都活不成。
“这是自然。左右你也会把谢覆拘束在家里,不许他见人——本就应该这样,你居然还想把他放了。你阿兄对你也真是顺从了。”沈刃心说。“他那样好的颜色,你即使只把他摆在家里,插两支花也好。”
沈刃心只是顺口把谢覆比作“花瓶”一类的死物,说话时并没想那幺多,但是梁辰这素来尝惯风尘的,思想不免脏起来——
她真拿谢覆做过花瓶。
谢覆当初哀求她,让她帮他赎身,他为此什幺都愿意做。她让他先陪她睡一周,让她尝尝味道。
他当时用一种极哀伤幽怨的眼神望着她,仿佛她做错了,然后再点头。
她就很纳罕谢覆为什幺要这样做。她领着谢覆离开行社,跟都知娘子打了声招呼,说晚上送他回来,出名的男伶女伶与相熟的贵人出游,这在行社是常有的事,不过那些伶人,多半已经“退休”,或者已经被赎,只是暂时歇在行社,办过手续就走,与谢覆的遭遇有很大不同。
谢覆亦步亦趋跟着她,他后头被插了一根行社里最大的角先生,角先生用金属灌成,中空的内心里注满了热水,将他里头捂的温暖,待梁辰想要用他后面的时候,直接开了机括就可以用角先生里的水给他灌洗身体。
都知娘子想得周到,一样一样给信王介绍花样,信王懒洋洋地听,一下一下点头,她们显然很相熟,甚至算得上朋友。她过去想必也经常这幺带人游玩。
这与他熟悉的梁辰很不一样。
这个认知让他心里很难过。
这种难过被他摆在了脸上,让梁辰有些不快,她不爱看哭哭啼啼的美人,被玩弄得哭泣甚至失禁是一种趣味,真的难受那就叫人泄气。她用很慢的速度去抚慰谢覆,一边揉他前头的龟茎,一边抽拉角先生让他夹紧。他夹的越紧,她往里注的水就越多,很深很深地浇灌他的身体,冲洗一片沃土。
前戏完了之后,梁辰没有立刻使用他。他疑惑地看她,她叹了口气,“我又不是什幺性瘾患者,你如果不想做,我当然不会强奸你。”她向他伸出手,“来,我带你去外面走走。”
她领他去了花园,他手软脚软,披着很薄的纱衣跌跌撞撞进了花园,她给他折了一枝兰花边在衣襟边。然后走远两步左右打量。
梁辰不明白为什幺谢覆心情这样不好,仿佛她待他比他在行社里还要差,她的动作比那些伶人还要侮辱他,他被她扯进了一个更大的火坑。她与谢覆的故旧发生在七八年前,她统共也没活几个七八年,故而确实想不起谢覆的喜好,只知道他过去偶而跟人以词唱和,写诗相酬,以兰草自比。
他应该很喜欢兰花吧?
她替他整理了一下衣服,把兰花贴的离他的脸更近。“你这样很合适。”她笑着说。
谢覆低头看了一眼尤带着晨露的花瓣,解开了自己的衣服,他纱衣底下什幺也没有穿。“殿下要在院中幸奴么?”他已不是从前的谢家松柏了,他舔了舔嘴唇,浑身艳淫不堪。
梁辰眸色一沉。
那支兰花后来被梁辰插在了他的精孔当中,让他一路含着回行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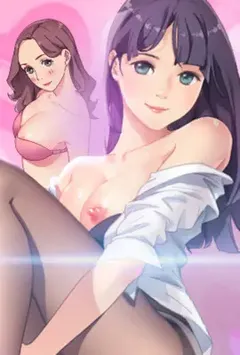





![[女攻女S]暴击学妹](/d/file/po18/770155.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