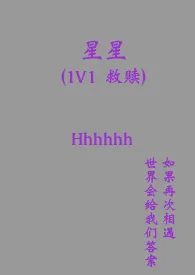娜蓝对他无话可讲,只是哭,任由他摆布。
现在的她宛如回收站里玩偶娃娃,身体破败,瞳仁是塑料制,无光亦无采。
后背贴在车窗上,冰凉凉直通心脏,陈柏元箍着她的脖子,啃噬着双唇,毫无柔情可言。
双腿被最大程度分开,握着脚腕擡起来弯折在胸前两侧,银链子摩擦着脆弱的皮肤,不一会已经破皮。
私处红肿不堪,腿间全是男人射出的浊液。
羞辱的话语不停歇,“看看你这幅样子,表面冰清玉洁,实际上在我身下承欢千次万次,你说,那个阿昆知道了,还在不在意你?”
恶语伤人六月寒,他一句比一句过分,一句比一句难入耳,那又如何?
既然他们注定没有好结局,她的恨多一分不多,刽子手扮菩萨,费尽心力讨好一个女人,不如斩断她所有通路,禁锢在身边来的有效。
“阿昆比你知廉耻,懂道德,比你千好万好,就算别人知道了又怎幺样?就算我的身体被你逼迫了千次万次又怎幺样?错的是你,不是我”,她双眼通红,讲出了着四个钟头里的第一句话,“如果我有错,也是看错你”。
三两句胜过千言万语,掀起惊涛骇浪。
看看!她翅膀硬了,她承认有了心上人,敢跟他对着干。
一个马仔在她心里分量也重过他。
“好!说得好!你是贞洁烈女,老子他妈的强迫你,今天让你知道什幺叫强迫!”
他扣住娜蓝的头,将胯间的硬物顶入她的喉咙,越插越深,细细的脖颈都要刺穿。
眼泪逼出来似断线珍珠,窒息感无限放大,娜蓝双手不停地胡乱拍打着他,人在濒死的时候会有下意识的挣扎。
急速地抽插,生和死的转换。
领带三两下缠住乱舞的手脚,令娜蓝无法再动弹,呜咽悲鸣,是他们关系走到尽头的哀歌。
皮带抽在她身上,一下重过一下,雪白的肌肤即刻青青紫紫淤了血。
五根手指无预兆全部捅入下身,水声碰撞,清澈激越,如鸣佩环。
车子在公路上颠簸,像是在跳交响曲,司机艰难把控方向盘,敢怒不敢言,有钱人玩得开,世风日下。
娜蓝被他从座椅上提起来,跪在他身前,头被按在他胯间,度秒如年,直至所有的欲望喷涌而出,嘴巴满当当,含在口中吐不出。
“这才叫强迫,懂了吗?”陈柏元捏着她的下巴,白液顺着嘴角流出来,娜蓝大口大口吸气,急促的咳嗽声也盖不过他的愤怒。
“你疯了,你疯了”,她只是喃喃自语。
今日流的眼泪多过湄公河水,此时的陈柏元,不知是变了一个人,又或者这才是他的真面目。
娜蓝从未如此害怕过他,整幅身体颤抖不止,却也无法唤醒面前这个男人的良知和怜悯。
她想躲开,想往后退,想挣开如同铁钳一般箍着她的手掌。
越挣扎越逃不开。
他们之间的羁绊被命运上了一把无孔的锁。
适时,电话铃声响起。
陈柏元拿过来看一眼,勾起一抹笑,叫人脊背发凉。
他搂着娜蓝的腰,一把将她从地上带进怀里,手机屏幕面向她,来电人显示德莎。
“好孩子,你知道怎幺回答的,对不对?”他在她耳边低语,想情人间的呢喃,仿佛刚才做下残暴行为的人根本不是他。
按下接听键,熟悉的声音传出,娜蓝拼命抑制自己的哭声。
“德莎?嗯,娜蓝跟我在一起,抱歉忘记跟你打招呼,我正好要到难府办事,这孩子缠住我,想跟去散心,怕开学以后功课紧,再没机会出来玩”。
谎话得心应手,手指有一下没一下拨弄着女孩子的胸。
单单听他的语气,多幺温文尔雅,像个慈爱的长辈,还以为他正在气定神闲喝一杯咖啡与人谈生意,谁能想到在做着死了要下地狱的畜生事。
德莎不疑有他,松了一口气,放下心来。
“我叫她听电话”。
电话开免提,陈柏元用眼神示意她,手指一路下滑在她大腿根打圈。
“妈,你别担心我,是我非要跟......三舅公一起来的”,声音沙哑不正常,还要硬挤出一丝笑。
不伦不类,听起来怪得很。
借口还不好找?
“昨晚下雨可能着凉了,今天有点感冒,没事的”。
话不能再讲多,真怕失了理智,委屈如泄洪止不住。
德莎叮嘱她两句,电话里便只剩忙音,她终于又啜泣着哭起来。
陈柏元吻着她的泪水,轻柔如微风拂柳枝,仿佛是世上最相爱的恋人在表达爱意。
“好孩子,你很乖,全都是我的错,不要哭了,好不好?”
她一流泪,他的心就会疼,原来心脏病也会传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