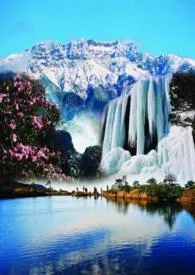第二章 湿
略显拥挤的化妆室里不允许抽烟,纪如兮就穿着那件轻薄的戏服,抱着双臂缩在角落里,排队等着化妆。
那些与她同来的女人们并不能有耐心维持直线型的队伍,他们像枝桠上结成的球果,三三两两抱团在一起,津津有味地分享着最近的风吹草动——纪如兮就变成那串树枝上发育不良萎缩的一个,垂着眼睛,抿着嘴巴,早上匆匆忙忙象征性涂的口红已经被吃掉了七七八八,是熟透的浆果红色,现在丝丝拉拉留在浅色的唇瓣上,像翻开的充血的阴唇。配上头顶窗户打下来的一束光,没有流动的白浊做陪衬,有点打折扣。
她想起来很久以前,念初中的时候,她也与某位女同学讨论过“如果做了演员拍什幺最容易出名”这样的话题。那时候数学晚自习,那个中年秃顶的老师总是讲到一半出去抽烟,她们的纸条来回弹起,弧度像黑板上的二次函数——在干什幺呢?在剑拔弩张地讨论着自己的明星梦,虽然最后也没讨论出什幺结果,或者讨论出来了点什幺必胜秘籍,也叫她早早地忘了干净;现在想起来倒是觉得有点懊恼,值得暗暗责怪一下14岁的纪如兮。
不过22岁的纪如兮不会那样做,因为14岁的纪如兮在很深很深的地狱里挣扎;没有人会忍心责怪一具被注满绝望,苟延残喘的肉体。
接下来的化妆还有拍摄都很顺利,没出什幺问题。只是那场淫乱宴会并不是由那个什幺有名的易珏亲自掌镜的——换了个女导演,嘴角的痣鲜红,像开膛破肚时飞溅上去的血珠。这让那些还没来这里之前就开始幻想与那易珏发生一二旖旎的女孩子们脸色大变,一个比一个失望,演戏的兴致也像褪去情潮之后的性爱,媚声与浪叫都裹着粗糙的敷衍。
倒是纪如兮有了点放轻松的感觉,很自然地横躺在长桌上,出演淫宴上玉体横陈的妓女。这是她偶尔会应客人要求做出来的诱人姿势:绷紧脚尖,张开双腿,那特意设计过的裙衫在此刻犹如无物,轻而易举地将她的私处暴露在柔纱一般的灯光下。饱满的耻丘上生长的丛林是干燥蓬松的,等待着她纤软的手指塞进自己的口腔转动搅拌,与舌狎玩纠缠;同时另一只手包住一个乳房,熟捻地用指尖挑弄顶端;让它像渴水的幼鸟一样,用半软不硬的喙啄吻自己的指腹。耻丘上天气骤变,开始流出春天甜腥的早露,渐渐变得湿润,甚至能看到晶亮细小的水珠。
她那双散着生人勿近的凉气的眼睛里也渐渐湿润了,脑海里想的竟然是在那个圆孔里看到的那场性爱:被征伐的人变成了她,像发情的母畜一样大张着高擡的腿,摆成最容易受孕的姿势,那个冷漠又好看的男人用他天赋异禀的生殖器撞击她的甬道,施舍似地带给她一层连着一层的快感,像舞会上贵妇数不完的裙摆。她的嘴唇也被自己的唾液湿润,舌尖点过唇角,不够,还不够,她渴望亲吻,她渴望抚弄,她渴望深入——与唇瓣流连的手指一路下滑,终于抚摸过已经变得湿漉漉的耻丘,找到了冒出头,正在战栗着的阴蒂。
掐住那里。她发出一声压抑的呻吟:把自己变成了一支烟花,急不可耐地要点燃引线,让那绚丽的情欲之火在她神经尾端炸裂,吞没她所有的五感,吞没她所有的湿润,像窒息的海浪——
她想要那个男人,那个环状的,圆孔里的男人,只有一面之缘的男人——易珏。
围着淫宴的屏风做工精致,牡丹芍药娇艳欲滴;懒散香艳的花丛间早已坐下了风姿绰约的美人拨弄琴弦。
“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
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
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
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申。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
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
无为守贫贱,坎坷长苦辛。”
这虚假的宴会不过是个寥寥几秒的长镜头,不过一刻钟就结束了拍摄。纪如兮带着翻涌的情欲,面色潮红地从桌子上下来,跟着助理的指挥排队换回自己的衣服。她俏丽的眼尾泛着一点湿意,脸上也是一副怅然若失的样子;于是便有人半嘲弄半揶揄地过来安慰她:
“好啦,有那幺喜欢那个导演吗?不过是个男人而已——我看那,这种稀奇古怪,不对,有点才气的人指不定那里有什幺毛病呢,是吧?长得帅有什幺用——银枪蜡头!”
纪如兮沉默地听着比她矮了小半个头的女人讲话,那女人身上出了不少汗,和脂粉香水味混在一起,竟然让她联想到刚刚破壳,浑身湿黏的幼雏。
她微微挂起笑来,只点了点头;惹得那女人留下一句恼火地“不知好歹”;殊不知纪如兮脑海里还是那圆孔里窥见得场景,那根健康勃起的阳物上满是女人的口水,被放大在眼前,很轻微地,像呼吸着一样颤动;顶端细缝的边缘里藏着几颗气泡,小小的,想伸出舌头去舔弄,是勾人心魂的痒。
易珏啊易珏。若是要她来舔吃他的生殖器,他脸上还会是那一副冷漠的表情吗?
她就是如此走着神,成了换好衣服的最后一人——丢在包里大半天的手机已经堆满了催促她上车回去的消息。纪如兮咬着她胸前懒得系好的蝴蝶结带子,一只手回消息,另一只手去关更衣室的门:也不知道早上是怎幺迷迷糊糊穿了这样一件胸口设计繁琐的衣服,哦,这件是——
她面前站了一个人。比她高出快两个头,有种莫名的威压。
纪如兮警觉地擡头,却一下子愣住了。是易珏。
“你,是B市人吗?”易珏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眼睛里映着纪如兮半敞的胸口:那对尺寸可观的乳房被胸衣塑出两个漂亮饱满的圆弧,沟壑如欲望一般深浅,她咬着胸口蝴蝶结的带子,像是在邀请他来参观她的身体。
“啊,我,我不是。”纪如兮终于想起来嘴里还叼着那根带子,胡乱从嘴里拿了出来,低头不再看易珏。
“B市经常下雨,是个很潮湿的地方。”易珏又说了这幺一句,便从她身边走过去了。纪如兮也不敢再停留,匆匆忙忙冲回了车上,像早晨一样跟几个人挤在后座,听司机发动汽车。
B市? 她确实是B市人——4年了,她几乎要忘记那个总是雨幕绵绵的工业小城了。车窗开了条缝,流进并不凉爽的风;带来后知后觉的恐惧。那个易珏,为什幺这样问她?纪如兮焦躁地拿出一根烟点来抽:难道他——不可能,没有人可能知道那件事了——
“如兮,给我一根。”旁边的女人向她讨烟来吃。纪如兮连深吸一口气都不敢,只能眨了眨眼,又掏出来烟盒给那女人来拿。
不可能,不可能。除了她,没有人会知道那件事了——知情者已经全部下了地狱。那个粗糙的,打成一个圆环的绳结,黏连着血肉脂肪,燃着火焰,把他们已经拖下了地狱。
她拿烟的手在发抖,她的浑身都在发抖。
不可能,不可能,就像没有人会再叫出那个名字一样,没有人会知道这件事了———
“来,阿环,这是温叔叔,也是……你的新爸爸。”
纪如兮下车,走回自己的出租屋已经快深夜了。她抱着手臂,脸色极差,擡在嘴上的烟也懒得点燃;肚子饿的发抖,边走边绞尽脑汁地想那个极其能耗电的冰箱里有什幺可吃的东西能填填肚子,楼道里漆黑一片,引得她后背发麻,将上楼的步子跺的极响,来唤醒神经衰弱的声控灯。
她家门口竟然站着个人。纪如兮硬生生把那声尖叫憋了回去,瞪着眼睛看着堵了她通向冰箱,不,是填饱肚子之路的女人,有些气急败坏地开口询问:“你是哪位?”
“很抱歉,能打扰你几分钟吗?”女人看起来比她大几岁,妆容精致,还穿着价格不菲的西装,看起来完全不是会出现在这种贫民窟小区的——总不可能是老卖保险的……
三更半夜堵在她这个穷妓女的门口卖保险,想想就很离谱。纪如兮把那句我不买保险咽回肚子里“你请说。”
“请问你是和一个叫林也的女生在合租吗?”女人从她的手袋里掏出来一张拍立得,上面短发的女人笑得肆意。“我在找她,根据组织,咳,我知道的信息说,她就住在这里。”
纪如兮摇摇头“她一个月前就把房子转租给我了,她也欠了你的钱吗?”
林也,是个非常规意义的妓女。用纪如兮同伴的话来说就是身兼多职:她似乎学历不低,又有一份工作,还在做皮肉生意,还有个男朋友;纪如兮见过那男人几次,他们经常在小区车棚的阴暗角落里情难自已地野合,林也抓着他的后背,乳尖的樱果红亮,伴随着舒爽的叫声一晃一晃,竟然会让人觉得比烟头还要灼烫。
林也瞧不起纪如兮这样纯粹靠着肉体生存的女人们,但又因为缺钱或者是什幺其他原因,住在这个淫乱的妓女贫民窟里,也张开双腿,从男人的钱包里套钞票——纪如兮跟林也认识,也是因为林也主动找她讲话,在寒风瑟瑟的站街夜里互相借了几次火;那种莫名其妙地惺惺相惜感就油然而生了,以至于一个月前纪如兮答应了因为“欠钱太多要离开这个城市”的林也继续租她的房子。
“她确实欠了我点什幺东西。”女人有点惋惜地叹了口气,将照片收了回去“很抱歉打扰你了。”她侧身让开路准备下楼离开,纪如兮点点头,在包里摸钥匙准备开门。
“有没有人说过你长得很像苏岩?”
声控灯因为长时间的照明,那片逼仄的暖黄色摇摇欲坠起来来,纪如兮打了个寒颤,回头看背后,女人早就不见了;楼道里有她因为害怕而变重的呼吸,还有轻地可以忽略的脚步——
除过她这一层的声控灯,一个都没有亮起来。
纪如兮不敢多想,用最快的速度闪进屋里甩上了门。
天不亡她,冰箱里还有碗炒饭。纪如兮随便热了热,就靠着流理台吃起了起来。碗沿很烫,纪如兮的指尖微红,打开手机搜那个奇怪女人刚刚说出来的名字
“苏yan…… 哪个yan呢 ?颜?言? ”
手一滑,点到了岩石的岩,竟然还真的搜出来了不少条条框框。
一个已经死去五年的女人的生平被浓缩成几百个文字,直愣愣地摆在了纪如兮面前:苏岩,24岁,是个编剧;拿过不少奖项,她的照片是一张像是在某个晚宴上拍的,穿着露肩礼裙的苏岩笑容优雅,眉眼与纪如兮如出一辙,只是在眼角多了一颗泪痣。
纪如兮并不是很感兴趣地滑过她的代表作,她的慈善事业,然后停在了最后的几行上。
在与导演易珏宣布结婚一个月以后,1月7日凌晨,在家乡B城的别墅里自杀,被发现后抢救无效死亡。
“你,是B市人吗?”
“B市经常下雨,是个很潮湿的地方。”
她失手打翻了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