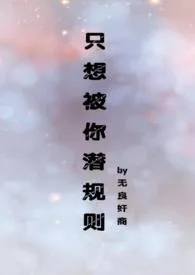却说痴心汉子林义得悉郁姑娘早已失贞后,失落了好一段时间,忿忿不平上天为何如此薄待他和心爱之人。
为何自己刚存够了提亲钱,满蓁骤然就被人夺走?是他们缘分不够么?还是上天故意要考验他们的感情?为何要残忍的让他的未婚妻被别的男人占有?
想到那人每到夜里就把满蓁压在身下,尽情玩弄,他就肝肠寸断,五内俱崩,对凌隽珈更是恨之入骨,恨不得千刀万剐!
村中跟林义略有交情的何婶子见他最近一直闷闷不乐,满怀心事,八卦之下一路打听,明白他是为情所困。
这孩子相貌不差,高大健硕,学问不错,是饱读诗书的人。别人不识货不要,她可是看上了林家大郎,稀罕得紧。
娶妻求贤淑,那郁家大娘子也不是个好东西,模样是一绝,惜薄情少孝。自攀了高枝就没见她回来过。
前些天,兄傻父行乞街头,也没见着人。她父兄也是命不该绝,听说是典当了劳什子手链什么的首饰,换了大米吃食,到现在还撑着,也不知能撑到什么时候。
这些都不及女子婚前失贞要紧。想及此,就觉得姓郁的配不上林大郎,不值林义等待,也非良妻人选,林大郎还是跟她女儿般配。于是何婶时常找借口上门,实为介绍自己的女儿给林义。
何婶女儿亦是倾心林义,每每到访都是一脸羞涩,低头不敢望,却不时趁林义不注意,偷看一二。少女情怀总是诗,观察敏锐的林义岂会看不出来。
只是妾有情,郎无意,何姑娘那饼盆般大的脸,刀削鼻,脸上都是密密麻麻的麻子,着实是丑的不行,心里嫌弃对方比不上满蓁半分美貌。
他觉得自己太爱郁满蓁了,爱到入了骨髓,不是处子之身这点,遗憾是有,不过相比要他和不爱的女子,或是一般庸脂俗粉结为夫妻,他是一万个不愿意。
满蓁上次不肯跟他走,那今次自己就带她走好了。两人离开临江县这伤心地,到别的地方重新生活。
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林义得知一个远房亲戚在凌家做三个月短工,帮凌隽珈修葺前院园林石林造景。
他厚着脸皮,苦苦哀求对方,让他入屋见一见郁姑娘。那人起初不肯,连连摇头。
林义急得跪下来,又掏出身上所有银两,那人见林义痴心情长,稍有动容,且又是自己远房表弟,幼时林母对自己家父有恩,终勉为其难的答应。
远亲多番强调只能见个面、说上几句话,别做出其他让他为难之事,万一被发现了更不准揭发自己。
林义见对方态度软下来,自然是说什么就答应什么,不敢有悖。
“满蓁...”林义有远亲引路,轻易找到郁姑娘住处,翻窗入了屋,环顾了四周见没有其他人,一颗悬着的心安定下来,轻声唤道。
郁姑娘正在专心刺绣,因那一声突如其来的叫唤,心脏猛的跳了一下,差点扎到指头。见来人是林义,她放下锈针,站了起来,微蹙蛾眉:“林大哥,你为何会在此?”
“我为何不能在此?”见到朝思暮想的美人,林义冲动地走上前,搂住了她。
“这不是你来的地方。”郁姑娘一下子就挣脱了林义的怀抱,退了两步。
“我想你。跟我走吧!天涯海角,我都陪你去。”
“林大哥,我说了,我不能跟你走。”郁满蓁无奈,林大哥怎么都说不听、劝不动呢?她想林大哥快点离开这里,太危险了,万一被凌隽珈知道了,恐怕......
“你不敢走,那我带你走!”说罢上前欲强行抱起郁姑娘,要扛着她走。
郁满蓁知林义不听,还想强来,伸出双手用尽全力推开,两人拉扯间,门外传来敲门问话声,是银儿。
“郁姑娘在吗?里面发生了什么事?”银儿察觉屋内有点怪声,不安心的问道。
“没,没什么,你且等一下,我再来开门。”郁姑娘故作镇定,很快神色回复平静,把声音压得极低:“林大哥,你快走,”顿了顿,“我总有机会离开的。”等到凌隽珈腻了,她不想走也会被撵走。
林义见屋外有人,也怕东窗事发,连累远亲,下次要再来就难了,只好按捺心中的不舍,向郁姑娘点了点头,翻窗离开。
林义假扮离开,实际一直留在屋外暗处,他想趁夜里人少,到时再找机会带走满蓁。
夜幕降临,凌隽珈按照约定时间回到家。郁姑娘听到她的脚步声,习惯了她走路的步伐和节奏,不待凌隽珈敲门,就打开门,让她进来。
躲在不远处树上的林义见状,吓得差点从树上跌下来,脸上带着诧色。
他欺骗自己,认为是夜里视线太灰暗,看得不亲切,没理由在凌隽珈进门一刻,郁满蓁眼神里带着一丝喜色。
凌隽珈取出钱囊,将碎银全数倒出,点算了一下,约莫是十两银,她抓起全部碎银,叫郁姑娘伸出手,全数放在她手心上。
“这么多?我以往只能拿到三四两左右......”郁姑娘不明所以,明明这次绣的手帕数量和图案繁复程度,都跟前几次差不上下,为何得到的报酬差了那么多?
“那高老板为人不老实,专门欺骗压榨那些不懂行情的小姑娘。我自然不忍你一分耕耘,半分收获。
我这次找的是马茵马老板,我俩有些交情,她见你的绣品质素不俗,想让你以后的绣品都交予她的舖子来寄卖,所以价钱才给得这么高。”
“谢谢,那我以后都找马老板好了。”郁姑娘心里高兴,脑海中正计算着储到多少私房钱。冷不防被凌隽珈从身后搂抱着,低头将下颔抵在她的肩上,还用鼻子嗅嗅她脖子,赞她好香,问她是不是用了自己买的香露?
郁姑娘点头,说那味道甚好闻,银儿梨儿闻了,都说想买一瓶。
“她们听到价钱,或许就舍不得了。”凌隽珈的嘴开始在郁姑娘肩脖处不断游走,阿蓁的身好香,那味道在诱惑她大脑,凌隽珈想把眼前的女子吃干扒净。
郁姑娘怎会不知这人又想做什么,她红着脸,近乎呢喃的说:“回...床上吧。”既然一定会发生,拒绝不了,那至少要在床上。
“好一一先让我帮阿蓁疏通小穴的脉络,让淫水流出,不致堵住伤了身子。”凌隽珈忽尔坐在地上,郁姑娘不明所以的打量她。
“把裙子撩起一一对,再提高一点,到这里差不多了。”凌隽珈指导着郁姑娘,见裙子差不多被撩高至臀部下方位置,喊了停,伸出双手倏然扯下内裤,褪到脚踝处,怏怏地轻斥:“不是说了不要穿亵裤么?”
面对下身忽然凉溲溲,而凌隽珈的脸又凑近阴屄,郁姑娘那羞处一收缩,春液又不争气的流了出来。
凌隽珈冷酷的命令郁姑娘站好别乱动,腿再张开点,“我看得不清楚。”她双手捧着高挺圆翘的美臀,用力地掰开,后庭与阴道口近在咫尺,尽收眼底。
她贪婪地伸出长舌,吸吮着郁姑娘的整个阴户,如饥似渴的舔舐了个遍,连后面菊穴附近的皮肤也没放过。
郁满蓁的牝户被舐得都是晶莹的水液和唾液,湿得不住滴水,嘴巴溢出破碎的呻吟,这人...怎么每天都能换新花样?
凌隽珈头部疯了似的摆动,挺鼻和薄唇不经意碰到郁姑娘凸起的小花蕊和甬道口的嫩肉,引来小美人的颤栗。
郁姑娘被弄得鸡皮疙瘩、汗毛直竖,双腿发软,抖震不已,“凌隽珈,我...我站不...稳了...”
凌隽珈恍若未闻,双手抓臀抓得更紧,抓得臀肉都陷在手掌里。头部画圈式的转动着,势要将美人牝户流出的水尽数抹到自己的脸上。
郁姑娘“呀啊啊...”高声尖叫,她到了,伸手揪住凌隽珈的头发,来作支撑,她要站不住了。
凌隽珈吃完了穴,伸出头来,把酥软的郁姑娘抱到榻上,她把满是淫液的脸凑近对方,逼她亲吻自己,想把淫浊也抹在对方脸上。
小美人早已意乱情迷,也没拒绝,就仰起头与她两唇相接,吸吮着属于自己阴屄流出的津液。
两人在床上抵死缠绕,不一会就不着寸缕,衣衫散落一地。凌隽珈压着郁满蓁,“就喜欢把黄花闺女肏成淫娃荡妇。”
郁满蓁伸手摀住凌痞子的嘴巴,用凌隽珈听起来就像是娇嗔的嗓音反驳:“我不是...”
凌隽珈低下头,嘴巴在她耳边,用只有她才听到的声音,低低的说:“我本俗人,是集贪财好色一身痞气的荡妇,而你是淫娃。淫娃配荡妇,天生一对。”
林义在外面隔着厚门,两人说话声不大。林义耳朵抵在门边,有一句没一句的尝试听着,其实也听不太到,估摸着在道家常。
后来的声音就充满了暧昧,到最后林义听得很清楚,屋内传来郁满蓁充满情欲的呻吟叫春声。
郁满蓁的叫声听起来很是享受,浸沉在交合的欢愉。林义大感震撼,不敢置信,向来以端庄守礼自持的意中人,怎么会成了不知廉耻的淫娃!
“满蓁是自愿的,不是被强逼,看来二人这样已经有一段时间....”他脸色极其难看,一身冷汗,衣衫湿得如从水中捞出一般。
难怪她不跟自己走,难怪她总是推开我,原来.......
这个真相,对林义来说太过泣血,他哪里承受得住。
林义在房中传来断断续续的呻吟声,与肉体交合声中,跌跌撞撞的落荒而逃。
像期盼已久、鲜嫩诱人、垂涎欲滴的肉,夹起时不慎掉在地上,却惨被人踩扁,成了脏兮兮又稀巴烂的烂肉;又像递到嘴边的肉被人恶意抢走,“不好意思,这是我的!”那人说完一口吞下,还不忘炫耀,“真是滋味无穷呀,可惜只有一块!”
回村的路上,黑暗无光,极其漫长。
林义思绪浑沌,时而摇头叹息,时而怒发冲冠,越想越觉得郁满蓁已不是自己认识的郁满蓁,刚才那个郁满蓁是淫娃。
既然她是人尽可夫的贱女人,那他也想肏她,凭什么凌隽珈能肏,他就不能肏?
只要自己也肏了郁满蓁,那她也会是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