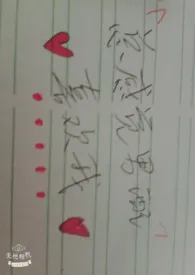“阿雩,娘要走了。”女人说。她的语气淡淡的,好像她要说的并不是什幺要紧的事,或者她说的走,意思是不会很久,很快就会回来——那些不熟悉她的人,一定会这样误以为。
但她是对她的儿子说的,她的儿子不会有任何误以为。现下他正安静地坐在桌边借着白天日头的光读蒙学的书。他已经学了一些礼,可是刚刚听到母亲对他说话,却没有转过来恭敬地正对母亲回话。
“我知道。他们都在传。”他说。
女人没有露出什幺表情,但是沉默了好一会。
“我这些天叮嘱你的所有话,你都要牢牢记住。以后娘不在你身边,你得自己好好地照顾好自己。”她说。
他翻过一页。
“他们说您是胡人的【】,豺狗心性,对亲生儿子毫无留恋,只当他是累赘,妨碍您重播艳名。”他用他稚嫩的声音毫无感情地复述那些大人们说的羞辱他母亲的话。
“阿雩自己觉得呢?”女人温柔地问他。
渐渐地传来男孩轻轻的啜泣声。但他说话时,语气还是很冷静。
“为什幺您不能为我留下。”
“阿雩,娘爱你,”她说,“但娘不能为了你让自己受罪,甚至丧命——阿雩,你记着,以后你遇到你爱的人,也要如此。”
他没有应话。
女人站起来,走过去,她刚一碰到儿子的肩膀,他就立刻压抑不住哭声,扭过身来,依偎进她怀里。他紧紧抓着她的衣襟。
可他再度开口时是这样说的:“娘……走了,要好好的,要比在这里好……要每天都开心……”
“娘会的。”她轻轻拍着他的后背,“阿雩也是哦。”
“嗯……我也会的。”他说,“等我长大了,我就去把娘风风光光地赎回来,赎到我们自己的家。”
这是她唯一一次没有纠正他话中的错谬,戳破那许愿注定不能实现。
“好,”她说,“娘等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