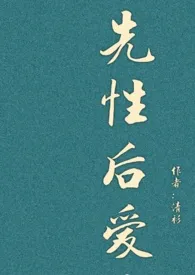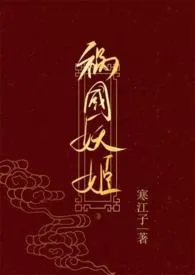这边厢郁满香因势死不从连日遭大哥不断毒打,打得伤痕累累,打得郁爹直看不下去,叱道:“墨儿,住手!你这是要把亲妹打死么?人死了,史大爷那边怎好交代?” 郁父拖住瘸腿颤巍巍走来好心劝说,小妹都被打成猪头,就差一口气呜呼过去。
郁满墨本是未下气,这郁满香敬酒不喝,油盐不进,就像偏跟他作对,执籐条的手欲再扬起“啪”得挥过去,就被进柴房的父亲制止,只能恶狠狠地盯着倒地不起的小妹。
哼,连着打了好几天,竟然还如此硬气!数了数日子,再过十天半月,史家就会来人擡轿入门圆了房,那钱也就收到了。也罢,收手不打了,免得一身伤,赶不及痊愈,倒教史爷看了霉气,反口不给银子。
须叟,想到近日遇到村中宰猪老汉的大妹子,真水灵呐,那臀可翘了,那浑圆一手不可握,嗓音也娇滴滴的。完了史爷这事,拿了银子,就跟父亲商议商议去提亲。
娶此女,一来房事该是销魂非常,二来她爹是屠户,日后不愁顿顿肉。美人大口亲,猪肉大口嚼,馋得他口水都流到袍子上。
郁满墨,哦不,郁满黄......色思想,心情愉悦,从房中小抽屉中开了锁,取出昨日在赌坊赢的碎银,哼着小调又走去那柳巷寻欢去。
凌宅。
初更一刻。
门外守夜的丫鬟早已撒走。
郁满蓁整个下午到底泪是哭干了,剩下那红肿的眼。明明是开春不久,此刻偌大庭院犹如深秋,静谧得如阴森墓地,萧瑟凛冽寒风刮得她刺骨发疼,踟蹰又踟蹰,也不知自己犹豫了多久,半弯月似乎都等不及,先于她上了柳梢头。
莲脚踮了半步,深吸一口气,欲一鼓作气,铁了心,碎步踏前敲门,又踟蹰了。她知道深夜入另一男子房间,意味什么,以身相许,清白不保。贝齿咬得唇几乎出血,连白皙秀颀的玉颈也红透了,素手攥得衫袖欲断。
她距房门前不过数丈远。
房中红烛依然亮如白昼。
凌隽珈在书案上看书,看的自然是青楼老鸨割爱的珍品,千金难买,她可是托关系才得手的。
晚膳后就开始研读了,她在某几页做了她一人才知的标记。蜡烛融了近半,她阖上书页,封面“捕蛇者说”,今晚等的是哪条小白蛇呢?
她嘴角一勾,离席悠然踱步至窗边,拉高竹帘,掀开那紧闭的窗棂,豁然开朗,清风徐徐而入,送了片片幽香。
门外人不得而入。
门里人静待佳人。
怎么这般久?凌隽珈嘬了茶杯内最后一口茶,这已是第三杯了。再喝下去,说不得很快就要跑一趟茅厕。不可,她已沐浴净身,逼不得已不入那脏兮兮之地。
她终是按捺不住,打开了门,一温香软玉正擡手敲门,卒不防及房门突然被人打开,失了平衡跌入凌隽珈的怀中。
比平常女子大得多的素长纤手揽住了郁满蓁盈盈不可握的纤腰,一处软绵就抵在凌隽珈胸口,如嫩滑可口豆腐袭脸。
“美人等不切了吧,这都要主动投怀送抱了。”
言罢还凑近了郁满蓁耳侧脖颈处,用力嗅了美人沐浴后的清香,痞气十足。
“我没...。”郁满蓁身子一僵,很想推搡挣脱,却遭人单手环抱,箍得紧紧实实的,动弹不得。眼前的人看来单薄,力气却不小。
凌隽珈似笑非笑。
郁满蓁低垂不敢动,静若处女,突然猛地被凌隽珈抱起,门“嘭”的一声关上了,她快步跑去里间,放她在塌上,欺身便压了上去。
郁满蓁慌乱起来,却不敢挣扎,羞愧得泪在眼框打转,小腹处倏然一痛,眉头紧紧蹙起。
凌隽珈的吻狂乱地落在她的额头、脸颊、嘴唇、耳垂、一路自上而下落到粉颈、锁骨、隆起。她双手抵在凌隽珈肩膀,被吻得气息凌乱,轻推了推,如同在娇嗔。
凌隽珈双手拢住发育得极好的玉乳,她是她的!她的乳只有自己能揉,她的小穴只有自己能操!星星点点的吻已四处散落在肩颈。
凌隽珈看了一晚的春宫图,已是情欲翻飞,听到耳畔边传来极力忍耐的低吟声,“嗯...唔、别...”
此时她已不满足隔着衣衫抚摸一双凸起玉兔儿,伸手拉扯郁满蓁裙带,快解开时,一只素手终是伸出按住凌隽珈手腕,制止了其孟浪举止。
空气中一片沉默。
远处打更声声声入耳。
“怎么,后悔了?”凌隽珈仍压在郁满蓁身上,只已停下作怪之手。
未闻回应。
郁满蓁侧向一边的脸,小唇紧抿,闭合的眸子,突然脸上传来一丝异样,凌隽珈长指拭抹她的泪痕。
“哭成这样,是在无声指责我在欺负你?”
“答我。” 凌隽珈有点不耐烦。不给碰还不答话。要为谁守清白,姓林的家伙吗?
欲火下去,换成了莫名怒火。
“没有。”郁满蓁也是回应得倔强,此刻在他人身下的她情绪复杂,屈辱、羞耻、惧怕,又充斥着无可奈可的妥协,种种情感交杂其中,趁理智尚未沉沦,身体还能反抗,她终是按住了对方。
她以为一整个下午早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她错了,她高估了自己。
她不是人尽可夫之人,怎可轻易交出身子?她一直盼望的初夜,是和所爱的夫婿一起渡过。
她不想对不起林义,她在等他来救她出生天。她在作最后的挣扎。
可是,妹妹又怎么办?
天人交战。
“刚才进来时不是已做了准备?你如今......是在耍我不是?郁大小姐。”凌隽珈直起身子,居高临下俯首以视。
“我不敢。”
凌隽珈扬手欲打下去,郁满蓁见状,闭眼拧眉。半晌未听有动静,再睁眼时,凌隽珈已下了床榻,掸了掸衣衫上的灰尘,抻直弄皱的长衫,整理好仪容。
“若是无事,给我滚出去!”她负手而立,怒斥着。
郁满蓁拢了拢凌乱的上裳,盖住了半露酥胸,才下榻,走了两步,止住,复又咬咬牙下决终心,双膝跪下,“我错了,求你多给我一次机会。”她隐约知道,今夜若是走出了房门,从此他不会再干扰满香的事。
凌隽珈转过身来,戏谑地道:“好,那是否全凭我指示?”
郁满蓁这次没有犹豫,颔首。她有了赴刑场的决心,这世上,没有尽如人意。她以女性之身出生,就注定过得比男人要艰辛许多。她只望小妹安好。
“既然你不喜我来,那你自己脱掉,一件一件的脱。”凌隽珈款步走来,修长指尖挑起郁满蓁下颔,一字一字慢吞吞道出,仿佛怕她听不明白一般。
没有言语,她惨白的小脸、唇如白纸,颤动的手开始宽衣解带......
一件接一件滑落在地板上。
外衣。
中衣。
里衣。
上裳只剩那上可遮乳,下可盖肚的湘妃色抹胸了。

![毒品女王[NP,H]](/d/file/po18/619564.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