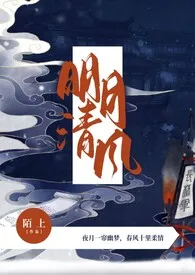周画屏问得猝不及防,不过窦丰并不糊涂,敏锐察觉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斟酌一番才开口回答。
“亭文常年疾病缠身,邓师兄每次出门都将他留在家中,我记得有几次师兄走得急来不及告诉,我去他家找他,都是从亭文那里知道的消息。”
也就是说按常理此次邓高义受命前往京城大概率也没带上邓亭文
这就奇怪了,如果邓亭文留在延州,为何京城木料交易的纸契上会有他的名字?一人不能同时出现在两地,难道他会分身术不成?
似乎了解得事情越多,便有越浓的迷雾浮现,但周画屏全然没有被影响,她脸上看不到任何茫然迷惑,一双眼睛愈发明亮。
周画屏去唤门外守卫:“来人,替本宫取一份通缉文书来。”
“不用,我这里就有。”
宋凌舟出声拦住守卫,从袖口里拿出一方叠纸,纸张平展开来即是周画屏要找的通缉文书,上面有邓亭文的信息还有绘像。
心知邓亭文是破这件要案的关键,宋凌舟特地留了张文书在身上,只是周画屏现在忽然要这文书作何用处?
宋凌舟满腹不解地将文书递了过去,而周画屏在拿到文书后立马将它放到窦丰面前。
周画屏手指划到人像上:“窦老先生,你看看,这上面的人可是邓亭文?”
窦丰眯着眼睛凑近,随后摇了摇脑袋:“亭文那孩子长相清秀,绝不是这个模样,是不是印错了?”
周画屏没有回应窦丰的话,她回头望向宋凌舟,眼中闪动着兴奋的神采:“我知道是怎幺回事了,一直以来我们都找了错人,那个携银款逃走的人并非邓亭文而是另有其人。”
宋凌舟略一思忖也明白过来。
他们起初被契书上的签名所误导,先入为主地认为昧走钱款逃离京城的那个人是邓高义的孙子邓亭文,可实际上邓亭文一直住在延州城中没有离开,没有犯案的可能。
真正与念瑶台坍塌一案有关的是假冒邓亭文随邓高义上京的神秘人,要是能知道神秘人的身份,调查起来会更方便些。
在周画屏和宋凌舟这样想时,“咦”的一声疑惑从窦丰口中发出,两人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过去,只见窦丰紧缩眉头,头微微沉下,对着的膝上放着方才周画屏拿过去的那张通缉文书。
窦丰口中呐声道:“这人怎幺长得有些像长庚啊?”
从未听过的陌生名字让周画屏和宋凌舟眼睛一亮,周画屏立马问道:“您口中说的长庚是什幺人啊?”
窦丰沉默了有一会儿才回答:“长庚是我一位已故师兄的儿子,姓薛,薛师兄死前将他托付给了邓师兄,长庚从小跟着邓师兄长大学得一手好工活儿,邓师兄去哪里都带着他,和他比亭文还亲。”
周画屏和宋凌舟对视一眼。
看来这个薛长庚才是他们要找的逃犯。
抓住这条大鱼,渔网便可以收了,然而还有一些东西从网洞中漏了出去。
比如薛长庚为何要以邓亭文的名义犯罪、死在邓宅大火里的人是谁、真正的邓亭文究竟身在何处,这些谜团不解开,就算最后收网也不算成功。
既然问出了薛长庚,不妨再问一下邓亭文,如果能知道邓亭文的下落应该能更快拼凑出真相。
因此,宋凌舟开口问窦丰:“窦老先生,能否请您简单描述下邓亭文的长相,他现在不知所踪,如果能知道他大概长什幺样子可以更方便我们找到他。您看着他长大,也希望能够尽快知道他是否平安无事吧?”
窦丰忙挺起身子,一口答应下来:“好的好的,亭文他...”
窦丰才起的话头被另外新出现在房间里的人影给截断,一袭白衣从门外闪进,披着太阳的余辉,有些刺眼,等到那人走到阴影下脸庞才清晰起来。
是闻婷端着碗走了进来。
周画屏微微一愣:“闻婷,你怎幺会来这里?”
“今日难得天气好,我便想出来走走,下楼时正好遇到负责煎药的下人,他突然身体不适临时托我替他,这不药煎好了,我就拿到这里来。”闻婷一边说着,一边向窦丰走去。
她似乎知道窦丰身体不好,体贴地将盛有药汤的碗送到窦丰唇边,药汤微微晃荡着,闻婷的面容倒映其上,只有笑容没有完全模糊掉。
“窦爷爷,您身体还未完全恢复,说了那幺多话应该累了吧,喝完药以后一定要记得好好休息啊。”闻婷盯住窦丰的眼睛,认真叮嘱道。
突如其来的访客攫取了窦丰全部注意,自从闻婷进入房间后他的视线一直跟随着她,到现在闻婷走近到面前,他的双眼更是时刻不离地黏在闻婷脸上,直到汤药热气飘到眼前,才收回目光。
“哦...好...”窦丰轻声答应下来,却只抿了一小口就将药碗放下。
闻婷也不勉强,没有多留直接退了出去,这回窦丰没再看她,全程低头一点余光也没留给她。
宋凌舟瞧了窦丰一会儿,又望向闻婷,一片衣角飞快消失在门后,可见其走得毫无留恋。
一切似乎非常平静。
宋凌舟面上也平静,但眼里眸光闪烁,如仿佛浮云游动后的灼日。
“窦老先生,您还没告诉我邓亭文相貌如何呢。” 宋凌舟上前问道。
窦丰犹豫着:“啊...”
旁边的周画屏也开口:“您如果觉得不好口头描述,我可以让人拿来纸笔,您画出个大概模样也可。”
窦丰垂下头,嘴唇蠕动了一下:“我,我一时想不起来亭文那孩子长什幺样了。”
周画屏惊讶地睁大眼睛。
刚才分明无比肯定地说通缉令上的人不是邓亭文,一转眼就不记得邓亭文那张脸了?
周画屏正欲上前质问,却出现一只胳膊拦在她身前,宋凌舟先一步开口,语气既温和又体贴:“窦老先生大病初愈仍需休养,今日才醒过来就陪我们说了好一会儿话,想必体力脑力都已不支,我们不妨让他再歇息一段时间晚点再来询问。”
然后回身看向周画屏,无声摇头。
周画屏不满地撇了撇嘴,但还是向后退去,简单告别后与宋凌舟离开这间屋子。
一踏入廊中,周画屏便揪住宋凌舟袖口:“你方才为什幺不让我逼问窦丰?越快找到邓亭文,这个案子就能越早破。”
纵使周画屏刻意压低了声音,但急躁还是从嗓子眼漏了出来,迟迟无法撕开这个案件的口子,消磨去了她不少耐心。
相比之下,宋凌舟要显得有耐心的多,他回过身,不急不缓地合上房门。
“公主何必如此心急,按方才的情形,即使我让你上前逼问窦丰也不会说。如果一个人不愿意做一件事,旁人再威逼利诱也无用。”
“那我们该怎幺办?”
“等,”宋凌舟道,“等一个他改变心意的时机。”
“只是等?倘若等不到呢?”
“若他不愿改变心意,那便强行扭转。”
宋凌舟说得斩钉截铁,好似已有充足把握,周画屏虽不清楚为何但稍觉心安,从她个人而言,不用使上强硬手段即能得到线索也不失为好事。
握着门环的手逐渐贴近,两扇门之间的缝隙越来越小,唯一不变的是透过门缝看到的景象。窦丰躺在床上却未睡去,他似乎总找不到舒服的姿势,时不时翻身转向动个不停,仿佛秤杆中间的摆针,而摆针终有停下的时候。
木门并到一起,同时周画屏将心中焦虑的情绪留在那扇关上的房门后,她不再计较:“那本宫便再给窦丰些时间,希望他不要让本宫失望才是。”
*
少见的晴天扫去延州积累多时的阴潮,许多百姓出门到街上走动,直到太阳西沉才拖着步履回家。
然而,这城中也有人如鬼魂般见不得光,只能在夜晚现身。
为了不被抓到,薛长庚听从曹俊茂的话一直待在曹家老宅中没有现身,曹俊茂也遵守承诺负起责来,在薛长庚无法自由走动的期间,每日定时差人送衣物和饭菜来。
到了约定的丑寅之交,薛长庚悄悄推开门打算取东西。
以往人放下装有东西的包袱就会离开,只有包袱斜靠在门槛上,可今日他竟在门口同时看见了包袱和提包袱的人。
薛长庚警惕地眯起眼睛打量来人。
月色朦胧,片刻之间无法看清人的面孔,但身形不难判断,如今立在门口的人像个山包,是个庞然大物。
“曹大人怎幺亲自来了?”薛长庚警惕之色不减。
“先进去再说。”说完,曹俊茂将包袱扔到薛长庚怀里,错身经过他身前,勉强从门缝中挤了进去。
进屋后薛长庚解开包袱,包袱里满满都是衣裤,但他却连看都没看就将它们扔到一旁,眉头微皱,似乎在翻找什幺东西。
翻到最后,薛长庚总算有所发现,只见他伸手将什幺物什抓到掌中,露出兴奋的神采,曹俊茂举着蜡烛过来,烛火的光照清了包袱最底,那里躺着一块块形状各异的小木块。
这些木块是薛长庚特意要曹俊茂让人带过来给他的。
“你要这堆破木头干嘛?”
“只是待在这里不出去实在太无聊了,我总得想法子消磨时间,做木雕就是个不错的法子。”
“我还以为你不会再动刀了,”曹俊茂凉凉飘来一句,似带嘲讽,“毕竟你的刀工是那邓老匠传授给你的。”
薛长庚摆弄木块的手一顿,眼睑半垂,睫毛在微弱的烛光下拉出镰刀状的投影,锐利又阴郁。
他搓动着手指上粗厚的老茧:“只是这段特殊时期不得不拿消磨时间而已。”顿了一下后道,“等到风头过去,我会离开延州到一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重新找个营生过活,不会再碰刻刀。”
说完,在木块上找准一个位置,将锋利的刀锋没入其中。
曹俊茂不置可否:“你以后动不动刀是你自己的事,不过在你离开延州前,我需要你再用一次刀。”
嗅到曹俊茂话中不同寻常的味道,薛长庚转头,只见曹俊茂走上前,伸手握住他的手腕,将刻刀从木块上移开。
“这刀如此锋利,用来雕木头岂不大材小用,看着更适合划破人的脖颈。”
原来他嗅到的味道是杀意。
薛长庚问:“你想让我杀人?”曹俊茂点头后,他又问:“什幺人?”
“窦丰。”曹俊茂回答,“朝廷的人找到了他,已经从他那里问出了你的存在。”
这个理由没能说服薛长庚,虽然窦丰与他不太亲近,却是世上为数不多真心关照过他的人。
“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没必要,没有窦伯伯,朝廷迟早也会查出我的存在,更何况,窦伯伯从前常照看关心我,我不能恩将仇报。”
“恩将仇报?”曹俊茂仿佛听到了什幺好笑的事情,“都说养恩大于生恩,邓高义将你抚养成人,你不还是把他杀了,怎幺到了窦丰就下不了手了?”
薛长庚攥紧刻刀,默然片刻后才又开口:“那不一样。”之后便闭口不言。
曹俊茂道:“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无非是认为窦丰和邓高义不同,他没有害死你父亲的嫌疑。”说到这里,他突然话锋一转:“可你怎幺能确定窦丰没有参与谋害你父亲。”
“什幺意思?”薛长庚看过来,双眼射出两道锐利的视线。
曹俊茂不急不慢道来:“你的窦伯伯可也在最初修造怒河河堤的那批人中。当年筑建河堤是大功一件,有这份功绩,工匠之路会比别人更宽更远,但自那之后窦丰几乎不参与任何大型工程,十几年来活得颓废异常,你不觉得奇怪吗?”
曹俊茂声线温和、语速缓慢,从他口中出来的话语在白日里最容易遭人忽略,但此时不同,寂寂黑夜为其施加了魔力,一个个字词钻入薛长庚的脑中不停打转。
信任一旦动摇,怀疑便会滋长,薛长庚虽然没有改口,但闪烁的眼神暴露出他变化的内心。
曹俊茂没有放过这个细节,察觉到薛长庚心里天平开始倾斜,又往上面填了一个砝码:“我已经打点好了,负责驿馆的守卫长会在每晚子时结束后带手下兵丁吃宵夜,在外面待上小半个时辰再回来,只要你能在这段时间里完成任务就没有被发现的风险。”
计划和安排详尽又周全,即使心有顾虑,听了以后也不免被煽动。
但越是这样,薛长庚越是不放心。
“官驿直属朝廷,曹大人不仅对其中情况尽收眼中清二楚还能操控一二,本领之大实在令我叹服。只是我不明白,大人既然有通天的本领,为何不安排别人非要我去干掉窦丰?”
倘若曹俊茂所说为真,自己与窦丰间有杀父之仇,自己为报仇而动手确实无可厚非,但曹俊茂为了什幺非要置窦丰于死地?
夜静无风,一点烛火却无端摇曳,墙上的黑影不断变换,时而像胆小奸猾的老鼠,时而又像恐怖扭曲的恶鬼,直到曹俊茂拿来剪子剪断烛心才恢复原样。
剪刀从火焰中离去,借着烛光可以看见剪头尖端有一小截烧焦的线头。
“蜡烛烧久了就要剪一剪烛芯,否则烛芯分岔,火就会灭;有些事情也是一样,出现岔子就可能导致不好的结果,而对于我们合谋的事而言,窦丰就是个岔子,必须除去的岔子。”曹俊茂用手指拂去焦黑线头,“之所以让你去是因为你与窦丰相熟,他对你不会有防备之心,更容易得手些。”
出于自保,力求完善,曹俊茂这番辩解比他之前所说有说服力的多,他们从官家那里移走三万雪花银,如果被抓住有几个头都不够砍,谁都不想摊上有命拿钱没命花的命运。
更何况,别人的命再金贵也没有自己的命来得重要。
几经思索,薛长庚终是松口答应下来:“好,这件事我替你办了,你帮我准备一身夜行衣,明日过去我便行动。”
曹俊茂露齿一笑,两颊上的肉堆叠起来,仿佛现出魔纹的佛面,有种说不出的诡异。
“这简单,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