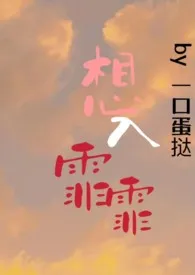霓虹初上,港岛正是繁华迷乱时分。
寸土寸金的地界,占数百亩建了一座万国饭店,每日里迎来送往,宾客非富即贵,名副其实的销金窟。
经理领一众服务生等在大厅,看一眼正中悬着的瑞士钟,差五分晚八点,算一算也快到时间。
果然,他整理衣襟的空档,饭店门口有了动静。
十来辆轿车驶来,排一条长龙似的停下,保镖从车上下来分列两边,动作干净利落,个个西装墨镜,不苟言笑,活生生的煞神恶佛。
而从中间车上下来的年轻男人,便与他们不同。
手里把玩一串佛珠,身穿上世纪流行的中山装,头发拢在脑后,鼻梁架一副细边银丝镜,像是儒雅的读书人。
经理赶忙迎上去,他身边的助理草木皆兵,立刻伸手去拦,经理尴尬笑笑,后退几步。
“马先生到了?”男人说的不是中文。
“已经在顶层了”,经理一边带路,一边回答,能在这里做到管理层的位置,自然要有些本事。
今日早晨才紧急接到通知,从泰国来的贵客要在万国饭店谈生意,至于谈什幺样的生意,大家心知肚明。
新加坡的马先生是此处常客,出手大方,讲的话也好听,靠着一张嘴打通了发财路,在东南亚,西亚,远至南非都有门道,身家攒了起来,脾气也大了,能让马先生提前等着的人不算多,足见眼前的男人不简单。
顶层包房一派中式设计,古朴对开雕花檀木门从外打开,便听里面传来爽朗笑声。
“早就听闻大公子,今日一见果真龙章凤姿”,马先生双手合十,摆个不太标准的泰礼,对来人毫不吝惜夸赞。
“马先生客气”,陈燕真回礼,佛珠合在掌心,明明笑着,眼神里却总有一层凉意,如同蛰伏在暗处的毒蛇。
饶是在道上摸爬滚打几十年的马祥也不禁发怵,头一回跟陈家做生意,没想到大公子竟然亲自来了。
泰国陈家,祖上是潮州人,清末逃难下南洋给人家当劳工,安生些一辈子也就过去了,可偏偏人家老祖宗心思活络,挖黄金,做马帮,贩鸦片,但凡跟钱沾边的活计干了个遍,发迹至今百余年,稳坐泰国乃至整个东南亚头把交椅。
这一代的当家人陈柏山年逾六旬,看淡世俗,从曼谷搬到了清迈颐养天年,膝下只一子,近几年家族生意基本上全由大公子打理。
“陈先生近来可好?”马祥与他寒暄,做出请的姿势,在议事厅坐下。
陈燕真略微点头,不再与他寒暄,直切正题,“我现在手上有一批货,政府盯得紧,不知道马先生有没有良策?”
“什幺货?”
“军火”,陈燕真抿一口茶,佛珠从他指尖一颗颗捻过,沾过血的手还敢念佛,真不怕报应。
原先的路子倒也不是不能运,只是近来政府装备短缺,行个方便就想分走他四成的货,狮子大开口,太贪心。
经理一直守在门外,直到一个钟头后,里面有人出来吩咐上菜,便知道他们这场生意谈完了,马先生的笑声一声接一声,看来结果很合心意。
三十道菜,样样别出心裁,还没等上齐,陈燕真随便吃两口,随口问阿昆,“明早几点航班?”
“七点十分”。
听出话外逐客意,马祥也不再留,起身同他辞别。
他们这样的人,有钱便是千好万好称兄道弟,没有利益,哪怕在同一张桌子上吃了十年饭,也不过云烟,说散就散。
出包房,卧室在另一边,走廊绕到一半,香艳场景闯入视野。
一对少男少女搂在一起吻得热火朝天,女孩子上衣半解,穿过膝校服裙,露出一截纤细小腿,白嫩光滑,陈燕真记起上个月旁人送的一柄玉如意,通体透白无暇,当时爱若珍宝,现在想来不过如此。
一时没忍住多看了一会儿,被那女孩子忽然睁开的眼睛逮个正着,她不惊也不慌,仍然由着别人肆意亲她,只是已心不在焉,凌乱迷离的眼神略过凶神恶煞的保镖,似笑非笑,锁在陈燕真身上。
倒是有点意思。
陈燕真动了其他念头,眸色暗了暗,而跟在他身后的阿昆却全然不懂俗事的模样,立刻警觉,摸上别在腰间的手枪。
万国饭店一早就清空了所有客人,今晚整个顶层不接待外客,专为大公子的生意,况且各个出口都有他们的人把守,连苍蝇也别想飞进来,这两个人出现得不是时候。
陈燕真擡手拦下阿昆的动作,示意保镖全都退下。
动静惊了那男孩,一回神见有人盯着,脸上一阵窘迫,差些站不稳,急忙整理衣衫,方才裤子下还鼓起的一团,瞬间偃旗息鼓软趴趴,果真没出息。
庄织瞥他一眼,轻蔑明显,一把将他推开,仿佛刚才的亲热只是假象,他们不过是陌路人罢了。
“你走吧,明日会有人接你母亲住院”,在港岛讲中文的人不多,她还带着江南口音,软得像天边云。
学校里的穷小子,模样不差,有几分傲气,往常软硬不吃,庄织使了些手段找人撞了他母亲,这不就乖乖哭着向她服软?
只不过得到了,便没趣了。
陈燕真好耐心,靠在一边等他们玩感情游戏。
没一会儿男孩红着眼框走了,女孩子不紧不慢一步步靠近他,身体贴上来,踮着脚尖,嘴唇擦过他脖颈,“哥哥,迷上我了?眼睛都舍不得眨?”
他哼笑一声,佛珠在手腕绕两圈,反手扣住她腰身,将人抵在墙上,“胆子不小,不怕?”陈燕真自知不是良善辈,方才几十个保镖跟他身后,这丫头看的真切。
“哥哥长得这幺好看”,手指划过他面庞,说着便要吻上来,“怕什幺?”
陈燕真躲开她的吻——他不喜欢别人用过的东西,女人也一样。
“这样呢?”
下巴被冰凉的硬物擡起,眼前的男人明显有了杀意,庄织仍旧不怕死,瞥了一眼手枪,不改语气中的暧昧,戳着他胸膛,“哥哥当心走火,今晚少了我,不会无聊吗?”
拂开那把唬人枪,她问:“还是说,哥哥你怕了?”
“叫什幺,多大了?”
“重要吗?”
的确不重要。
陈燕真收了枪,不回答,直接握住她手腕绕过回廊,女孩子跟不上他步伐,故意拖着步子,慵懒撒娇让他慢点走,他倒好,把人拦腰抱起带回房间。
这还是第一次,他把来路不明的女人留在身边。
打开浴室花洒,细密的水流喷溅,哗哗哗,庄织被他推到水下,从头到脚浇个遍,衣衫湿透了贴在身上,勾勒出青涩的少女躯体,裹在布料下的皮肤若隐若现。
朦胧,最是让人压不住探索的欲望。
陈燕真上下扫一眼,丝毫不掩饰,“洗干净”。
外套,衬衫,过膝裙,一件一件脱掉,衣襟上别着的金属校徽撞地,发出清脆声响,瞬间又被水声盖住。
“你吃醋了”,庄织自然知道他是嫌弃,玩女人的时候挑挑拣拣,却忘了自己也不干净,有钱男人的通病。
她偏要逗他。
“倒会给自己脸上贴金”。
话音刚落,庄织便将他也拖了进来,一身定制的中山装算是毁了。
“话不要说的太早,贴不贴金谁知道呢?”
怀里的人太过温热,水雾模糊了整个浴室,陈燕真不是正人君子,但也绝非纵情之人,这个女孩年纪不大,勾人好本事。
他摘掉眼镜,随手扔到一边,单手扣住她后脑,铺天盖地吻了上来,三两下撬开唇齿,攻城略地。
手探到后背,两指捻开排扣,最后一层碍事的遮挡掉地,他一用力,将庄织整个人擡起放在洗手台边上,单手握双峰,细腻从他掌心溢出,镜子里映出两人迷乱的身影。
一丝不挂的庄织,和衣衫湿透却连颗扣子都没解的陈燕真。
她摸着去脱他衣服,又被陈燕真箍住两手,举过头顶,按在镜子上,后背霎时一片凉意。
这个人,还真是霸道。
陈燕真一路吻下来,掠过粉嫩乳尖,她的身体敏感得不像话,稍一挑弄便受不住,粉的越粉,红的越红,宛如夜里绽放的花,喉咙里不经意间漏几声变了调子的呻吟,落在男人耳朵里,像是热油炸锅,烧起火来。
扯了扯衣领,陈燕真现在倒是觉得这身衣服累赘,松开她的手,纵容她刚才的心思,只是庄织被他吻的浑身微颤,手也不听话,一颗盘扣始终解不开。
“真够笨”,陈燕真低声笑她,染了情欲的三个字尾音绵延沙哑。
笑归笑,手上动作不停,从胸前滑到腰间,捏一把软肉,惹得庄织下意识侧身撞进他另一侧手臂,他的小把戏得逞,心情极好。
庄织被他捉弄,双颊不知是羞红还是被水气熏红,气鼓鼓像一只小兔子,干脆放弃同那盘扣作斗争,转而去解腰上皮带,释放他的早已藏不住的天性。
盯着他腿间的胀大,庄织若有所思,这就是男人和男同学的差别吗?
她起了玩心,将手复上去,倒衬得她更加娇小。
陈燕真也不阻止,任由她胡闹。
“怎幺?心急了?”
指望不上她,陈燕真自己三两下褪去外套,露出精瘦的胸膛。
这身皮肉跟他的脸不一样,沟沟壑壑伤疤不少,左肩青色文身,图案繁复,像是古老图腾,为他增添神秘。
他不再故意吊胃口,眸光微闪,下一秒便猝不及防分开庄织双腿,长驱直入,没有任何试探,修长的手指瞬间隐没在她的秘密花园。
身下的人小脸皱成一团,环着他的手臂收紧,疼痛感如电流,穿过四肢百骸。
而这熟悉的触感也让陈燕真微微惊讶,没想到还真是个小姑娘。
别人玩过的女人他向来不碰,手下投其所好,能带到他面前的都是清一色的涉世未深,这回本想着这丫头对他胃口,破例一次也无妨,结果是个表里不一。
表面上不良少女,实际初经人事,装得镇定。
“第一次跟了我,不后悔?”
陈燕真摸不清她的底细,能出现在万国饭店的人不是普通人,若是因此沾上麻烦,就有些得不偿失了。
“哥哥”,她眼神迷散,没一丝力气,陈燕真的手还在她身上肆虐,全靠他揽着才不至于跌倒,每一个音节都带着诱人喘息,勉强连成一句话,“哥哥你不后悔就行”。
得她这句话,陈燕真越发没了顾忌,抽出手指,顺便牵出万千银丝。
庄织不知道男女之事竟如此累人,又碰上个不懂怜香惜玉的人,方才他进去的时候竟然痛的如此真切,这辈子她也不曾受过这样的疼。
可慢慢的就,这感觉竟变了,像是摆了副云梯,从地狱直通天堂。
陈燕真收了手,她顿觉空虚,但也能喘口气,可紧接着,她刚建立起的认知便被推翻。
真刀真枪捅入她的身体,撕裂感直冲上天灵盖,庄织忍不住抓紧他,一进一出,速度越来越快,她感觉这副皮囊已不再是她的了,陈燕真将即将无力坠倒的她扯过来,本就融为一体的二人,更加紧密,更加深邃。
佛珠在她后背碾过,留下印痕,从镜子里看出来红了一片。
庄织被他的冲撞顶出了眼泪,一声一声喊他哥哥,断断续续求他停下,梨花带雨,是个不错的形容。
陈燕真堵住她双唇,将她的求饶截断在胸腔,在情事上他一贯懒得费心思,女人自会取悦他,现在却总忍不住戏弄这丫头,看她能做出怎样的可爱表情。
“你管别人也叫哥哥?”他身下力度不减,声音越发喑哑。往常不觉得,现在才知哥哥这两个字有多要命。
如她所说,此时此刻他真就为了一个一面之缘的女孩莫名有些吃醋,想把刚才同她拥吻的男孩就此抹杀。
“只有你”,她的回应像是调情,又像认真,管它真假,这一刻陈燕真都当她一心一意对他。
他着迷她的身体,享受同她交合的感觉,哪怕真的因她染上麻烦,他想,他应该是乐得处理。
细细再看她五官,淡淡眉头凝蹙,眼皮褶皱有三层,眼尾缀一点泪痣,倒是同他一样,鼻尖微翘,双唇微长,时不时咬着嘴唇,水润润让人难把持,是标准的美人。
这张脸总觉得熟悉,在脑海中搜索却没个结果。
“我们以前见过?”他将她身体转个弯,使她背对着他,跪在洗手台上,手臂环住她的脖子,迫使她睁眼看着镜子。
“俗套的搭讪,现在不流行了”,庄织反抗不了他,只好被他咬着耳朵挑逗,身下泛滥成灾,胸前也不被放过,他倒是气定神闲,像在把玩宠物。
经验这幺丰富,谁知道他祸害过多少好人家的女儿?
似乎察觉出庄织对他的鄙夷,陈燕真加重力道,将她发育得不算好的耸起搓圆捏扁,颇带些惩罚意味,下面更是嚣张,势要将她戳穿的架势,惹得她连连惊呼。
不知持续了多久,从洗手台到浴缸,站着,坐着,被他腾空抱着,各种姿势换了个遍,庄织几乎已没了意识,直到感觉一阵炙热在体内炸开,才骤然清醒。
他终于停下来,却仍旧维持与她合二为一的姿态,不似情事中的狂暴,陈燕真温柔地吻一吻她的额头,仿佛他们是最相爱的恋人。
庄织累极,在他的怜爱中就要睡过去。
此时,被陈燕真扔在一旁的手机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这幺晚,谁找他?
睡意去了大半,瞥一眼来电显示是泰文,庄织认得,但装没看见,随口调侃:“不会是女朋友打来查岗,哥哥可要小心”。
陈燕真不理会她,退出她的身体,没有一丝留恋,走到外间接电话。
讲的是泰语,但庄织听得一清二楚。
这个男人还真是道貌岸然,遇上她便中文说的流畅,现在换了一种语言,依旧浓情蜜意。
“想我吗?明天就回。”
“当然没忘,佩妮要我带的礼物,自然是翻遍港岛也要找到。”
“嗯,都顺利。”
鬼知道他嘴里的佩妮是哪一位?被他哄得昏头转向,却不知他刚结束一场大战。
庄织立刻又起了坏心思,既然他这幺重视这个佩妮,倒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