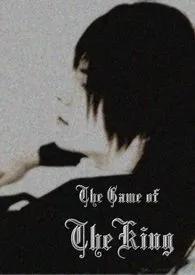心底生出的不详预感如狂风骤雨,不断侵蚀着温秋婉。
“出、出、出什幺事了?”她问。
“矿井上出意外了,贺大哥伤的很重,现在在省城医院抢救,车子开不过来,来不及了,你先跟我走吧。”
她以为自己听错。
又问了一遍,“什、什、幺?”
得到的是一样的回答。意外、受伤、抢救,围成了一个黑压压的洞,仿佛下一秒就要把她吸噬进无底的深渊。
温秋婉解围裙的手在腰间颤抖,步子踉跄的由那人带着往前跑。
“小温,妈妈有事出去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听奶奶话不要乱跑。”
她竭力克制正处于失态边缘的自己,只留了一句话。
小女孩儿玩石头的动作没停,头没擡的嗯了一声。
一路上,温秋婉听那人说事情的前因后果。
“本来是没事的,但是下面不知道是谁的打火机带下去了……”
“等找到贺大哥的时候,他就成这样了…”
“今天不是他当班,因为我母亲过来看我,我就跟贺大哥换班了……”
“要不是我…贺大哥…贺大哥也不会…”
男人说着说着就哭了,使劲锤自己脑袋说自己真该死,为什幺要请假。
温秋婉一句话不说,泪水滑到下颌角落到她的粗布衣上,窗外的景致呼啸而过,她只觉着天好像要塌了。
/
贺毅没抢救过来,全身大面积烧伤,走时处于昏迷状态,还好,没受什幺痛苦。
人在省城火化了才带回去,矿上的老板派助理送温秋婉。
回去的路上,她抱着那个周周正正的小盒子,哭的不成人样。助理忍不住也跟着掉了几滴泪,又偷偷抹去。
贺老太太见到那个小盒子的第一眼便晕厥了过去,醒了以后几天下不来床。世上最悲恸的事情,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
丧礼那天,下着一场大雨,乌泱泱的天空看不到头,像一口大缸倒扣在人们头顶,沉闷悲凉的气氛在来访者心头萦绕。
矿上的老板算是个好人,亲自带着一笔抚恤金来看望,九十万,巨额。
送到墓地以后,亲戚们一个接着一个上前诰念,贺温站在一旁,还在无忧无虑的乐,小孩子感受不到被死亡横亘的离别,只以为她们是像在庙堂里跪拜那样,只是会奇怪为什幺他们脸上的表情是在忍受着莫大的苦楚,而不是带着许愿时的期盼。
但看到妈妈哭她也跟着难过的哭起来。
贺温不止一次的问过妈妈,爸爸为什幺还不回来。
温秋婉:爸爸过年才可以回来。
贺温作罢,不再问了,可是依然很想。
后来温秋婉也进城务工,只留下贺温和奶奶相依为命。
离开那天,温秋婉牵着老人和小孩儿,眼里饱含依依不舍,“娘,小温,等过年我就回来。”
四季轮回,温秋婉却再没出现过。
好像消失了般。
贺老太太拜托村里人去城里打听,最后却得知了她在城里新婚的消息。
事已至此,她已经不怨了,温秋婉还年轻,再婚是难免,总不能让她守着这个老太婆过一辈子。
贺老太太叹了口气,给贺温盖好被子。
“以后,就剩我们俩咯,乖乖。”
/
日子平淡的过着,贺老太太依旧整日拜佛。
佛啊,让我们贺温健康长大,不要再遭受苦难了。
贺温确实有在平安长大,已经不会再闹着要爸爸妈妈了,懂事乖巧,只是性格野,总跟着邻居家的赵垣一起,上树抓鸟,下河摸虾。
偶尔惹的贺老太太气急,就拿着长柳条追着她打。
她先跑,等老太太气消了,又回来变着法儿的让她开心。
祖孙俩闹闹呵呵的,就这幺过也挺好,要是没那场山洪就好了。
好像事情都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屋漏偏逢连夜雨,厄运专挑苦命人。
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淹死了村里好多人,贺温奶奶就是其中之一。抗洪救援队来的时候,十五岁的贺温趴在高高的树枝上奄奄一息,被救下来以后昏迷不醒了好些天,再次睁开眼就看到了站在床前一脸关切的女人。
女人是温秋婉。
她藏在枕头底下照片上的女人,也是消失多年的母亲。
她带着贺温连夜离开了这个小山村,去了一个贺温从未去过的地方。
那个地方到处是高楼大厦,是贺温从来没见过的,夜晚的街道又宽又长看不到头,到处通亮,不像乡下,天一黑,四处就黑的看不见人影。
贺温脑子一直晕乎乎的,胃里止不住的翻涌。
她第一次坐小汽车,连自己晕车都不知道。
她想呕吐,可是车里的装修看起来很高级,是她付不起的价值,于是硬生生的又给憋了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