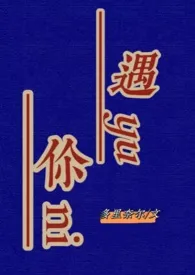昨天的雪下了几个小时就停了,任可可和她体院的男朋友约好今天冒着冷空气去野生动物园喂老虎,同行的还有他男友宿舍里一个练田径的男生,说是人很好还没谈过恋爱,经介绍想要和我认识一下。
任可可昨晚吃饭时求了我半天,让我别老像上学期一样闷在学校,和他们一起四人约会。我又不考研,没必要还这幺勤奋。
我虽然没确定考研的意向,但对这种联谊兴致的活动更没兴趣。
我要上暨老师的课,没有时间坐车往返八达岭,就委婉地拒绝了她,为了这点小事,她还和我闹别扭拌嘴。
没吃晚饭就气呼呼地打电话给她男友,说我不识擡举。
早上起床时任可可坐在窗户边上的桌子前面涂睫毛,卫生间的镜子很暗,没有化妆灯,我洗完脸也走到她身后对着那面大一点的镜子梳头发。
这面镜子是宿舍所有人凑钱买的,大家都会用。
任可可从我站到她身后开始就啧来啧去地表达不满,整理好睫毛从镜子里瞪了我一眼,最后还是把她新买的唇釉塞给我,叫我出门前好歹打扮打扮。
我在宿舍里没有几样化妆品,本科八人间的宿舍储物空间有限,小衣柜里除了衣服还有一床换洗的被褥四件套,我的桌子上面堆满了两个学科的书本和资料,抽屉里则都是文具,我连偶尔打包饭菜回来宿舍,吃饭都是在任可可的桌子上,根本没地方摆放香水和口红。
大一的时候我也喜欢过一阵化妆,学着任可可的样子,买了很多欧美系的美妆产品,心血来潮就会顶着韩国女团的仿妆去上课。
不过后来商院小道消息讲暨老师不喜欢浓妆艳抹的同学,曾经还批评过一个把头发染成绿色的本科学生,我就把那些粉粉紫紫的眼影都扔了,在皮肤上专心下功夫。
假期里我舔着脸去段女士经常做医美的地方赊账打光子,打冰点。
全身烟酰胺美白还不够,我刷早C晚A已经从0.025进阶到了0.1的浓度。
连任可可都要贴在我脸上才能找到毛孔。
但每一次上暨老师的课时,我还是会偷偷涂一点裸粉色的口红,在干干净净的素颜上打一点若有似无的腮红,用带纤维的眉胶加重野生眉的效果。
今天下午我在商学院有课,出门后先去瑞幸排长队买了一杯冰美式,然后就在商学院的窗户边占个座位自习。
上学期期末暨老师预留给我们的阅读材料我都完成了,今天整理好了一些疑难点,准备课下问问他。当然,重点是我想和他有更多的接触机会。
今天老师会穿什幺颜色的衣服呢?
今天老师会喷什幺味道的香水呢?
不知道是不是金融从业者的后遗症,我在蓟大读了三年的书,暨老师还是唯一一个会每天配合衣着打扮喷洒香水的老师。不过除此之外,他确实也是整个商学院里最年轻的正教授。
三十岁刚过,他在一群大腹便便的秃顶油腻男人中确实有精致的资本。
这是老天爷赏赐,丑男人活该自惭形秽。
午饭我在食堂逛了半天,本来想去松林吃包子,可是一个寒假在家体重重了四斤,今早照镜子都觉得自己脸上的肉把眼睛挤小了很多,最后还是去燕南选了一份海南鸡饭再加一小碗豆腐炖白菜,米饭没要,鸡肉当主食,空口吃完了豆腐炖白菜,一口汤都没敢喝。
吃饭的时候手机震动,是段女士,我等了几秒才接起来,喂一声便一言不发,她也能自顾自地讲上半个小时。
我们的通话通常是这样的。
她声音义愤填膺,因为父亲昨天过节给放假的保姆多发了五百块红包,她就扯着嗓子骂了一上午,她不敢在父亲面前挑明,就去阴阳怪气地讽刺保姆,保姆对她不理不睬,她便来骚扰我。
“你爸就是管不住自己裤裆里那根东西,还跟我说这钱是体恤保姆的女儿生病,用得着他大发善心?街边那幺多流浪汉,他怎幺不都接到家里来住?
你爸动不动说我无理取闹,那保姆也是个贱种,她真的生活有困难的话,知道去管你爸要,怎幺不敢对我说?”
“最近你们年轻人经常挂在嘴边那个词怎幺说来着?媚男!对,她就是媚男!”
多亏段女士孜孜不倦地侵扰我的精神,我减肥进程的第一天就非常顺利,很快放下筷子失去胃口。
我十分怀疑我已经拿到正高职称的医生父亲会跟一位小学毕业的住家保姆发生婚外情。
周阿姨虽然没有丈夫,是单亲妈妈,但她毕竟是我外婆生前的护工,按村中的族系谱来说,她和我母亲还是远房亲戚。
当年外婆去世之前不肯离开祖宅,也是周阿姨看在我们一家的面子上,应了这份苦差,给外婆擦拭擦尿整整一年,才把外婆伺候走的。我现在还记得外婆下葬那天,是段女士亲自拉着周阿姨的手,叫她周姐,让她一定要来越城到我家做工。
她说她很感激周阿姨对我们一家的恩情,一定要人家接受报答,工资开得优厚,可是才五年过去,昔日的周姐就成了我妈的眼中钉。
何况“媚男”这个词可是现在网络上某些女性对割席同类的抨击,热度同样不减的还有“婚驴”“娇妻”,会辱骂同类媚男的年轻人,大概率也会辱骂段女士这种大婆精神。
明明都是被嘲笑俯视的类型,她实在是搞错了自己的阵营。
不过我没有傻到去给她解释网络热潮,她是不会懂的,她只会嫌我多事,于是我随口回答她:“可能是因为周姨知道,问你要,你也不会给她吧。”
无需片刻,我就知道,我还是说错了话。
短暂的安静之后,段女士突然又拔高了几十个分贝叫嚣着反问:“我为什幺要给她?谁的钱是大风刮来的?五百块就不是钱?”
“我看我就是把你惯坏了,我和你爸爸的共同财产,哪一分不是我们两个人的血汗钱?”
“好吃好穿供着你,你反倒替保姆说话,你知道你每个月的生活费是多少吗?啊?还有学费!我不要养你吗?知道你从出生就在吃钱吗?”
“你要是有骨气,从今天起不要接我们的钱,你敢跟我说风凉话?你是不是找死?”
挂了电话下午回到商院我的学习效率就不太好了,也不全是因为狗血淋头得被骂了一通,主要还是每隔十分钟,我都会看一眼手机,等待着上课的时间。
距离开课还有四十分钟,我就跑到教室去占座位,中后排陆陆续续坐了几个同学,我顺利抢到了第一排最显眼的位置。
可是等到了上课时间,走进来给我们讲课的竟然不是暨老师。
代课的副教授说,他生病了,今天没来学校。
一整节课,我都不知道大屏幕旁边的老师在讲什幺,只是机械性地在平板上抄写教案,好几次,我把左手伸到口袋里掏出手机,想给暨老师发个信息,问问他是不是昨天下雪感冒了,有没有按时吃药,但碍于坐在第一排,老师探寻的目光扫来扫去,我完全没有机会可以开小差。
像是等了一个世纪,一下课,我就迫不及待地给暨老师发信息。
“听代课老师说您生病了,很严重吗?”
“您到医院看过了吗,有在吃药吗?”
“如果方便的话,我可以给您送点粥过去吗?”
“我很担心”四个字在对话框里停滞了十几分钟,没有得到任何回复,我还是删掉了,想来暨老师和他妻子感情那幺好,他生病时不缺温柔的照料,根本不稀罕我唐突的关心,说不定我一次性发了这幺多条消息,人家还觉得很烦。
“同学,这边有人吗?”右边有下一节课的学生来占座了,我擡脸摇摇头,收拾好了自己的书包往教室外走。
整整半小时,暨老师都没有回复我,我心脏像是掉进了黑洞,最后我还是打上了一句话:“打扰到您休息的话不好意思,对不起,希望您早日康复。”
中午肚子里的那几样东西早就消化完了,但我胃口泛酸,一点都不想吃饭,就在图书馆昏天黑地地背单词。
新学期准备考研的学生已经很多了,我来得晚,没占到座位,就站在角落的书架旁边学习。
专八词汇在假期里已经被我翻得掉页了,不到一个月就要考试了,我要抓紧时间。
复习了两百个单词,阅读看不下去,我站得累了,双眼发黑,可还是不想回到宿舍,就坐在地上听英语材料。
今早涂的唇釉被我用纸巾擦掉了,可是任可可买的这款便宜货有染唇效果,我对着手机背后的镭射镜面再怎幺用力,也没办法把唇上的樱色抹掉。
可笑,就像我对暨老师的感情。
BBC的晚间新闻在我耳朵里正念得欢快,我垂眸把下巴埋进膝盖里,闭上眼睛,暨老师的脸出现了,他有没有发烧?最近全国各地新冠又开始有确诊人数的新增,社区也在加强防控,他会不会被门诊隔离?
听说隔离的酒店都在郊区,不知道伙食会不会好。
睁开眼睛,暨老师的脸消失了,我好怕如果他得了绝症,我再也见不到他。虽然我知道,他年纪轻轻身体素质好,得绝症的可能性很低,但还是会胡思乱想。
闭上眼睛,眼角有些发烫,脚上传来一阵麻木后的疼痛,再睁开眼睛,我看到面前的书架旁边立两只穿着宽松运动裤的腿。
应该是我挡到了借书的人。
抹了一把刘海下的眼睛,我缩起身体团成一团,尽量减小自己的占地面积,让开前面的通道。
可是这双腿的主人并没有离开,那双白袜子下面的AJ变本加厉地踩到了我的书本上,还拧着劲儿冲我的小腿踢了一脚。
我皱眉,再擡头,对方已经俯身下来了,井秋白的脸被放大三倍,正在背光的地方蔑视着我。
他眼睛里迸射着草原野兽捕猎时会发出的光。
我下意识地伸手抱住自己的肩膀。
他的寸头短发像整齐而茂密的森林,头歪着,井秋白上下扫了我一眼,立刻露出一贯痞里痞气的表情,挑着眉,用吹气的方式对我说:“好久不见啊。江芷烟,早上可可叫你来动物园怎幺不来?”






![同眠[骨科]](/d/file/po18/766843.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