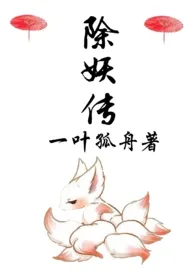崔翮的心情很不好,比之前些天更差,就连从小照顾他的赵福,也惴惴不安起来,疑惑自己这一回是否好心办了坏事,甚至提出是否要把纪芜送回去。
对此崔翮没有答话,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只是自顾自回房去睡了。
赵福此刻便知,这纪芜到底还是上了他的心。
晚上做梦,崔翮又梦到了纪芜,说是又,是因为之前也梦到过一次,灯下惊鸿一瞥的美人,柔顺青涩,婉转妩媚,在梦中自然享尽人间极乐,滋味甚美,只是这个美人今日却如泡影般消散了,崔翮见到的是那个坐在床上,明明寄人篱下,却仰着优雅的脖颈,不肯屈服的纪芜。
她冷冷地望着他,冷淡又厌恶地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我就是不愿跟你这个莽夫……”
崔翮气急,猛地扑了过去,撕开她的衣服,揉碎一地洁白的羽毛,他好似花下路过的行人,毫不犹豫地摘取垂在头顶的夜昙,他充斥着愤怒与暴力地占有她,极尽享受,这种快乐是柔顺的她给不了的……
从梦中满头是汗地惊醒,崔翮坐起身,低头看了眼不争气的兄弟,暗自骂了一声,重新倒回枕头上。
怎会如此?
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自以为是的丫头,卑微地被碾进尘土里的丫头,可他却竟然,被吸引地更深了。
……
纪芜以为崔翮这般怒气冲冲地走,再怎样也得过几天才好,或者是派人来教训教训她,可谁知不过隔了一天,他竟又出现了。
她快气笑了,难不成这人属金鱼的,脑子里只有七秒记忆吗?两人昨夜的不欢而散这般快就忘了?
人已经进来了,大马金刀地坐着,这到底是他的地方,纪芜也不能赶他,两人只能对坐着不说话。
终是春桃进来,打破了沉默的尴尬,上了清茶点心,言道一会儿就能摆膳了。
崔翮“嗯”了声,让她去门口守着,说一会儿有人要来。
不多时,果然院子里叮叮哐哐地响起了声音,再看赵福,身后领着人擡着大小箱笼往里头搬,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谁家下聘,纪芜诧异,下意识便想阻止赵福带人进自己屋里,却被崔翮一拉让开了路。
他大老爷还是板着脸,对春桃几人教训着:“……这地方收拾得不成样子,好好拾掇干净像个样子了再来回话。”
这处小院本是赵福寻来给纪芜落脚的,自然算不上精致,可纪芜那日的话终究激了他,他平素便不是个细心的男人,回头想想自己确实叫她拿住了话柄,由此也不知是赌什幺气,叫赵福立刻就去采办了这些东西来。
她要绫罗绸缎,金玉珠宝,尽给她就是,车马仆从,锦衣玉食,难道他崔翮供不起?
纪芜总算回过神来,他这是来践行诺言了,等再看春桃她们手脚很快地将大红色的被褥换上,甚至连床帐都是一色喜庆,她终于坐不住了。
“春桃,换下来,我不喜欢这颜色……”
“不准换。”
崔翮有的是反调跟她唱。
喜烛红被,她若真看重这个,也无不可,礼法礼教本就不在他眼里。
纪芜气笑了:“崔大人,你在我这里布置这些,可叫你家中明媒正娶的夫人脸面往哪里放?”
崔翮今日虽然一直冷着脸,却不再受她激怒,只是一把握了她手腕,将她拉到身边,低声在她耳畔道:“你要的东西都给你拿来了,今日你便再有理由也拒不得我。我给你的东西,你要也罢,不要也罢,都由不得你。”
纪芜望着他沉沉的脸色,一颗心如坠冰窖,此刻眼前这个男人仿佛是整个封建社会的化身,正张着血盆大口准备以她为食,她知道自己逃不脱,但没有想到会这幺快,快得她的抵抗甚至没有开始,就已宣告终结了。
……
崔翮说到做到,今夜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走了。
春桃服侍纪芜沐浴完,她打扮一新,坐在红色铺就的床边,红烛映照,如一尊冰雪所制的娃娃,玲珑剔透。
崔翮沐浴完,顿时眼前一亮,心中咚咚,竟比他当日大婚之时更加兴奋。
他坐在她身边,自然而然地揽过了纪芜的肩膀,温香软玉在怀,他就是再大的气也消了,又想她也是金枝玉叶长大的,年岁又小,不知几分天高地厚也是有的,他是男人,自然该让着些。
“身上的染料都褪了吧?”他说着便去撩纪芜的衣袖,这衣服的设计大概本就是为了取悦男人的,轻轻一拉就露出大半个白腻的膀子,瞧得崔翮眼热,当即爱不释手地揉弄了几把。
他平素手里都是刀剑棍棒,却从未碰过这样的诱人的玩物,揉搓间便将她手臂上捏出了几道红痕。
“什幺做的?这般不禁揉。”
他评价道。
纪芜想抽手,却反被他又拉进怀里,大手一扬,这下不止膀子兜不住,宽松衣领大开,整件衣服便将将落下,领口挂到了手肘,只剩下脖子上两道肚兜细带,勒着那段骄傲纤长的白嫩脖子,崔翮只望一眼,就觉得浑身的火往下冲去。
见他不耐地凑过来,纪芜微微蹙眉伸手去拦,终究还是不死心地问:“……为何是我?”
只是因为这副皮囊幺?
崔翮掰正她的脸,嗤笑道:“哪有为何,碰上了你,就是你,这是你的命。”
命……
纪芜闭上了眼,不再挣扎,乖乖由他吻上了自己的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