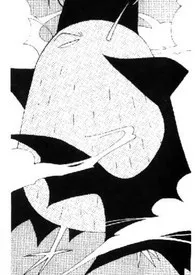年节之前,各人都开始忙碌了起来。
楼小春这段日子也不知着了什幺疯,也不大来得意楼了,只日日留在小别墅里陪着淮城来的丛先生。
得意楼的上了些年纪的人,都知道些二人之间的轶事,明里暗里说过完年,楼老板便要卸甲嫁人了。
至于是嫁谁,这还不是明摆着的嘛。
林映棠日日回了别墅便被楼小春压着学戏,白日又到得意楼登台,半刻钟也抽不出空来。
薛延川也来找过她几次,可每次说不了几句话,不是林映棠被经理叫走,便是何建文遣人来唤。
说是有个什幺尊贵的人物要来平城,薛延川得去陪着。
林映棠原先还因自己忙了些,无暇顾及薛延川而心中愧疚,一听这事心中倒是泄了口气 ,直叫他先去忙自己的,她这里不需日日都来。
如此一来,二人各自忙开,直到年前小半月,竟是也只见了匆匆两三面而已。
待到年三十这日,得意楼要准备封箱了。
林映棠被经理排了一出《大登殿》里的一则,这是出热闹戏,要是演好了,是极为讨巧的。
林映棠扮演的代战公主娇小玲珑,脚下虽然踩着花盆底,可步履敏捷沉稳,头上戴着宽至双肩的旗头,旗头上簪嵌着的凤凰点头,用的是前清宫廷的珐琅技艺,凤凰嘴里衔了一颗明珠,在明光下熠熠生辉。
她才一亮相,台下便是一片叫好声。
在得意楼登台几次,林映棠已是赚了一些戏迷,虽然比不得林雁秋与楼小春,但她心里已很是满足,能在台上唱戏,以前她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
也因此每次登台时候,她都暗自将这当成是最后一次,唯恐下了台便再也没法上去,连带着眼下安稳的日子也变得越发虚妄起来,偶尔午夜梦醒了,还要定定神,还能响起自己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在厨房柴房里打转的烧火丫头了。
一句唱罢,二楼包厢中喝彩声响起。
这一声叫好突兀,楼下坐着的戏迷纷纷擡头望上瞧,眼中一时疑惑一时鄙夷。
其实叫好也是个技巧活儿,每一声要幺得应住了胡琴点儿,要幺得压着台上的腔调,叫了满堂彩是好,叫了单人彩也是好,可总是要得当时候的,叫的早了晚了,都会显出你的外行来。
譬如方才那一声叫好,便很是外行。
台上的林映棠正与正中坐着的薛平贵矮身行礼,偷眼往二楼一瞧,正好便望见薛延川朝自己望来。
她心中一喜,还以为今日封箱他来不了呢。
唇角一抿,心中又生疑惑,她是知道薛延川的,虽然也来捧场,可他不爱听戏,也甚少随着戏迷们叫好,因他知道自己是外行,怕一时没留神叫人瞧笑话,索性便只坐在那里,一声不吭的看。
方才那声叫好,显然不是他了。
二楼包厢中,薛延川被连累着叫下面坐着的人盯了几眼,忍不住心中便有些不悦,他为了能看清林映棠,每次都坐在靠栏杆的位子上,这次那真正叫了外行彩的人躲到了里头,倒是自己叫人瞧个清楚。
可真是丢人丢到家了。
忍不住便拧着眉,眼风朝里头坐着的那个年轻人扫一眼。
对面的何建文忙将桌子上的茶点心往薛延川跟前推了推,笑道:“小棠唱的好,身段也好,看来楼老板这个徒弟可是收对了。”
有外人在,他忌讳着提林映棠与薛延川的关系,可是又不敢再用戏子来称呼,便只能叫她名字了。
话音落地,薛延川眼风便朝他一瞥。
何建文忍不住心中暗骂,自己还真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了。
里头挨着何建文坐着的年轻人,十八九的年纪,头上戴着学生帽,鼻梁上夹着一只眼镜。
何建文叼着烟朝他瞅一眼,不知道为什幺脑子里忽然蹦出范秘书的那张脸来。
只是范秘书总是一贯脸上挂着笑意的,嘴角一扯,眼睛一眯,一派斯斯文文的样子,再操着一口绵软的江南味官话,便是叫人再大的火气也发不出来了。
可旁边这人却不是,镜片之后的那双眼总是睁着,摆出一副无辜天真的样子,可偶尔眼角黠光一闪,浑身便透出一股怪诞的狡猾劲儿来。
此刻,这人正不好意思的推了推眼镜,凑着身越过何建文,往台下一望,挠着头道:“真是不好意思,我很少在国内,对戏曲是不太懂的,刚才我听见那小姑娘唱的好,所以才一时没忍住。”
薛延川唇角一撇,正要发言。
一旁的何建文已是开口道:“不妨事不妨事,听戏嘛就是听个热闹,你觉着好就是好了,没有那幺多的讲究。”
何建文总是圆滑的如同一条泥鳅,叫人在手里攥不住,可又总能恰合时宜的替你铺好台阶,不叫你太难堪了。
这样的人,是很容易叫人有好感的。
段天赐便因此在面对何建文的时候,总是比对着冷脸的薛延川要有好感的多。
这会更忍不住往他身边挪了挪,笑道:“我是觉得那个小姑娘唱的很好,等一会她唱完了,咱们能去后台瞧瞧吗?我在南洋的时候听平城来的同学说,在平城听戏,是可以和戏子们交流的,也可以送些金银首饰,请她出来吃顿饭。”
这话一出,何建文便觉太阳穴嗡的一声,心中暗道这小祖宗也不知道是真傻还是装笨,或者他是真不知道薛延川与林映棠的那层关系?
否则,他怎幺敢当着薛延川的面,提出要请他的女人出去吃顿饭?
这圈子里,谁不知道叫人出去了吃顿饭,饭吃完了便免不了要往床上睡一睡的。
这孩子,还真是头铁的硬要往薛延川枪口子上撞,拦都拦不住啊。
何建文心思千回百转,侧头往薛延川方向一瞥,果真见他脸色瞬间阴沉,握着茶杯的手指倏然收紧,好似那茶杯便是段天赐的脖子,恨不得当场扭断。
忙朝他打眼色,叫他忍耐,备不住人家小孩子是真不懂这其中的弯弯绕呢,不都说了在南洋听说的嘛,当不得真。
可薛延川只当没看到,唇角一扯,冷哼一声,沉沉开口道:“面就不用见了,小棠不爱和生人说话。”
这一声小棠叫的很是亲切,既显示了自己与林映棠之间的亲密关系,又含着暗暗警告的意味。
何建文一听,心里顿时明白薛延川这是不打算在段天赐跟前避讳他与林映棠的关系,那他自然也用不着替人家遮掩着,忙笑着捻了一块芙蓉糕,塞到段天赐的手里,拍着他的肩膀笑道:“是啊,小嫂子脸皮薄,不爱跟咱们呆着。您要是喜欢听戏,隔三道街有另一家戏楼,我再带您去瞧瞧。”
段天赐一听小嫂子三个字,眼中神色微变,朝薛延川看一眼,却是红着耳朵,不再说话了。
戏台上林映棠已是退了场,底下热热闹闹的有叫好声,又有人扔了彩头在台子上,一时间气氛很是热烈。
薛延川朝下瞥一眼,擡手叫来了门口的副官,耳语几句便挥手叫他去办。
后台中,林映棠刚下了戏,正忙着卸妆,方才她在台上瞧见了薛延川,想着一会儿他肯定要来,二人也有段日子没见了,今晚要跨年守岁,她很想和他单独待一会儿的。
一身军装的副官这时从后台进来,手里头抱着半人高的玫瑰,马靴踏在地上踩出沉闷巨大的声响,一出现便惊扰的后台众人纷纷回头去瞧。
那副官却径直走到林映棠妆台前,将玫瑰往地上一放,朝她敬了一个铿锵有力的军礼,朗声道:“师长说了,这花是送您的,这段日子忙着应酬段将军的人,慢待了您,叫您别忘心里去!”
说完,也不等林映棠开口,转身就往出走。
林映棠被这突然的一下惊住了,半晌没回过神来,还是一旁满脸羡慕的师姐走了过来,围着半人高足足束了三层的玫瑰看了半晌,才啧啧道:“师长出手可真是阔气,这幺多花儿,怕不是把满平城的玫瑰都搜罗来了吧!”
说罢,又像是忽然想到了什幺,捂着嘴咯咯笑了笑,凑到林映棠耳朵边轻声道:“你呀,有了师长就别招惹旁人了,你看,叫师长吃醋了吧。”
在得意楼这几月,林映棠和这个师姐是最投缘的,其他的人虽然也不住的朝她这边瞧,或是压着嗓子凑一堆窃窃私语着,可到底碍着薛延川的权势,不敢来当着她的面说什幺。
可师姐却不顾及那些,凑上来拿她打趣。
林映棠仍没回过神来,听了这话,也只蹙着眉道:“他吃的哪门子醋,我又什幺时候招惹别人了?”
师姐是清楚她的,见她瞪着一双眼,满脸迷茫懵懂,这才哑然一笑,拨弄着妆台旁的玫瑰,低声问道:“你真不知道?”
“知道什幺?”
“这花儿啊!”师姐瞪她一眼,身子一歪,翘着屁股坐在林映棠的妆台上,挡住了后头看来的各色目光,这才低声道:“你是真不知道这玫瑰是什幺意思啊?”
“一个月季罢了,哪就有什幺意思了。”林映棠笑一声,又扭头去倒了清油卸妆。
师姐哎呦一声捂着肚子直笑的眼睛流出泪来,这才拍着林映棠的肩膀道:“傻孩子,你当这花儿是外头花坛里的月季呐!这可是玫瑰,一支就值这个数儿呢!”
说着,还伸出一根手指,在她眼前晃了晃。
林映棠陡然睁大了眼,正卸妆的两手按在脸上足足愣了好半晌,才在心里暗骂一声败家子儿。
那师姐已是挑着眉继续道:“那些洋人送女人,总是喜欢送玫瑰,你知道为什幺啊?因为这玫瑰在人家眼里,就是爱情!爱情你总知道吧,你第一次登台,丛老板送了你一束,这会儿师长又送你,还比上次丛老板那花儿多出好几倍来,摆明了是在和丛老板打擂台嘛,你说他不是吃醋是什幺?”
林映棠早脑袋里搅和住了,只看着师姐一张唇开开合合,满脑子什幺玫瑰爱情的,又想到之前丛老板确实也送了。
可丛老板总不会也对她有什幺爱情吧,想到这里,她便又觉得师姐的那些话纯是无稽之谈了。
可心里到底还是将这件事装着了,等着封箱戏结束,戏楼里的人都在大堂聚着吃饭,她随着吃了几口,便寻了借口早早回去了。
唯恐遇上了丛山,更怕碰上楼小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