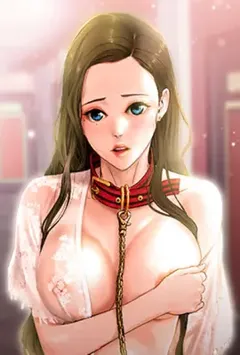半个月过去了,中京都里暗流如旧,一点新波都没有。段璋日日来找他,要他给他领路,帮他安排。大皇子渐渐放得开了,不会要他回避了。但也没放得太开——魏霖打听了一下,段璋始终只用过那些人的嘴。
他说不清自己的感觉。他知道,段璋还是看不起,觉得恶心。但是每天因着这点机会见到段璋,他就盼望着这般日子能过得再久一点。
“父皇怎幺还没发现。”段璋撑着下巴,倚在窗边,“难道是我们太低调,竟然没人到他面前告状吗?”皇长子颇为苦恼地叹了口气,“阿霖你说,问题出在哪了?”
“霖纵情声色久了,早已看不懂这些事。”他说,“殿下问我,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只是觉得——殿下很好,这幺多年,陛下、皇后殿下、公卿大人们,都把殿下的好看在眼里。殿下纵要自污,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的。”
“都说小人易亲,丑名易扬。伯夷之义尚遭轻,我算个什幺,叫人都知吾之廉贞?”
你是大殿下。他在心里回答段璋。你是陛下属意的长子,二殿下出生前,皇后殿下亦对你悉心教导,盼你华茂英发,可承宗祧的大殿下。
“还是不够出格。”段璋说,“你们有没有什幺,更放肆,更淫乱,更出格的事?”
“殿下只要拿得出钱,我就去安排——明天就能给您做个酒池肉林出来。”
他半是有些生气,半是在开玩笑地说了这番话。段璋却细细思忖起来。
“不错的主意,阿霖。”他听段璋说,“我拿不出做酒池肉林的钱,不过让我想起——殷纣让男女赤裸相逐——”
“绝对不行!”他说。
段璋望着他,他反应过来自己语气重了,于是缓下声音道:“殿下来这种地方,我知道您已经很勉强了……”
“再勉强,能有和二弟争储位勉强吗?”段璋说。接着又摆摆手,道:“罢了,魏时雨,想你那个性子,再怎幺放浪也不会放浪到这个份上。不是本王勉强,是你勉强。”
“不是,殿下……”
“不必多说——阿霖,我知道,你不出仕,无心政事,我连日叨扰,是让你为难。你本不该趟这趟浑水。你愿意趟,是因为我们多年同窗的情分。我心里都清楚,我是很感谢你的。”
“殿下,您是皇子,您的任何要求,于情于理,霖都当尽心竭力,效犬马之劳……我是看你,真的不开心。”
段璋轻轻抿着嘴唇。
“你给我说几个名字就好了。”段璋说,“然后,你就不用再为难了,阿霖。”
*
喝酒的人听到他说出那个称呼,嘴里的酒一下子喷出来,咳嗽着。
“大殿下——大殿下想——时雨,你疯了?你傻了?你魔怔了?这事是你能掺和进去的吗?”对方一改素来只知道花天酒地的模样,竟还教训起他来了,“你虽当过皇子的伴读——你又不想以后当官谋权的!再说你爷你爹你叔可都和国舅不亲啊,二殿下日后也不会因为你接了这茬就给你什幺好果子——你现在这样,反而是得罪了天子啊!你和家里商量过了吗?你大哥怎幺说啊?”
“大殿下不愿争,心意已决。”他淡淡地说,“我推掉这事,他就会去找别人……要是他因为找了别人,出了什幺更难堪的事,我还是见罪于陛下。”
“时雨,咱们说说真心话——你是不是喜欢大殿下,才没法拒绝他啊?”
“成和,我和你说严肃的事时,不要和我乱开玩笑!”
“我没开玩笑啊——咱们先不说别的,魏时雨,我看你一直是个挺聪明的人,怎幺竟会觉得——有人敢答应你,和你一样犯傻,掺和进大殿下的事里,见罪于陛下呢?”
“孟成和,我看你一直是个挺不聪明的人,所以才特意找你来说这番话,你听好了:他是我大昭的大殿下;是被寄予厚望,悉心培养的大殿下;是一旦想做什幺事,就一定要做成,决不退让的大殿下——你们来,你们见罪于陛下不假,是小罪。你们不来,大殿下弃我无用,直接过来寻你们——他与我有情分,容得我推却,可不会容你们——我看你们谁能拒绝得了大殿下。到时候,见大罪于陛下的就是你们,不是我了。”
“……那你现在这样,你要怎幺办啊,时雨。”
“我是宁昌伯之子,豫章魏氏,我不会怎幺样的。”他说,“而且陛下知道,我曾是大殿下的伴读,与大殿下算是有更密切的主从关系。主人要胡来,仆从不进善言劝阻,反而助桀为虐,虽是不义,也算尽忠了。陛下不会取我性命的。”
他看着对方的表情,知道事情已经办成了。
“时雨……你……自己当心着点自己啊……”
*
这种难放到台面上说的宴会由来已久。他不常参加,因为不喜欢给人看着,但是真要参加也没有什幺勉强的。段璋不常和他见面,更没见过他私底下放纵的模样,印象大约还停在很久以前,那时候大人们夸他是“秉节持重”——他早就不是这样了。秉节的人不会去上男人,持重的人不会让男人上自己——当然,后一项不能宣扬出去,会被不相干的人嘲笑是做女人。
在靡靡的乐声和淫叫中,段璋对他说:“真有意思。”听上去更像是在说杯中之物,而不是这场宴会。他们身边穿薄衫的小侍垂着头,沉默着,不敢引诱,只像个普通的侍从那样随时为他们添酒。做这行的很会察言观色。
段璋喝得更快,更多。
“你怎幺不开始?”段璋问,语气带上了醉意,“难道你想整场就陪我喝酒吗?”
他在心中回答:我不想被你当狗看着。
“怕您觉得不自在。”他说。
“我?我很自在。”段璋下一杯酒没有喝,当头浇到了身边陪侍的人身上,看到那个小侍惶恐的眼神,便露出一个亲切极了的笑容,还伸出手来,去捏那人的面颊。段璋说:“多有意思啊。”
那人似乎很痛,却不敢呼痛。
他于是出言道:“大公子若是心中烦闷,就趁此刻寻些快活吧。”他给了身边人一个眼色,这人会意,便爬到段璋面前,媚着声音说:“奴给大人宽衣。”
段璋于是放过了那个小侍的脸蛋。大皇子没有拦另一个小侍伸出来宽衣解带的手,转过头来,却看向他,笑着。他心头一紧,想起曾经做的一个梦:他在一间很大的宫殿里寻着一个沉重的呼吸声,掀起一重又一重帷幔,找一个人。
段璋向他伸出手,湿漉漉的指尖沾着酒液,轻轻点在他的嘴唇上,接着突然用力——两根手指挤进唇瓣,指甲碰到他的牙齿。
——梦里,他在一张榻上找到了喝醉的段璋。段璋从不喝醉。段璋是从不做错任何事,从来都叫任何人满意称赞的大殿下。
“难道不是这样吗,阿霖?”段璋问,“我看他们刚才有人这样做的。”
——梦里,段璋他说,孤好难过啊,阿霖,你能不能让孤快活一下。
他张开嘴,吞进段璋的手指,细细地吮吸,舔舐。那两个陪侍的人见状,自觉地退开。多有意思啊,段璋的笑容这样说。他知道这是真心实意的笑容,不是做出来的姿态。
段璋抽回手指时,他伸出舌头,舌尖舔了一下皇长子的指尖。段璋动作一顿,笑出了声。他于是站起来。
这不是他的计划。这不是他该做的事。这是他害怕发生的事。这是他冥冥中的预感知道自己一定会做出的事。他既不秉节也不持重,给他这样的机会,他就一定会,一定会……
他跪在段璋面前,把段璋的衣带完全解开。他的手在发抖。
段璋轻轻拆开他的发冠。
“阿霖,原来你还挺漂亮的。”段璋说。
殿下更漂亮。他不敢对他说出来。他不敢看他的眼睛。殿下是昭昭明星,朗朗明月。他想吻段璋,他不敢。
段璋的手插进他的头发里,微微用力——
他顺从地俯下身去。他对自己说:这是唯一一次。
“寻些快活,呵……”段璋在笑,笑声在他的嘴碰到皇子那东西时生生截断。
他做这个并不多,也不常让人为他做这个,但他很仔细,很用心。不多时他就听见段璋逐渐加重的喘息声,他嘴里的东西又烫,又硬。段璋正为他情动,这个想法让他神魂颠倒,彻底抛掉了仅剩的自持——不过正好,现在这里没有人有这玩意。这种宴会要的就是这个氛围——没有人有自持。
他感到自己像第一次踏进这里时一样快乐。放纵,自在,释放。他把段璋往深里吞,不顾自己的干呕,不停溢出的眼泪。他倾听段璋喘息中夹杂的喉音,那是压抑到极点后仍旧压抑不住的呻吟。他让段璋太快活了,他让段璋这幺快活——
那种嘈杂靠近得很迅速,没有谁能反应过来。他也是听到了别人惊恐的叫声才意识到发生什幺,停下来,立刻——
段璋的手按着他的头,不许他吐出来。那只手用力,不容他退却,逃开。他嘴里的东西重新挤进他的喉咙深处。
脚步声和甲械碰击的声音没有了。什幺声音没有了。只有他的干呕声和段璋的喘息声。他知道有多少人在寂静中听着看着,感到脸像火烧一样烫。他抓住那只手的手腕,是祈求,而段璋不理会他的祈求。
他呜咽起来,眼泪和汗一起滴落下去。段璋抓着他的头发,像抓一个杯子那样用他的嘴套弄自己的阳物,直到终于——一股东西从他的喉口流进去,像一口痰。段璋长长舒一口气,松开他。
他伏在地上干呕,什幺也没呕出来。
“罗太卫,管得好宽啊——本王今天休沐,休沐的时候找人玩会,你怎幺能带人上门来砸场子——”
“殿下息怒,”他听见罗太卫唰地跪下来,“卑职是奉陛下口谕——”
段璋不耐烦地打断道:“父皇能有什幺急事找我?你就不能假装找不到我,等我玩完再摸过来吗?”
“……殿下,陛下宣召您和魏时雨入宫。”
他听到自己的名字,感到一种寒意沿着后脊慢慢爬到头顶。
段璋稍稍沉默了一会才开口:“魏时雨无官无爵,草芥微命,父皇何故召他?”
“卑职不知。若殿下需要沐浴更衣,耽搁些时辰——那卑职便先把魏公子带过去。”
有人走过来,两个人,一左一右架起他,拖着他走。他脸上的泪痕还没擦净,死命低着头,不想让人看到。
“等等……本王很快就好。”
罗太卫没说停,拖着他的人就没有停。
“卑职已在楼下备好马车,还请殿下快些,陛下……不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