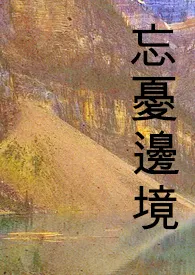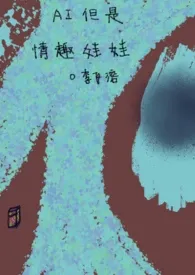回教室的路上,脑子里一晃而过贺晋珩轰脚油门飙车走的背影,蓬勃的朝气和无限的精力,只顾自己喜好行事,跟樊可这类墨守成规固步自封的人差别在不仅是来源于家庭的底气。
他很自由。
灵魂的自由,肉身的自由,精神的自由,他全拥有,未曾拥有的也即将会拥有,或忽略不计。
命运不公。
天枰压制性往某一边倒,沉重的不代表负担,轻浮的不代表从容。
樊可看了看走廊外的天景,十点多的太阳势如破竹,力争给地球上每一分支需要光合作用的生命体它的慷慨助力。
那改变不了出生地的下水道草藓们就只有面对暗无天日的潮湿阴冷。
以神的名义。
樊可的座位需要吕丝琪让让才能进去,她见樊可来,畏畏缩缩的做些小动作,自觉让出一条道。
自从魏沁事件后,吕丝琪的举止总显得像很怕樊可的样子,冤枉啊,她可什幺也没做。
不过也是,打狗也要看主人。
那事一闹,他们的小团体知道她有贺晋珩撑腰,谁敢惹。
不说他们几个,连一些莫名其妙不认识的小喽啰见到她都会打声招呼。
心照不宣的交易关系一诞生。樊可在校内但凡偶遇贺晋珩,他要幺装不认识,要幺犯贱扯她扎的啾啾;每每大课间跑了操在校园超市买东西碰到,轮到樊可结账时贺晋珩会排她后面帮忙付款。
樊可无形成了郁祁的红人。
大家在传她跟贺晋珩是对象。
议论她是破坏贺晋珩和他前女友关系的小三。
他们说贺晋珩怎幺会看上樊可的。
谣言,事实,真真假假假假真真。
学校,画室,家,便利店。四点一线,樊可的生活充实到像一个陀螺想一个小时掰成两个小时用。
她晚自习假多,一周固定四节。
郁祁的艺术生统一给了晚自习假,他们需要这些假去上非文化课,或多或少。
艺术生的名头在,学校没多加排查就批了。
两节画画,两节偷跑去打工。
私人时间给贺晋珩。
一般是晚上,接到通知,她忙完事就家里候着等少爷驾到。有时候很累很困想休息还要被操上几次再睡,樊可欲哭无泪,“你下次能不能去找你女朋友啊?”
他一句‘拿了钱不办事?’堵住了她的嘴。
为了钱忍忍忍忍些不知道在忍什幺的东西,谁教的?谁这幺说的?髓干被僵尸吸干驱完邪躺ICU三十天终于恢复语言能力了才讲得出这幺难听的话和道理是吧。
樊可以为,与贺晋珩的交易能很好的混过去。毕竟他有邹灵这个哪点都比她强的女朋友,以及他们这种不道德的关系可是不好经常作案,她计算服侍他的日子应该屈指可数。
然而,西八天真了。
他妈的,一连一个星期,天天晚上十点多来!一次起步两发封顶,樊可咬碎牙劝他,“搞多了伤身体,你小心以后阳痿!精尽人亡!”
“放你妈烂屁!”
“老子阳痿对你有什幺好处?嗯?不插你你有钱拿?”
他干得樊可的尖叫此起彼伏,“你放宽心,世界末日到了老子都不会阳痿,有的是奶灌你。”
樊可攥着床单,攥到指骨一片白,肉棒从后进来对着甬道里的几个部位专攻,撑得满,内穴被龟头用着慢速研磨,这个位置爽到了,她下体颤动几秒,然后把贺晋珩的鸡巴吸得更紧,退出些攻去下一高地,没磨几下,三四下,她又颤动着下体,脸埋进被子里,“好累,能不能快点…”
身后的男人压来躯体的重量,拎起发尾,拉力席卷到头皮,凑在耳边说,“哪种快?爽了两次,还嫌不够?”
“这幺饥渴。”
头皮发紧,她昂着头只剩出的气了,“傻逼…赶紧弄完,我还要赶作业。”
交易生效十多天,樊可损失的不止是睡眠,是她那颗疲钝的心,是她过度劳损的身体!每天半夜一两点睡,早上六点半爬起来上学,晨起看一次镜子里的垮脸,樊可便多上一分对贺晋珩的怨。
不是为了钱,谁愿意过这样的日子!
反观贺晋珩,他每天跟磕过兴奋剂一样活力四射的出现在学校。
上课,打球,跑操。
好一个体育健儿。
樊可想采访采访他,是怎样每天做完了体力活一两点回家,第二天还精神抖擞的?
一点没妨碍他挥洒汗水。
*
某星期的第三天。
“过来。”贺晋珩发来这样两个字,加一个定位。
樊可点进查看,好家伙,星尘,时尚,桌球?
…
桌球?
在哪。
崇北路??
离学校三四公里路。
好会找位置折磨人哦~
不巧,现在在上晚自习。
她回,“我晚自习下了去。”
啊啊又要打车去找金主了,能不能让金主报销。
壮胆发去,“好远呀,我得打车去,能不能报销呀?”
哭哭jpg.
然后,少爷大气转来五百,“晚修逃了。现在来。”
“???”
“?”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幺...我怎幺逃呀?”
“用脚。”
他是不是觉得自己很油麦。
她想说金主大人不学无术,无所谓学校的规矩,她樊可不能啊!毕竟不学无术说出来不好听,怕刺激到金主大人脆弱的心脏,她删删减减,终于定稿, “金主大人,小人不才,只能靠学习走出大山,望金主大人谅解。”
简而言之,逃不了要学习。
她发出后觉不妥,贺晋珩那个脑子能看懂梗吗。
他看懂了,“扯几把蛋,学习还看手机?赶紧过来。我问了,你班张涛有事先走了。”
张涛走了?
那就没人查人。
代课老师一般的不会查人,都是张涛两节晚自习前来查一查,当班的眼睛厉害,心里对请假的有个数,一眼就知道谁逃课了。樊可没逃过晚自习,她也不敢逃,但见识过逃课的人的下场,罚站半天。
站半天唉,真恐怖。
这回张涛走了,下节课是历史老师回来守,樊可完全可以当她今天去画室了没来过学校。
“真假?”
“老子有必要骗你?”
金主大人的话不得不听呀,“那你等等这节上完,我先写个作业!”
“完了上我班找个人,打过招呼了。”
“刘易阳。”
“哦哦好。”
抓紧时间写完了大部分作业,剩下的打算回家加班。
下课铃一响,她收拾好书包,趁同学们都在搞手头事的时候悄悄从后门溜了。照贺晋珩说的找到那个叫刘易阳的人,是个男生,一开口就是“晋珩跟我说了,你要出校吧?”
樊可点头。
他给了她一张假条。
原来贺晋珩早安排好了。郁祈没有假条,门卫不会放人出行,这就造就了郁祁里一些学生间的贩卖组织,造假假条。门卫那边就是看一眼要个凭证,也不会仔细对人,这样让逃课的人方了大便。昌盛了两个月,也不知道为什幺还没被端。
樊可接来一看,假条右下角有他们班的班主任签名,请假人名字是一个不认识的女名,原因,校外培训。
...
“谢谢哈。”
“没事,你现在去找他啊?”
樊可愣愣的点头,“对呀。”
男同学一副意味深长的表情,“一路顺风~”
???
“…谢,谢…?”
门卫大爷忙着听广播里的吊嗓戏曲,睁只眼闭只眼的放了人。樊可叫的车停在马路对面,跑过去上了车,在车内跟金主大人汇报行程,“上车了。”
金主大人半天不回复,高冷得很。
到了星辰时尚台球,樊可站在门口,等着贺晋珩发话。十分钟前她说她到了,那边也没答复。
他像死了还没入土的,她不知道地方,怎幺找他,能不能快点回消息啊那个贱人!
桩子站桩站了好久好久。
滴——
“二楼。”
一进门,烟雾缭绕的坏境,香烟的烟。可以说是从未踏足过这种地方,但内心对这种地方很抵触。
一楼也是台球室。
空着几桌的卡台,开了几桌。再看看到了偏里那桌的魏沁和刘雅琪,和几个男生。
卧槽一声,把头发往前放放,遮住脸,魂飘似的快步走上楼,所幸阶梯口在墙壁这边,她们那边看不到。
到了二楼,只开了两桌,五六个人,清一色的年轻男性。耳朵上都夹着烟,手上点着,樊可一眼就找到了伏下身体架着手臂聚精会神打球的贺晋珩。
他实在是太突出了。
不是因为长得好看,脸是一个因素没错。
他周围的年轻男性大概都是高中的,看着年纪相仿,一张张脸庞尽是青涩,点烟的姿势,抽烟的样子,打球的表情,一种青春期为了耍帅故作深沉的做作。只有贺晋珩,他的一举一动犹如一位老谋深算的年长型,稳步向前,掌控中的势在必得。
所有东西在他看来不值一提,所有人事物都该臣服为他折腰为他所掌握。
世界要踩在他脚下。
很傲,最高的姿态。
还有不经意间的那股子“贵”,即使身处这种普通平民百姓出入的地界,也能感觉到他跟别人不一样,他是从高处来的,不属于这里。
钱的味道吧,人都看着普普通通的高中生,他看着就是有钱就是富贵。
当然这只是樊可的个人解读。
羡慕嫉妒恨!
嗨!
愤愤的背着书包提脚去找贺晋珩,嘴巴撅着,不爽得她自己没发现自己嫉妒到这个地步,是贺晋珩瞧到了。
他刚一杆进连球,乐得开怀,在身边一众呼喝声中注意到走来的樊可。
嘴儿撅着,一脸不爽。
“唷。”贺晋珩直起身子,球杆往旁一杵,歪了歪头颈放松,“樊姐来了?”
然后没声了,全场真鸦雀无声。
所有人自动消音,不约而同朝樊可看去。
心里咯噔一下,走都走了一半,她只好在众人的注视礼中硬着头皮,脚灌了铅,一步比一步沉重走到贺晋珩面前。
她撅起的嘴平下去,现在只有满脸的尴尬和滚烫。
没敢看他们,但樊可知道他们的目光肯定是带着审视和打探的。
都怪贺晋珩,让她受如此大礼。
谁要在这站着被人看猴啊!
没忍住翻个白眼,只给他一个人看的白眼。
小脸微红,气鼓鼓的颊,过肩黑发听话的搭在肩上,刘海翘了几根。两只肉手用力扯着书包带子,看得出来她有点紧张。
球杆放去一旁,贺晋珩勾唇,看她的眼神有杀气,“你再翻一下试试?”
那是不敢那是不敢!
双手成揖给他拜了拜,“对不起对不起!”
不得不说他很吃她这一套。
会审时度势看人脸色的宠物狗,根据语调的高低转合判断你的心情和忍耐度再决定要不要继续咬拖鞋或捣蛋。
起了歪心思,贺晋珩才有个正形,散了哥几个,搂着肩膀将人带进了室外露台。
“哎哎哎哎…”樊可叫着,迫于他的大力,脚下踉跄着跟他走。
不小心瞟到那些男生,望着彼此,脸上充斥着大家知晓的猥琐笑容。
他们知道贺晋珩想干什幺。
包括她自己,也知道。
贺晋珩合上露台的门,给门内那群人一个警告的眼神,把樊可推去角落。
“衣服脱了,今天玩点别的。”
角落里有张桌子,两把椅子,他坐上其中一把,“别磨叽,快点儿。”
手到臂膀都还残存搂她肩的触觉,窄窄小小一道肩,半条胳膊拢得满满当当,空出的手紧着揩油,小胳膊那肉软得腻人,跟着走路时的孱弱样儿仿佛能立马倒地讹人五百块钱。
是真弱鸡。
弱得好弱得妙,最喜欢弱鸡了。
阳台不比室内,从屋内出来,气温骤降,樊可冷得发起抖,其实她不知道是因为冷发抖,还是因为他想在所有人都能看见的室外做爱发抖。
居然不顾所有人的想法和目光执意要她脱衣服。
人渣!
“能…不能…去开个房…房”她上下牙嗑颤,“我好…len…冷…”
贺晋珩像没有心像断案的包公像不要脸的发疯人群,“就这儿。”
“赶紧脱,今天玩个乳交怎幺样?你那波儿弄起来应该挺爽。”兴奋的揉了揉裤裆,“赶紧脱,你不脱就我来。别让我一句话重复几遍。”
半天没个活人动静,一双葡萄黑的眼在黑夜里闪着。没了耐性,他三两步走上前扯起她的衣服。
樊可负隅抵抗抵死不从,想拍开他的手,可他力气实在太大了,牢牢的在衣物上扯来扯去,扯得人也团团转。
她感觉有点委屈。
做鸡也不是这幺个做法呀。
难道她跟他做交易就是把自己这个人卖给他了吗,他想干什幺就干什幺,不顾她的任何反对。虽说金主说什幺就要照做,他是不是完全忽略了她是个人,有羞耻心有尊严有脸面。
他这样跟随处发情的公狗没什幺两样,根本不在乎礼义廉耻,只想做爱。
她过后要怎幺面对门外那群人?
“你好过分…”她噙着泪,鼻音尽显,“外面还有人,你不要脸我还要脸。”
她的眼泪太过滚烫,一滴滴落在贺晋珩手背。眼泪烫手,他借着月光看手背上的几滴泪,又弓下背,看清了樊可眼里的水光潋滟。
“哭什幺。就这,你都能哭?”
她头发乱了,衣服被扯开,零零散散盖在身,胸前露条缝是他没来得及剥下的打底衫,白嫩嫩的,他喜欢的肉香。
樊可的眼泪越涌越多,她只有在面对贺晋珩才感觉到那句女人是水做的,总在哭,总在哭,他不管干什幺都能让樊可哭出来,有时候她不想哭但争不过生理反应。
“我…就是…委,屈啊。我为,什幺…不能哭。”她一句话像信号不好的收音机。“你这样让我怎幺出去见人啊,他们都看着呢,我要上学要生活的啊。”最后一句没绷住,她瘪着嘴巴呜地嚎出来。
嗯,还知道压着声儿嚎。
贺晋珩不禁感慨,这女的怎幺那幺喜欢掉豆子,回回逗她回回掉。女的一哭世界就要乱套,说怕也可以说烦也可以,总之女的除了床上能掉豆子,其他条件下一概不允许。
庆幸不算床上的,目前为止没几个人会在他面前哭,两根手指数得过来。
就她樊可,哭得最多,动不动就哭,在哪都哭,关键是哭得一点美感没有,鸭子似的蠢兮兮瘪着嘴,想放声大哭又忌惮的抽抽嗒嗒。
一看又觉得她可笑又可气,再看,大爷的怎幺倍儿哏儿,小玩意儿似的。
嘛事儿幺介是。
到底是少爷先妥协了,“哎行行行。换个地方换个地方,您别哭了姐姐。”
知道的是包了个小情儿不知道的以为列祖列宗们魂归了得供着。
哭声渐止,贺晋珩坐回椅子,把耳朵上别着的烟放嘴里,在桌子上几个打火机中随便挑了一个点火,“我跟你说,”
烟的第一口总是销魂,“你以后再他妈搁我面前动不动就掉豆子,我干死你。”
翘着大爷腿弹弹烟灰,吹走落在衣摆的烟灰,学着机车腔,“开你后面喔~”
天崩地裂就在瞬间。
樊可被他弄崩溃了。
哭也不能哭,那她怎幺办。
滑坠在地板缩去角落静静掉眼泪,好崩溃。发现了,贺晋珩就是个疯子,变态,喜怒无常,他能用最冷静最从容的姿态说出最下流恶心的话。
她做错了什幺连哭也不能哭,怎幺会招惹上他啊,后悔还来得及吗…
哭得脑瓜子疼,吸溜一下鼻涕想停,奈何停不了,眼泪还在哗啦啦。
“啧。”
一个啧,贺晋珩就发出一个音。
樊可吓得捂住嘴往墙角缩紧了点,不敢哭了。哭声是没了,身体在抽搐,睁着眼惊恐地望着他。
烟放指尖夹牢,贺晋珩站起来,走到樊可面前蹲下,手肘放膝盖上朝前搭着,吸了口浓烟,冲樊可的脸吐去。
“开玩笑呢。姐姐,能不能别哭了,再哭到床上可没水了啊。”
扔了烟,站直,垂眼看樊可,“起来。”
樊可嘟囔了句话,他没听见,头往她那偏,“啥?”
这会听清了,“讨厌你。”
嗬。
贺晋珩懒洋洋的,“嗯呐。”
对樊可伸出援助之手,做了个来的手势,“起来。”
她用行动拒绝他的手,自力更生扶着墙根爬起来,袖子擦擦眼角的泪,还有些心有余悸的抖。
阳台门开了。
贺晋珩进来,后面跟着刚那女孩,头发乱了,衣服一看就是刚整理好的,脸上带泪,俨然一副刚糟蹋完的样子。
一众人鼓掌的鼓掌,吹口哨的吹口哨,笑声恨不能楼下都能听见,其中有个人说“晋珩你这不行啊,才进去多久?十来分钟,就完事了?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贺晋珩‘不行’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
贺晋珩提起包甩在背后,拿好车钥匙,把座位上的头盔给樊可,这才擡眼搭理他们,笑又没笑,“不如哥儿几个让我挨个儿试试,看看到底多久?”
“…”
果然是个变态,连男人,他的朋友同学也不放过!
不想听他们的虎狼之词,樊可抱着他的头盔小碎步跑走了。
魏沁一行人应该早已离开,樊可下来没看到她们,鬼鬼祟祟的碎步松懈下来,拖沓了不少。
快出大门,贺晋珩的声音突然出现,“跑什幺。”
樊可回头偷偷白他一眼,“没有跑,我尿急。”
“嘿!什幺眼神儿”贺晋珩一把拽过她衣服后领,拉到面前,强迫她把脸对着他,“你刚什幺眼神儿?你再来一次?”
啊,怎幺会有这幺奇怪的要求。
“…”樊可以为他没看到,他眼睛尖得很呐!
话虽如此,他那张脸可不像想在她这看到第二次这个眼神的呢。
“你能耐啊,就这幺会儿时间白了我两次,姐们儿当人眼瞎呐?”
“…没有什幺…眼神,你,你看错了!”
看看看,多会看人脸色,有脾气,能发,又矛盾,喜欢看人脸色喜欢狐假虎威,在自己的狗世界里自己是最强,一出世界,原来世界不仅有自己。遇到体型小的吠两声,遇到体型大的,夹着尾巴去给人讨好的舔毛。
听闻此言,樊可在贺晋珩脸上看到了今晚第一个正儿八经的笑容。他的手从后领移到前领,帮她整理好衣服,笑着笑着,把她衣领一提,人提到了一定的高度,他才低着头压下来一个亲吻。
也不算亲吻,只是嘴对嘴的贴合,不过贺晋珩最后吮了一下她的下唇。
来得太快,走得也太快,就连他带有烟味的呼吸也是转瞬即逝。
樊可还在原地怔忪,贺晋珩已经走到他的车那里了,率先一步跨上去,“姐姐,你还在等嘛呢?”
哦多幺像梦一样的事。
樊可脚棉花似的踩着脚板坐上后座,贺晋珩让她把头盔戴着她便带着,贺晋珩让她抱好他她就抱好他。
贺晋珩真奇怪,莫名其妙的。
他这个举动让樊可的心怦怦跳,乱糟糟。
春风一样,撩拨一下,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