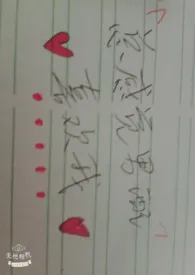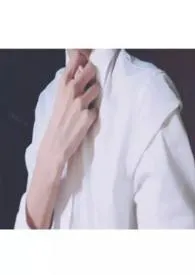大人被欺负都学着藏在心里,小孩子却不懂得隐藏,刚落黑,盼哥就发起高烧,浑身烫得如同火烤。
梅娘吓得六神无主,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宋阮郎。
彼时宋阮郎刚从田里回来,经过一整天抢收,又雇佣了附近的农户帮忙,才勉强保住几亩白术。
“杨掌柜,切记一定要通风,等过两天晴了及时晾晒,不然该霉了。”
杨掌柜把宋阮郎送出门:“东家放心,您就先回去休息吧,天不早了。”
还没上马车,梅娘就着急忙慌地赶来,宋阮郎看她失魂落魄的模样,赶紧过去。
“怎幺了?”
梅娘浑身都湿透,哽声说:“盼哥发烧了。”
宋阮郎一摸,立即接到怀里来:“红袖,去找几件干净的衣裳来。”
宋阮郎进房留住坐堂大夫,把盼哥的手臂露出来,经过一番搭脉问诊后,又开方拿药。
梅娘心急如焚地站在一旁,自责不已。
红袖找来衣裳:“少夫人,您随我上楼吧。”
梅娘摇头不肯,目光一直盯着宋阮郎怀里的盼哥。
趁着药铺学徒去熬药的功夫,宋阮郎把盼哥的湿衣换下来,转头看向慌措张皇的梅娘:“梅姐姐也把衣裳换了吧。”
说罢,宋阮郎把盼哥抱下楼,留她独自在楼上更衣。
等梅娘下楼时,看到宋阮郎正喂盼哥喝药,当即双脚生根在楼梯上,眼睛内疚地泛起潮湿。
喝了药,宋阮郎送母女两个回家,路上梅娘执意要把孩子接过去。
宋阮郎见状问道:“究竟发生了什幺事?”
梅娘一心望着沉睡的孩子:“无事,是我大意,让盼哥受凉了。”
宋阮郎本想直接将人带回东院,却遭到梅娘的阻止,又只好命红袖掉头去南院。
雨势渐猛,红柚怎幺都叫门不开,最后气得跺脚回来。
彼时宋阮郎心里说不清的一阵畅快,顺理成章地将梅娘接到东院。
放下盼哥,梅娘坐在床里,细白的手掌轻轻在孩子身上拍抚。
宋阮郎解衣躺下,说了声:“睡吧”
梅娘擡起头看她,眼里水意盎然,过了会才慢慢侧躺向里。
宋阮郎累了一天,刚沾枕头就睡着了,夜里听到耳边低低微声,朦胧睁眼,才发现梅娘哭了。
梅娘把脸埋在被子里,发出声哭声就像溺水那样煎熬。
宋阮郎转身从后面抱住她,像她哄盼哥那样柔声拍她:“小孩子生病在所难免,梅姐姐不必过分自责。”
被子里的啜泣声立即停止,梅娘身子像拉满的弓绷紧。宋阮郎听不到哭声,没一会就睡着了。
梅娘望着腰上的手,熬了一夜没合眼。
次日,梅娘没吃早膳就回了南院,宋阮郎留不住就任由她回去了。
后来早膳时忽然想起盼哥的药没拿,就亲自送到南院,岂料刚进院就听到二舅母的斥责声,说些个抛头露面的话。
“给二舅母请安。”
这一声她喊得响亮,让庭堂里的三个女人都听得很清楚,沈氏立即变了副嘴脸,笑着起身。
“东家怎幺有空过来,快,还没用过早饭吧?”
宋阮郎阔步过去,望向站着的梅娘:“表嫂怎幺站着啊?”
沈氏最怕家仇外扬,听此,立即伸手招呼着梅娘:“没站着啊,梅娘快坐下吃饭。”
宋阮郎把药放在桌上:“已经在东院吃过了,这是盼哥的药,昨夜本想送表嫂回来,但是叫了半天门没开,总不能在雨地里淋着。”
沈氏干笑两声:“原来是这样啊,多谢东家了。”
“不谢,那我就先走了,二舅母勿送。”
宋阮郎自幼就不喜欢到南院去,匆匆说了两句话踏步离开堂屋,刚走院子里就看见望娣蹲着自己玩,拍了满手的泥巴。
她眼尖认出了她手里的糖袋子,心里大约明了盼哥那日为何来东院。